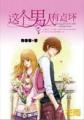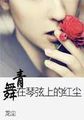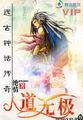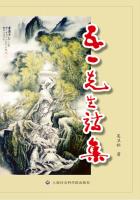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柴家的这个年在热闹喜庆中过得似乎特别快,不知不觉就已经过了元宵。今年的这个年,过的最快活的,除了重新回到家里的春梅,就数柴永康了。按照江南的民俗,嫁出去的女儿在除夕到初三的这几天里,是不能回到娘家过年的,必须和婆家的人共度佳节。柴永康却说女婿家已经没有活着的长辈,这规矩也就不用当真了。因此,除了除夕和大年初一,其余的日子春梅全家都是在她娘家度过,只是到了晚上才回家睡觉。
春梅的儿子长生,成了柴永康的宝贝,只要是他们全家一进门,长生就和舅公不离须臾。弄得春梅的几个嫂子开玩笑地说公公不疼孙子,独独疼爱一个外甥,心也长得太偏了一点。
长生也是,他本来就不认生,见了谁都自来熟,人又长得特别讨人喜欢。几个舅舅、舅妈嘴上说老爷子偏心,实际上也都很喜欢他,争着塞“压岁钱”和东西给他,逗他开心。不过长生还是和舅公最好,没事就黏在柴永康身上,有时候手下没轻重,把舅公稀稀疏疏的山羊胡子揪下几根来,舅公反倒乐得咧着嘴笑。孩子还小,男孩子开口也晚点,长生至今还不会叫“舅公、舅婆”,只会含混不清地发出“球、球”的声音。柴永康却不管这些,没事就逗着长生教他叫舅公。
元宵节一过,新年也就算是过完了,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开春的事情。正月十八以后,祝家桥镇上差不多所有的商家都开了门,开始新一年的生意。梁家的几爿店也是如此,梁子奚显得比过年前更为忙碌,不但要忙镇上两爿店里的事,还要兼顾城里和滨湖两头。
梁家的这个年虽说也是阖家团圆,迎来送往宾朋满座,真要细说起来却都过得并不十分舒心。梁家在祝家桥上的两爿店,是梁子奚赖以起家的根本,去年一年经营得还好,但是受到环境的限制,生意做得并不大。他家现在主要的生意是靠临江城里那爿店,还有滨湖与人合伙的那一半股份。去年上半年,县城的店经营还不错,但是到了下半年却每况愈下,收入日渐减少,也找不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滨湖和人合伙的生意,开了几年,倒是一年比一年红火。这家店虽然梁子奚只占了一半股份,但是红利却已经上升到了他几家店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人们常说:几个人合伙做生意,做不好是分手,做好了也是分手。这话很有点道理,梁子奚现在就面临着和合伙人分手的可能。当初这家店是梁子奚利用自己生意上的关系开出来的,由于资金不足,再加上鞭长莫及,管理上需要一个当地人出面,这才找的现在这个合伙人。几年下来一直没事,但随着营销渠道逐渐被合伙人掌握,生意的利润也越来越好,事情就出来了——合伙人借口他直接掌管,付出的辛苦多,所以要求将“五五分成”改为“四六分成”,他要多拿两成。
梁子奚在过年前就和这个合伙人交涉了好几个月,可是没有进展。这家刚开始发达起来的店,面临的是要么自己让出一成利润,由平等的合伙人变为二股东;要么就是一拍两散分手。一旦分手,这家店所有的经销渠道和创出的人气,就顺理成章地全部都落到合伙人手里,自己只不过落得个“为谁辛苦为谁忙”的下场。
大女儿秋烟和女婿过年的时候双双过来省亲,看得出两人的关系愈加不睦,梁子奚心中更添块垒。他没有责备女婿——女儿没能为夫家生育,自然也就气短。他知道这不能全怪女儿,但世俗如此,只要不能生育,似乎就错在女方,他又能说什么呢?
梁子奚将镇上的生意全都托付给了管家,自己进了趟县城,匆匆安排一番,马上就赶往滨湖,家中顿时冷清了起来。
梁寒烟也不开心。她在柴春梅私奔,柴家颜面尽失之后,也曾暗暗窃笑。但是很快,她就为了春梅得遂所愿终于和赵汉昌走到一起,心中生出嫉恨。正当她的这种嫉恨随着时间渐渐消散之时,柴春梅却和赵汉昌携手回家,不但得到了她爹妈的原谅,还带回了一个儿子——据见到过春梅儿子的人说,那孩子长得乖巧,十分讨人喜欢。今年这个年,自家的人各怀心事,过得并不很开心。柴家却大肆张扬,过得热闹非凡。她心中的嫉恨更是快速发酵膨胀,恨不得天上掉块大石头,砸到柴春梅全家头上才解气。
梁子奚走后,家中就留下了寒烟母女两人。寒烟的母亲唐婉芬平日不大管事,和这个二女儿也说不到一块儿去,寒烟在家里就愈发的寂寞难耐。一过“八九”,天气明显回暖,她在家里更坐不住了。祝家桥离开临江县城有几十里地,附近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她只有在镇上游荡,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新鲜的玩意儿打发日子。
春梅现在有了儿子,所有心思就都扑在了长生身上,她爹妈又宠爱外甥,两天不见就会差人来叫,于是她就会带上儿子回娘家去。家里现在一应开销都有爹爹照应着,他们根本不用操心。爹爹给的八十亩地,现在也还没到收获的季节,没有什么大事,一些小事情则自有柴永康请来的管家打理。春梅三天两头回娘家,赵汉昌作为女婿,也不便每次都跟了去,又没事可干,他反倒觉得难受,还不如以前天天在码头上扒食来得自在,甚至还没有在九里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宿的日子来得踏实。
赵汉昌在家无所事事,实在憋得慌,于是在春梅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个人到祝家桥镇上去闲逛。他去原先住的小柴屋看了看,不过两年的时光,原本就破败的小屋由于缺人气,已经倾颓了,只剩下大半个屋顶还算完整。他最常去的地方还是码头,看着那里熟悉的情景,听着和以前没什么两样的嘈杂声音,闻着并不陌生的各种气味,他不禁想到了过去。短短的两年多点时光,祝家桥没变,他却变了。他现在有钱、有房、有田地,有了自己的女人和儿子,也有了“身份”。可是他却觉得好像比那时候少了什么东西,至于到底是少了什么,他说不上来,只是有时候还对以前那种生活有种留恋。偶尔他还会有一丝后悔——后悔自己回来了,后悔没有回九里汇去——那里的生活是比现在苦,可是好像过得比现在反而自在。
码头上的人大多都熟悉,见到他都和他打个招呼,可是他觉得他们和自己有了距离。这种距离不是他造成的,而是以前那些互相呼喝小名,有了不痛快可以随口对骂几句的伙伴和他疏远了。他们见到他还打招呼,但是再也不会对他说粗话,变得客气了起来,也不再是无话不谈。几个长在码头上走动的老板,见到他大都显得客气而冷谈;那些一起挣饭吃的力夫、伙计,则和他没了以前的那份亲热。
赵汉昌在码头上感到了一份孤寂,但他还是愿意到那里去。在那里看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们忙忙碌碌,即便没人理他,也比在家里被管家、仆人和丫环恭恭敬敬供着舒服。
春梅在家的时候,赵汉昌和她说说笑笑,逗逗儿子,还是很开心的。不过也有让他不习惯的事——刚住进来时,管家和下人都叫他“老爷”,叫春梅“太太”。不但是他听着觉得别扭,连春梅都觉得好笑,对他们说了几次,后来管家才让大家改了称呼。管家要大家随着柴家的规矩叫春梅“小姐”,而叫赵汉昌是“姑爷”。他听着还是不习惯,但春梅不再反对,他也就没说什么。
这天春梅又带上长生去了柴村,临走时问赵汉昌去不去?赵汉昌想到前天自己刚去过,再说一旦去了,基本上就是一整天,这一天他在那里坐也不自在,站也不舒服,所以就回答说不去了。春梅知道他在爹妈面前不自在,也就不强求,一个人带上长生走了。
春梅走后,赵汉昌挨到吃了午饭,就出门朝镇上走去。到了镇上,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还是来到了祝家桥上。他没有下到码头上去,而是倚着桥栏,远远地注视着河面上来往的船只,还有码头上奔忙的人们。
他正看得入神,忽听有人叫他:“汉昌。”
他回头一看,叫他的是梁家的二小姐寒烟。回家这么多天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他回来以后回忆起了不少事情,却很少想到这个梁寒烟,差不多就把她忘了。现在梁寒烟叫他,他想起以前和她也算有过一段交往,她也算是曾经帮过自己,所以就和她打起了招呼。
两人互相谈了几句,梁寒烟说道:“汉昌哥,这儿太吵了,我们到茶馆里坐坐吧。”
赵汉昌闲来无事,对这提议也没反对,茶馆就在桥边,两人在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要了茶水,开始聊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