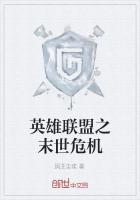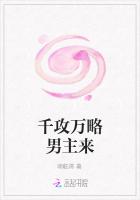婚姻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感情的归宿,尤其是中国人的婚姻,肩负了太多的社会职责,夫妻之间不做爱又如何?如果单纯为了性,可以解决的方式有很多,何必一定要影响婚姻?
男人如是,女人更是如此。
几天前还看到另外一篇专栏文章,说,女人的婚姻选择从来都不是A类结果,往往都是B类以下的那个选择。女人对于婚姻,有着比男人更现实的考虑和量度。这和女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保障密切相关。
2006年有一个调查数据说,超过51%的美国女性主动选择了单身,她们认为,单身生活比婚姻更让她们感到快乐。恋爱当然是要有的,只是不再勉强自己一定要有婚姻,除非那婚姻能够是A类选择。
社会学家说,女人的经济独立,使女性可以拥有越来越多的自尊和自由,也让她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心灵独立,这些变化促使她们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件商品,以各种方式等待着买商品回家的那个男人,而是选择了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选择真正适合她们自己的状态,包括选择真正适合她们自己的男人。
只不过,生活到底要过成什么样,有性?抑或自宫?或者虽然不从生理上自宫,但从心理上自宫,只要能够保持住一段关系,保持住一段婚姻,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当事人自己的切身感受。
一个季度都不做爱,每天看她的脸色,但他仍然甘心情愿与她在一起,别人又何必多言多说。
女人不爱这个男人了,不愿意让他触碰自己的身体,也未必就一定会提出分手。这本杂志,对女人并没有完全彻底的了解吃透。
生活从来都是过给自己的,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感受得最清楚。还是把这类问题留给当事人自己去处理吧,要求别人发生改变,始终都是皇帝不急急太监,到头来急死的太监既没看到皇帝改变,自己还落得个灵异他处,牺牲得既没意义,也没价值,不若当初放任不理。
世间万物,都只是个人意像的投射,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非常享受,那就好好的一个人自在享受,大可不必一定要教别人如何依法照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必强求一致,不必把别人的问题压到自己的身上,替别人去沉重,疲惫自己。
正在读一本好书《告别娑婆》,渐渐学会了这个道理,正所谓黑白泾渭,各司其职,他死他痛他伤,都是他自己的业和命,谁能真的替他?
他的命,让他自己去经历,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
单身生活,时尚还是罪过?
有人说,单身女人是“社会公害”;也有人说,单身是一种新的时尚。
不管外界对单身女人的评价如何,单身意识是帮助女人获得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当你拥有了单身意识,生活就会开始进入加法状态,因为即使什么也没有,你也还是一个完整的独立个体,生活不会因为没有爱情没有男人没有其他那些附加的东西而呈现出不断耗损的下降状态。
根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结果,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的未婚人数每年以28%左右的比例逐年递增。这说明,主动选择单身生活的人越来越多。选择单身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有人说,女人单身是心虚的表现,是骨子里的不自信让她对婚姻充满恐惧。事实或许只是单身女人通常比较挑剔,苛求更完美的生活,认为婚姻不仅仅是一种合作关系,还应该有爱情的因素。没有爱情的婚姻,对于一个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的女人来说,是不能够容忍的,所以她们宁可选择单身。
主动选择单身是因为对自己更负责任,她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她们肯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负责,而不是被动地选择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为了结婚而结婚。婚姻和爱情的确有所不同,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匆促进入婚姻,不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另外一个人的辜负。
至于说单身女人是社会公害,这个词说得有些偏激,因为一个婚姻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第三者,而取决于婚姻中的两位当事人。如果婚姻本身没有裂痕,第三者再怎么费劲那只脚也无空可插。
换个角度去讲,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自身的魅力可发掘。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单身只是其中的一种。无论你选择了哪种生活方式,独身、结婚或有伴侣但不结婚,都始终要记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首先是你自己,你是单独的一个人,如果你能够首先把自己这个个体经营好,你的生活就会处于一种加法状态。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加二十分;有一份好的工作,加二十分,这些统统都没有,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你还是原来的你自己。
有单身意识的女人,这便是我所理解的单身女人的概念。
只有第三性
犹太人祈祷时说:“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而他的妻子也顺从地说:“感谢上帝按他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我。”
柏拉图在感谢众神的祷告中,首先感激的是把他造成了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然后才感激把他造成了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
17世纪有一位不太出名的女权主义者普兰·德·拉·巴雷说:“制定和编纂法律的人都是男人,他们袒护男人,而法理学家则把这些法律上升为原则。”
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的女权作家、女学问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经典著作《第二性》里曾说到:“立法者、教士、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都很想证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的。男人创造的宗教反映了这种支配愿望。在夏娃和潘多拉的传说中,男人把女人当做敌人。他们还利用哲学和神学来助威,如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语录就是如此。自古以来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都以揭露女人的弱点为乐事。法国的文学充满了对女人的野蛮指控,对此我们已司空见惯。这些敌意有些也许是有根有据,但一般来说是空穴来风。”
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使女人加入了产业大军,她们的经济基础.那些反对她们的人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为了证明女人的劣等性。当时反对女权的人不仅利用宗教、哲学和神学,还动用了生物学、实验心理学之类的学科。他们顶多愿意给另一个性别“有差别的平等”,和针对北美黑人制定的歧视性法律中的“平等但要隔离”如出一辙。
即使是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而使一切都变得无比快捷,使整个地球都缩小成一个统一部落,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女人幡然觉醒,可还有大多数的女人依然摆脱不了从属的地位。
男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爱情是女人的最高成就,为的只是让女人把她的生活不断奉献,而这奉献却并不是他急于接受的东西,他不过是为自己多些囤积罢了。
对爱情的盲目迷信,使女人变得脆弱不堪,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
而男人从来不会认真对待女人的眼泪,尤其是在职场。
爱情是以最动人形式出现的祸根,它沉重地压在被束缚于女性世界的女人的头上,无数的爱情殉道者都证明了,这种不公平的命运不过是把不毛之地的地狱,当做最后的拯救提供给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