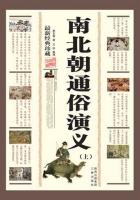这年二哥上五年级,班主任王森水和父亲无论怎么做工作,二哥也不想上学了。这与我正好相反,我上学的时候没人管,虽然调皮,但对学习还是充满浓厚的兴趣。
“保贵啊,我和你叔都是为你好,你要好好想一想,以后不上学怎么办?要注定一辈子下庄户了。”王森水说。
“老师,别逼我了。一提上学我就难受,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逼我了!”二哥说。
就这样,二哥步随大哥、姐姐,三人小学都没毕业。
不知为什么,我这辈子注定和二哥结怨,自从记事起,我们两个就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经常父母不在的时候,找个借口就偷着打起来,虽然我打不过他,但也不服输,更多的时候是对骂。当着父母面,我一般不敢和二哥打,父亲老是把罪责归就我身上,即使是二哥的不对,他也拿我出气。
秋天,我放学后刚把鹅赶进圈里,放下沉重的装满兔子草的筐子,抚摸着被筐子压得红肿的胳膊歇口气。
“福收,去把门前那车子棒槌秸卸下来,我喝口水,还要推去。”父亲又吩咐我。
“叔,你没看我刚放鹅回来吗?二哥在干啥?怎么老我干。”我也累了,说开了抱怨话。可不知道,刚才父亲找二哥干活,二哥躺在炕上哼哼唧唧不起来。秋天正是忙时候,他竟然躺着睡大觉,父亲拿他也没办法。
其实,这几天我心里也憋着气。在学校里上晚自习时,我看见一个人影在门口晃动,煤油灯下我也看不清是谁,我以为是哪一个学生,就多嘴说:“大冷天的,你在外面干什么?不进屋里暖和暖和。”没想到外面那人听到了,“呼”一下子推开门,我一看是语文老师高保地,那时,原来的语文老师王学香已经出嫁到外村了。高保地在学校打人是出名的,他爸是国民党,逃到了台湾,此后他跟着母亲嫁人不知挨了多少批斗,当了老师后,整天不知道有多少火向学生身上发泄,加上特别瞧不起我们村西南角出来上学的家庭贫困的学生,已经不知几次把我们西南角的学生轻则找碴叫到黑板下用手摁着我们的头在黑板上碰,重则挨他穿着那时最流行的火箭式皮鞋的脚踢。他还美其名曰“严师出高徒”。
“完了!”我心底一凉。
“过来!”他大喝一声。
我规规矩矩地走到讲台下走廊上,他一句话也不说,走到我后面,用手把我身体扳正,突然“噔”飞出一脚,跺在我腰上,我就像小人书上画的日本鬼子背后挨了枪子一样,强大的冲击力不得不使身体向后仰去。疼痛中又挨了两脚。就这样,三脚把我踢到了门外,并在外面罚站两节自习课。
一想起这事情来,我就来气,我好心好意地随便这样说了一句,就被挨了一顿重打,回到家还不敢说。
父亲本来怄着气,我这么一说,他气冲我出,随手拾起根梧桐树棍拦腰就打来,我猝不及防,想不到父亲竟然会这样做。梧桐树棍打在我腰上都断了,可想而知,那力量有多大。即使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那梧桐树棍,我腰就痛。
“你这小子,还管不了你了,你再给我犟嘴!看你再给我犟嘴!”父亲边抽边骂。
母亲正在锅里捞小麦晒干后磨面,看父亲这样,急忙过来拦住。
“你还不快跑?在干啥?”母亲对我说。
“你干什么?他刚回来,你这不是找事啊,拿孩子发泄。”母亲又对着父亲火起来。这些年,父亲始终是怕母亲,母亲这样一说,父亲丢下手中的半截棍子不说话了,顾自卸车。
我呜呜地哭着跑到村后面,坐在一捆棒子秸上伤心地抽泣着,心里冤冤的。
月亮上来了,看起来那么安详,那么宁静。整个大地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纱,给人一种朦胧美。远处传来拖拉机突突的耕地的声音,偶尔见一两辆牛车“哞哞”经过,拉着满满的拖拉到地的棒子秸,慢腾腾地扫着地面走着,像画家的大刷子在路上画着秋夜。身边和我做伴的是蛐蛐在轻声地歌唱着。我真喜欢这种和谐的美,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庭就整天折腾不停,像马蜂窝戳了一竿子,吵吵嚷嚷,闹来闹去。
我只想这么静静地坐着,真不想回去。心想,放了学,我把书包一扔,作业都没做,就挎着筐子赶着鹅出去了,刚到家就挨打,心里越想越冤,越不想回家。
“收噢——收噢——”村里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忍不住了,母亲一般是不出来找我的,到了出来找我的时候,肯定是着急了。
“娘!”我老远喊了一声。母亲已走到村东在和一户人家说话,我模糊听见是问见到我没有。
“你跑哪去了?”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快走,回家吃饭去。”
“快吃饭吧!明天还要上学。明天我让你二哥去帮我推棒槌秸。”父亲见我回来了,搭讪道。他明知自己做的过分,也不好多说什么。
晚上作业我也没做,就躺下了。一般我和大哥、二哥在西屋睡。父亲、五叔在南棚,姐姐和母亲还有弟弟一起睡。
睡到半夜,我被一阵的穿衣服声音弄醒,借着月光一看,是二哥。他轻手轻脚下炕,从橱底下掏了两个编织袋,轻轻地闭好门出去了。
已近望月,高挂西南。万籁俱寂,秋韵浓浓。偶尔露珠吧嗒吧嗒地从盛开的牵牛花上滴下,老鼠、刺猬在草丛里地活动,使妩媚的降媚山在黎明更加寂静。一个身影闪现在果园边,迅速扒开一个缺口,灵巧地钻了进去。
几天来,我感觉房间里满是浓浓郁郁的苹果香,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苹果,最后发现那香味是从炕上的一个大箱子里发出的,箱子用一把小锁锁着。二哥没想到我竟然还有那把锁的钥匙。打开箱子,金光闪闪,像神话传说中阿拉丁神灯打开了宝藏,满满的全是“国光”。呵呵,我明白了,这是二哥下午睡觉,晚上出去干的活。我拿了一个,咬一口,酸酸的甜甜的。哈哈,不用费事还能吃到苹果,哪有这般好事。每隔几天,我就偷偷地打开吃一个,尽量恢复箱子里苹果的原样。
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二哥的眼光老是敌意地看着我。我估计是不是他发现苹果少了,吓得再也不敢打开箱子偷吃了。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刚放学回家。
“军,你和收去南沟刨点茅草,晒干摊煎饼,顺便把兔子吃的捎回来。”母亲喊着二哥和我的乳名吩咐我俩。
我挎着筐子,二哥抗着镢出门了。
南沟一片开阔地,地头一段是一栋墙一样的山岭。民兵连长李天曙正领着民兵在用半自动步枪练习打靶。打靶结束后,一大群孩子疯似的跑进地里捡那些黄铜铜的弹壳玩,或用镢在岭上刨子弹头。我挎着筐子沿着沟边挖那些野茄子、荠菜、苦苦菜等兔子吃的,二哥则扛着镢到处刨岭上的茅草。
我的筐子一会儿满了野菜,二哥刨起茅草来浑身懒洋洋的,身边没多少茅草。一会儿发现他去刨那些嵌在土里的子弹头却来了劲头。
“军啊,你下午就刨了这些茅草,你干什么去了?白养活你啊!整天不干活。”母亲看二哥回来就带了那么点茅草。
“你以后少向咱娘告状啊!吃饱了撑的!”二哥瞪了我一眼,径自进屋,从兜里掏出一个个子弹头放在一个木盒里。其实那东西没任何用处。
“收啊,家里的洋火怎么拿出一盒一会儿就没有了,到哪去了?不知道两毛钱一封洋火,挣那两毛钱容易吗?”母亲发现这几天火柴用得飞快。火柴放到炉灶边,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时候农村习惯称火柴为“洋火”,以为那国产的火柴也是进口的。
“娘,我没见。你去问我二哥。”我说。
我是有一把用自行车链子做的“洋火枪”,但我一般都是诳小伙伴的火柴用,把火柴头上的药粉刮到“洋火枪”枪膛里,枪头放一根火柴棒,扣动扳机,撞针撞击火柴药粉,就能“叭”的一声,把火柴棒射出去。晚上,我才发现二哥也用自行车链子自制了一把大号的“洋火枪”,把刨来的子弹剥掉外层,放在里面打着玩。我看见他打过,效果很差,那子弹根本没力量射出去。十四五岁的孩子了,他还和我们小孩子一样玩那东西。
母亲知道了,把二哥的“洋火枪”放进锅底下烧了。
“我警告你,你以后少在咱娘面前告我状。听见了没有?”二哥用手指点我额头说。
“你别做啊,别让咱娘怨我啊。”我腆着胸脯回顶一句。
二哥气哄哄地推搡了我一把,我一倒,后面是一个土堆,绊倒了,气得哭着找父亲。一会儿,我又听见父亲和母亲打起来。
“是军干的,你怎么怨收。你看你养了些什么孩子?上学不争用,还净给我添麻烦,我整天跟在后面擦屁股。”父亲在向母亲发火。
“我养的孩子不好,当初你别和我结婚啊。孩子不好,你怎么不管?你不也是把气往那俩孩子身上泄?”母亲也火辣辣地。
“你让我怎么管?上次保财推车子故意把车子推到沟里,让生产队扣了我两天工分,我回来说了他几句,到现在还不和我搭腔,你让我怎么管?”父亲话音也拔高。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烦死了,锅里耙菇都糊了。”姐姐毕竟是女孩,在这个大家庭里一直充当和事佬。
二哥下了学,白天睡觉,夜里行动,常常老鼠一样昼伏夜出,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这还不算,还让我碰到过更为尴尬的事情。
老槐树东南是鬼的好自栽的一片梧桐树林,长得挺拔秀丽,枝叶繁茂,每到了春天,鬼的好就捡粗大的刨出来,去市场卖树苗,留下小的长着第二年再卖。这里也是很多家禽的栖息和交配之处,里面公鸡、母鸡亲热地偎依在一起,或者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唧唧”叫着翻开树叶找虫子吃。狗也经常来凑热闹,特别是夏天,跑进来乘凉。我经常到那捡鸡粪,一会儿就能满瓢。
小学四年级的秋天,我照例提着三条绳吊着破瓢到处转悠捡鸡粪,不知不觉钻进了梧桐树林。我不想惊动那些母鸡,我想悄悄地靠近他们,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惊喜,以前我就在里面捡到过几个鸡蛋。树林里好寂静,只有秋日午后的太阳慵懒地斜射进来,照在地上映出斑驳的树影。圆圆宽大的梧桐树叶掉在地上,踩上去软软的,很舒服。
突然,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女孩躺在铺满梧桐叶的地上,微微鼓起的胸部穿着淡黄色花格褂子,头上束两个小辫子,向后翘着,头下枕着厚厚的梧桐树叶,眼睛半闭着,脸色绯红,小嘴张着微微娇喘,下身裸体,露着白白滑腻的大腿,裤子堆挤在脚踝处,白皙平展的小肚子下面隐私处还没长出阴毛,有点高高的白白的,和小肚子融洽地连成一片,能看见那下面很嫩的红色的神秘。她的身上用胳膊撑着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肉红色的小弟弟硬硬的,外面包着的那一层皮还没有完全褪尽,半包着那小弟弟的头部,直挺着对准那神秘处试探着插去,看来是紧张或插不下去,他很笨拙地一次次撅起退下半截裤子的屁股,一次次插下去,可就是插不进去。
“好了,该轮着你在下面,我在上面了。”那女孩睁开眼睛说。
就在他们交换姿势的时候,那女孩和男孩——我的二哥同时看到了我。我也认出那女孩是我们生产队会计的女儿。
我只记着他们两个同时惊讶地张大了嘴,以后的事情我一片空白。当我从麻木中醒过来,地上只剩下了那压得有点揉烂的像锅贴饼子样的梧桐叶。
很长一段时间,二哥都躲着我,吃饭的时候,偶尔有片肥肉,他也不和我抢吃了,要是以前,两双筷子在碗里像两条龙在搅动,谁也不让谁。最后母亲夹起来喂给弟弟了,我们才悻悻地罢手。
随着秋风落叶,懒懒地飘来大哥的一封信,这是他当兵快两年来的第二封信。
“秀明,念念听听,你大哥说了些啥?”母亲很兴奋。父亲正在做饭的堂屋里坐着马扎,细细地摘着刚刚收获的芫荽的烂叶和杂叶,准备挖个土坑埋起来,过年卖个好价钱。
“对,念一念,看你大哥怎么样了?人家松元村那姑娘还正等着哪。”父亲也很高兴。
“我在这里很好!你们不要瓜(挂)年(念)。现在在伙房干,吃的很包(饱)。我准备今年十二月回去叹(探)亲,趁叹(探)亲机会和她结昏(婚)。你们在家里准备一下。另外,我没有手表,给我买一块。”
大哥的信,开头没有称呼,信尾也没有署名,只是署了个日期,足见大哥对这个大家庭的怨恨。
“娘,大哥要回来了。说是回来结婚,还要块手表。”姐姐高兴地说。
“哎呀,太好了!你大哥要回来结婚了。这拖拉两年了,该结婚了。菩萨保佑!儿子要说媳妇了。”母亲非常高兴。
父亲听到结婚,脸上也挂着满面笑容。但听到姐姐念到“我没有手表,给我买一块”,那正摘着芫荽的手擎着芫荽在半空停住了。那年头,一块手表多少钱啊?结婚也要花钱哪。
父亲低头看看屋里的芫荽。
“唉!本来想留到过年卖个好价钱。”他轻声叹了口气。
十一月十日,飞水大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头戴破毡帽,手推小推车,车子的两边各放一个破席笼子,上面盖着破被子,艰难地行走在赶集的路上。路上冰冻很滑,他不得不把腰哈的更低,两腿叉开,小心翼翼地走着,有时滑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手上连手套都没戴,走一段路程,他不得不停下来,搓搓冻得发红的手,哈出的热气,凝结在嘴上,形成白白的胡子。
到了集上,找个摊位,他蹲着,可怜巴巴地指望着能有人买他的芫荽。
“老兄,芫荽不错啊!批发给我吧!三毛钱一斤怎么样?天这么冷,蹲在这里滋味很不好受啊。你快卖了,早回家暖和,你看你冻得这样子。”一个差不多大的菜贩子凑上来说。
“三毛?凭我这芫荽,至少四毛啊?不卖,我零卖。”父亲说。
那菜贩子悻悻地走了。
日到中午,父亲卖得差不多了,起身直了直腰,从车子上拿出一个书包,推着车子来到一个羊肉汤摊。
“老范,来一碗羊肉汤。”父亲和他是老熟人了。
“哎哟,仕途啊,又卖上了。来喽,来个火烧吧?”老范说。
“不用了,我自己带的煎饼。”父亲说。
每次赶集回家,父亲把那些破碎的油渍渍的黑糊糊的零钱仔细地数一遍,小心地放好。
“40块了,差不多了。”父亲叨念着说。
年底,大哥回来探亲了。穿着军装,英俊潇洒,真不亚于斯诺当年在陕北给毛泽东拍的相片上的模样。
“保财,看这表怎么样?你对着收音机调好时间,我不会上弦。”父亲喜滋滋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这是父亲托本村在外面干供销员的王余水给买的。
大哥打开一看,亮闪闪的,是北极星牌的。
“好,这手表不错!”大哥赞叹说。没来得及调准时间,就戴在了手上。
一年后,也就是1981年,大哥复员回来,又和嫂子住进了父亲和五叔及亲戚帮忙盖的新房子,虽然是土房子,父亲已经尽力了。
分家时,碗、筷子、粮食各一半。
“叔,大哥就两口,我们六口,还对半分,这太不公平了吧。”我不满地说。“你看,囤里就这点粮食了。”
“你孩子懂啥?我对你大哥十分,才不赚别人说,这还不一定赚的好。可对你三分,没人会议论我。”父亲说。
刚刚分开家,四叔回来了,这天也巧,二姑也来看父亲。二姑一家自1958年移民到吉林后,忍受不了那里的严寒,前两年又迁回牟山水库了。表爷爷又重新给二姑一家盖了房子才安顿下来。
中午刚放学回家,就看到母亲在炒菜。
“娘,谁来了?”我问。凭我的直觉,一定是有客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