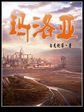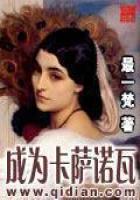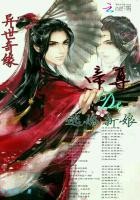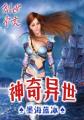鉴真的到来,将唐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得日本对大唐的崇拜之情上升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并非夸张。
之前就说过,在孝谦上皇摄政时代,朝廷曾经把所有的官制都一一对照,并起了相应的中国名(唐名),其实据说当时还有人提出不但官位要用唐名,最好人名也改成唐式的,好在女皇大人冰雪圣明,当场就给驳回了,不然用不了多久,整个平城京里头就该遍地走着李家的人了。
改名还只是其一,接下来说其二。
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十月二十二日,桓武天皇下令迁都,把京城从平城京搬到了山背国北部的葛野,然后把山背国改名为山城国,接着又将葛野改称平安京。
着名的“平安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山城国就是今天的京都府,平安京大致就是现在的京都市。
就这座城市的本身而言,堪称是唐文化,尤其是唐代建筑文化在日本的极致体现。
平安京的内部规划构造严格仿造了中国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西侧仿长安,东侧仿洛阳,基本上就是两城的等比例仿照版。不过后来西侧废弃,因此实际上的主要市街只剩下了东侧的洛阳部分,故而人称小洛阳,在古时候的日本,去京都也被叫做“上洛”。
直至今日,“洛”仍是京都的简称,那里不但有“洛阳交运”“洛阳堂”,还有一家名为“洛阳工业高校”的学校,着名影片《御法度》(北野武主演)的导演大岛渚,正是毕业于此。
不过当时日本大都市规划仿唐并非稀罕事,几乎可算得上是惯例,国家首都更是如此。但关键在于,自打迁都平安京,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千余年里,日本的首都都不曾挪过地方,不管国家闹腾得多厉害,京城永远是这一亩三分地,天打雷劈海枯石烂也不动摇。
为什么?
我们在上一本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日本历史的大致进程,也知道日本古代的主要政治中心要么在九州,要么在奈良,最次也在大阪,京都一带在那个时代尚属待开发地区,平安京所在的那个位置更是一片荒芜,堪称不毛之地,可为什么桓武天皇偏偏就要在那里建都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平安时代之前日本的首都一直在变,迁都从来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但不管迁到哪,首都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点却从未改变。而平安时代之后,虽然日本的首都被定格在了京都长达一千年,可国家的政治中心却并非一千年不变地都在那儿,比如丰臣时代的政治中心在大阪,德川时代在江户,等等。至于京都这个地方,到了后来纯粹就成了皇城,只是一个供天皇居住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因为半仙天皇的存在,仍然是国家的首都,并且颇具神圣性,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那个天皇沦为象征乃至傀儡的岁月里,堂堂一国首都却不再是政治中心了,甚至几乎和国政都失了缘。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都这样了为什么还不迁都?
从历史经验来看,“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勾当很明显是应该把天子挟在身边才好掌控,可后世的众多日本实权统治者,既没有自己跑去京都执政的打算,也似乎并不准备让天皇迁都到镰仓或是江户(当然天皇本身也不肯),这又是为什么?
换句话讲就是,为什么古代日本人在国都方面会如此执着于京都这个地方?
个中的理由,说得铿锵一点,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说得玄乎一点,是因为那地方的风水好。
但不管怎么说,平安京的脱颖而出都和中国文化有关。
桓武天皇迁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是光仁天皇的儿子,也是天智天皇的曾孙,不过在他继位之后,天智一族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了。虽然他贵为天子,可当时整个平城京乃至整个大和国(今奈良县)里都没几个肯听他的,各路豪族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对中央朝廷置若罔闻,一副无所谓有无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就想到了搬家,预备换一个环境再换一套班子。
新都城的地点一开始被选在了山背国的长冈,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府的向日市附近。那地方算是当时山背国那一片里头最繁华的了,从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开始,秦氏一族就奉了天皇的旨意,在那里搞开发。
本来迁都长冈这事儿已然是定了,连长冈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长冈京,可就在桓武天皇都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开路的当口,意外发生了。
简单说来就是在搬家前大和国发生了一场地震,接着周围又出现了饥荒,遍地饿殍都还没来得及埋下去,滔滔洪水又席卷而来,等到洪水退下,大伙都以为灾难到此为止,谁知道瘟疫又蔓延了开来。
和瘟疫一起四散的还有谣言,整个奈良国上到朝堂下至江湖,都流传着诸如天皇失德,没资格当天子之类的说法,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桓武天皇当然就吃不消了,众所周知,日本的天皇主要是以“神威、神德、神道、神迹”服众,结果现在却弄得天怒人怨,如果不想办法来弥补的话那肯定要出大事。
所以他就问群臣,该如何是好。
大臣们很想说你问我我问谁,毕竟是天灾,你问人怎么办?人能怎么办?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正在长冈京搬砖的秦氏一族收到了风声,于是他们立刻派了个家族代表赶回了平城京,面见桓武天皇,然后告诉他说,之所以会发生这一连串的天灾,是因为妖魔作祟。解决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弃用长冈京,另寻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当新首都,以镇压魔物,顺便保国泰民安皇朝万年。
天皇似懂非懂,但见那个姓秦的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便也跟着不住地点头,一副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总觉得好厉害的模样。
他主要不太明白什么是风水,虽然这对于桓武朝的日本而言,并非是个新概念。
早在飞鸟时代,风水学说就从中国传入了日本,只不过因为列岛本土的神道教根深蒂固,加上佛教深入人心,所以风水在列岛一直都是非常小众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即便是奈良时代遣唐使大规模来往于唐日之间的时期,风水学的普及也仅限于中国移民和“知唐派”日本人之间,对于广大的其他日本人来讲,仍是非常陌生的一个词。
不过,作为当时屹立于整个渡来人集团之首的秦氏一族,当然是精于此道的。
他们告诉天皇,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观察经验,如果真要迁都,那么新首都最好是造在葛野那里。
桓武天皇忙问为什么。
那位秦氏成员则反问道:“陛下,您知道四圣兽吗?”
天皇点点头又摇摇头,表示自己听说过,但并不知道具体。
“四圣兽指的是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他们分别守护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天皇说这个我懂,从飞鸟时代的时候起,但凡造宫殿,东西南北必定会竖起画有四神兽的旗帜,用于守护。
这是实话,虽然那会儿风水学的概念普及率很低,然而四圣兽在皇亲贵族中却一直被频繁地使用着,除了上述造宫殿插大旗之外,还主要体现在权贵的陵寝里头,比如在据说是天武天皇的某位皇子,或是奈良时代高官的高松冢古坟和龟虎古坟中,就有画着四圣兽的壁画。
只不过,让桓武天皇感到奇怪的是,这四圣兽跟新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什么关系?首都不管选在哪,旗子不照样都能竖起来吗?
秦家人摇了摇头,表示话不是这么说的:“唐土的风水学博大精深,绝非仅限于插旗壁画那么肤浅,事实上风水这样东西本身就应该要跟自然地理环境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恕臣下直言,先代的那些插旗作画的表面功夫,虽不能说是无用之举,但比起前者终究还是差了一截。”
此言倒也不虚,就好像如今造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固然也有讲究,但整栋房子到底造在哪里,是靠山还是靠水,是坐北或是朝南,显然更被关注。
天皇虽然觉得秦家人的话说得挺有道理,但仍是不明白为何首都要在葛野:“葛野之地的风水很好吗?”
“是的。”秦某点点头,“之前臣已经说过,四圣兽分别守护四个方向,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栖息之地。青龙住在川流,朱雀栖于湖沼,白虎位于大道,玄武则在山陵。葛野那个地方,青龙位上有鸭川,朱雀位上是巨椋池,西面的白虎位是山阴道,北面有船冈山,四方正好完全对应,从风水上来讲,堪称完美,所以我们秦氏一族都认为,那里才是新都城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