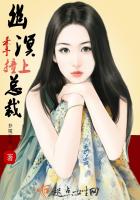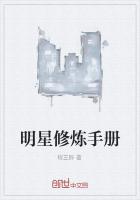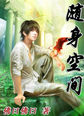主人公开着一辆白色小车出现在画面上,依旧是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形象,但目光明亮,嘴角紧抿,完全不是那副罗哩八嗦神叨叨的模样。
停好车,开门下车,正好见到前方有女人倒下。
一名长裙女子好端端地倒到地面上,不省人事,顿时引来路人驻足围观,男人也开门下车瞧热闹。
一名自称医生的男人摸了摸女人的脉搏,下结论道:“没事,低血糖而已,多吃点胡萝卜就好了。”
男子道:“大家帮个手,让这位女士到我车里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围观者七手八脚将女子抬进了男人车内。
男人回到驾驶座,正犹豫下一步该怎么办,身后女人坐起身来,满面幽怨地说:“你刚才摸了我的脖子,感觉很舒服吗?你们这种男人啊,怎么总是这么无聊,我躺地下关你什么事嘛,要知道,我已经站在那街口整整一天,就为等那医生,唉,好事都让你给砸了……”
男子闻言,无语回头看前窗,看着看着,眼眸突然放出惊讶的光泽。
道路那端,一名身穿白色风衣的男子正朝他缓缓走来,不正是刚才那位医生吗?
那医生越走越近,皮鞋踩在石子地面上,悄然无声……不,那医生的鞋底根本没沾着地面,整个至少悬空五公分。
再回头车后座看女子,身子倾斜,左臂撑着脑袋,嘴里还在嘟嘟哝哝的唠叨着些什么。
特写镜头,女人的臀部、腰部……整个身体都没有挨着坐垫。
结尾画外音,依旧是那女子不停抱怨的嘟囔声。
五、天堂电影院
接下来十多个故事均是如此,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角色,演绎出与银幕正面完全不同的故事,看得我啧啧称奇。
《巴黎我爱你》放完片尾字幕后,我本打算起身告辞,不料银幕紧接着上出现了“20世纪福克公司”的标志,英文字幕打出片名《巴黎最后的探戈》,刚见过马龙白兰度的中年版,片子又是英语对白,这样又钉住了我的屁股。
我还记得,马龙白兰度在这部电影里塑造的保罗,是一名潦倒颓废而流浪到巴黎的美国大叔,一天,在小巷里偶遇一名法国姑娘,两人一见“钟情”,实际上,那女孩是一名电影演员,因在片场里找不到角色感觉,特意到大街上寻找灵感。
女孩找到了保罗——他们躲在一间旧屋里疯狂做爱……整部片子充满令人血脉喷张的情欲镜头——这是我愿意多看一遍的原因。
欢愉之后,女孩开枪打死了男人,面对前来调查的警察,做出一脸无辜——“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跟踪了我,强暴了我。”
银幕后面演出的情节大致差不多,不同的事,保罗并不潦倒,他是一位美国富翁,到巴黎公干,因为无聊而上街寻找刺激的。
银幕后还有一个特别结局:姑娘杀死保罗后,回到片场,导演对她说:“你被解雇了——你杀死了而我们的投资商,电影没法拍下去了。”
看得我哭笑不得。
再接下下来,是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全世界铁杆影迷的最爱,一部只为影迷打造的致敬电影史大师之作,我又怎么舍得错过?
奇怪的是,这部电影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银幕前后的情节都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不同之处,是电影在进行到一半时,表现观众看电影的表情时,竟出现一张中国人的脸,而且,那张面孔很眼熟……似乎有点像我哥哥。
三部电影看下来,外面天早该亮了吧?我竟然丝毫不觉得疲倦,倒是戈尔茨提醒我:“天亮了,我们也该出去走走,活动活动。”
我跟在戈尔茨身后,向银幕旁的幕布走去,掀开帘子走出门洞,眼前豁然一亮。
炫目的阳光几乎让我晕厥,但真正让我欲欲想倒的不是阳光,而是眼前的场景。
我不是从地下室放映厅前台走进后台的吗?出了门洞应该回到银幕前才对啊。可我眼前竟出现一个户外小广场,周边都是一些低矮古旧的建筑物,建筑造型完全不是法国风格,倒像是一个意大利小镇,广场上来往的人们都穿着上个世纪20年代的服装,听听他们的交谈,一句不懂,但可以肯定不是法语,从舌尖灵活的弹跳音来判断,应该是意大利语。
回头看看我们刚走出的门洞,却是一幢小剧场大门,看着怪眼熟的。
等等,这,这不就是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小镇电影院吗?
看着我惊诧的神情,戈尔茨很从容,他拉住我的胳膊,说:“别紧张,出口在这边。”
我被半拽半推地穿过广场,穿过一条小巷,小巷尽头有一扇小门,门上挂着灰色布帘。挑开门帘进门,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我们回到了左岸咖啡馆的大厅,有贪婪猫图案的挂钟时钟指着八点,门外阳光灿烂,塞纳河上游船穿梭。
我们坐回昨天互相认识的座位,我想给自己叫一份三明治做早餐——虽然肚子一点不饿。
服务生竟对我的呼叫充耳不闻。
“别叫了……他看不见我们。”
“说啥呢?吓人。”
“哈哈,不吓你……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一名……怎么说呢,电影鬼魂吧,与马龙白兰度的保罗一样,因为电影反复放映而被困在这里的游魂,不同的是,我只是《戏梦巴黎》中一名匆匆路过镜头的的路人A,连个角色姓名都没有,戈尔茨是我做临时演员时领薪水用的名字。而此刻,您——尊敬的散客月下先生,昨晚上,一不小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什么?”我大吼大叫起来,身边顾客、服务生、路人,谁也没看我一眼。
“您别激动,激动也没人看得见您——我是说,从此之后,只有真正的铁杆影迷能看得见您,就像您能看见我一样,您现在已经是《天堂电影院里》的一名观众。”
一位黑人小哥光着膀子走过。
一对情侣互相亲吻着前行,白种人,不明国籍,这对忘情恋人,完全不知道他们身后跟随着一名中东肤色的小男孩,一看便知是小偷。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太太牵着七条狗,狗们大小不一,品种各异,人狗同行于人行道上,看不出谁遛谁。
理发师的女儿
上世纪初的神秘故事。
茫茫大海上,中国女孩邂逅欧洲贵族……逃过一场灾难。
外一篇《江南女子》:汉学教授离奇死亡事件。
(一)四等船舱
我叫陈玛丽,西历一九二零年,我出生在大不列颠国南安普敦一个华人理发馆里。
我父亲原籍福建,靠祖上传下的剃头手艺维持生计,宣统三年,大清国覆灭,汉人割辫子后前额蓄发,剃头生意因而一落千丈,后来,遇上不列颠国与德意志开战,民国五年,不列颠人到中国招募华工充当士兵,应征者都要剃光头,我父亲被洋人请到船上给华工剃头,那一船华工至少有一千多人,我父亲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还没完工,累得昏睡在船舱里,等他醒来时,轮船早已行驶在茫茫大海上。
就这样,我父亲糊里糊涂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参加战地救护,结识了我母亲,一个出生在南安普敦的英格兰护士,战争结束后,两人结婚生下了我。
我们一家人在南安普顿定居,南安普敦是一处天然避风良港,许多远洋货轮都在这里停泊。父亲开了一家理发馆,母亲在教会医院工作,父亲在他的顾客引导下,学会了投资股票的生意,开头几年也赚钱少,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转眼间我长到了十八岁,西元一九三八年,欧洲大陆布满战争阴霾。经济危机席卷英法,我父亲投资在股票上的资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还欠下了大量债务。
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毕业,出落得如花似玉,在小小的南安普顿算得上一个出名的美人,远近小伙子争相向我献殷勤,就在我从容选择情侣,预备恋爱时,父亲把我卖掉了。
父亲为了解脱经济困境,承诺远在美国的一个亲戚,把我嫁给纽约一个华人富商的儿子,我看了照片,那小子有一张很不讨人喜欢的圆脸蛋。
不顾我的眼泪与反抗,家人匆匆将我推进“利物浦号”的四等舱里,让我孤独一人,启程前往美国。
(二)甲板邂逅
“利物浦号”也许是当时往返大西洋两岸最破烂的客轮,没有酒吧、咖啡馆弹子房,除了大餐厅外,没有任何服务设施,四等舱塞满钢架床,乘客多是贫穷的犹太人、矿工牧民以及他们的家属,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味和臭烘烘的汗味、婴儿的尿臊味。
邮轮经过朴次茅斯海湾驶出英吉利海峡后,月亮挂上了夜空。我爬出船舱,走到在甲板透气。
甲板上没有灯,天空不见星辰,月亮从朦朦水雾中黯然升起,在黑漆漆的海面上推出一道狭窄的微波粼光,好像一条通向天边的路。
当时,我真想一头跳进海浪里,试试看这条月光小道是否可以通向天堂。
就在我伏在栏杆上,思索着要不要纵身跳进大海的时候,身后一道黑影向我移来,我依然低着头,看见一双镶满巴洛克图案的黑皮鞋正向我走来,并且很快定在了我的跟面,我被迫的抬头向上一望,看见一双深邃忧郁的蓝眼睛。
一个身材高大,脸庞清瘦的白人青年站在我面前,他一头短发,鬓角修剪得干净整齐,身穿旧式黑色西装,淡蓝色月光环绕着他的身体。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副高傲冷峻的神情。
见我抬起头,他垂下双臂,微微向前倾斜了一下身子,说:
“您不会跳下去,美丽的小姐,您拥有天使都为之嫉妒的容貌,美神为之倾倒的身材,您不该死去,而是应当获得永生。”
我凄然一笑,说:“永生?我已经被上帝抛弃了。”当父亲决定把我远嫁美国的当天,我曾在教堂祈祷一整夜,但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
“哦,亲爱的,看来您的确有些不幸——不过凑巧的是,我也是被上帝抛弃的人……难得咱俩如此同命相连,请接受我的邀请,跳一曲月光舞吧。”
说罢,他向我深深一鞠躬,然后拉起我的手,环住我的腰肢,带着我在甲板上转动舞步。
海浪拍打船帮的声音高一阵低一声,拍出了最美的音乐节拍。
“我是德拉库拉,世袭伯爵。”他在我耳畔低声说,声音充满磁性与魔力,令人迷醉。
很多年后,我都忘不了那个迷离的海上月夜,在年轻的德拉库拉伯爵怀抱中,我身心溶化,血脉喷张。
一片乌云飘来,遮蔽了月亮,我们停住了旋转,德拉库拉还不愿意放开我,反而把我抱得更紧了些,看样子他想吻我。
那一瞬间,少女的矜持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我轻轻推开了德拉库拉,莞尔一笑道了一声:“晚安”然后便逃离了甲板。
(三)有趣的伯爵
第二天晚上,我又在甲板上见到了德拉库拉,我们在月光下漫无边际的聊天,伯爵是一个有趣的家伙,口若悬河且彬彬有礼,一整夜,我都很小心地保持着与他的身体距离,他也给予了相应的礼貌。所以,我答应了他再次见面的邀请。
横渡大西洋实在是寂寞无聊的漫长旅程,有了德拉库拉这样的旅伴,旅途有了些生气。日子过得也快了许多。
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每晚见面,听他给我讲述中世纪的各种奇闻逸事,这家伙懂得真多,我想我已经喜欢上这个有魔力的家伙,但是,我依然不敢接受他的吻。
我是一名邮寄新娘,我身上担负着拯救父母生命的使命——虽然等待我的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婚姻。
每次告别德拉库拉,回到我的四等舱铺位上,我都彻夜难眠,夜复一夜,德拉库拉英俊的脸庞与照片上的未婚夫那张圆脸交映对照,令我满心纠结。
(四)战后余生
月亮缺了又圆了。
“玛丽,我真诚地邀请你到我的头等舱做一次客。”德拉库拉借着银色月光,再次向我发出了诱惑:“船舱不大,但里面有很舒适的、罩着羊绒套的坐椅和金丝绒床单。”
我们都知道,满月后的第二天,“利物浦号”将在美洲新大陆靠岸。
“答应他吧,就去坐一会儿,坐一小会儿,又能怎样?”我脑子里有个不乖的玛丽这样劝说我。
“好吧……”我迟疑地点点头,德拉库拉顿时满脸喜色,他冲我一鞠躬,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伯爵像照顾女王一般,引领我踏上旋梯,转过二层楼,来到一个有陈旧木装饰的门前。
我心跳得很厉害,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这扇门的背后,匿藏着一个事件,一个有可能改变我命运的事件……
就在德拉库拉弯腰拧门把手的时候,一个突然袭来的发现吓倒了我。我开始害怕了,腿脚颤栗。
德拉库拉闪身走进舱内,站在门边向我鞠躬施邀请礼。
我突然一把抓住门把手,往回狠狠一带,将德拉库拉反锁在门内,然后转身奔逃。
我逃回了四等舱,呼吸着空气中的劣质烟草味和臭烘烘汗味,我感到很安全。伯爵先生高傲,自命不凡,他是不肯屈尊走进我们这个下等人的世界里的。
第二天上午,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出现在海平线上,船到纽约了。
下船的人群中,没有见到德拉库拉伯爵。
我见到了我的未婚夫张承业,承业虽然不英俊,但还算个不错的丈夫,结婚后,我们生活得很安宁。至少,我得以逃避了德国人的轰炸……我父母亲后来死于德军对南安普顿港的一次轰炸中。
(五)辨别吸血鬼
其实,我真正逃避掉的灾难不是战火,而是吸血鬼。
在我到达纽约后不久,报纸上不时登出有神秘死亡事件,死者被某种巨型啮齿动物咬破血管,吸干鲜血。
警方追溯源头,查到了我所乘坐的“利物浦号”邮轮——轮船泊岸后,头等舱里发现两具女尸——被吸干鲜血的女尸。
我知道了,德拉库拉伯爵就是吸血鬼。
就在德拉库拉低头为我拧开门把手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伯爵先生的后脑短发与鬓角实在修剪得太干净了,而这船上根本没有理发馆,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经历了一个月航行后发际还这么整洁。
毕竟,我是一个理发师的女儿。
外一篇:江南女子
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
我的江南女子,就是这样从诗中走来,从画里飘来,吹拂着盛唐和风,滋润着宋朝细雨,掩映着明清圆月。
我是一个幸福的男人,依偎着垂柳绿杨度过了一生。
——这是法国汉学家路易·蒙贝尔为自己题写的墓志铭。
蒙贝尔先生一生没到过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古代江南诗歌》十三卷,同时还撰写了数十本汉学著作,在欧洲影响巨大。
蒙贝尔先生死于一次不幸事故——在他的书房里被书架上落下的书籍活活砸死。
两个月以后,厚重如山的书籍已经结满蛛网,尸首才被发现。
那些书籍,恰巧正是他毕生撰写翻译的汉学著作。
每一本书的装帧都异常精美,皮革的封面,骨质的书脊,
经警察鉴定,封面所用的皮革居然是人皮,书脊所用的骨料是人骨。
十三年前,路易·蒙贝尔曾经雇佣过一位来自中国杭州大学的女留学生做助手,那学生后来失踪了……
此案正在调查中。
推着小车到伊斯坦布尔卖番薯
伊斯坦布尔老市场上,一场致命危机即将爆发……
(一)新老城区
一切准备就绪,穆罕默德·斯塔法·易卜拉欣·赛义德走出家门,步履坚定稳健,目不斜视,一副义无反顾的态势。
伊斯坦布尔四月,春回大地,郁金香花顺着沿海大道南北延伸,阿泰佩山脚下盛开的几百万株郁金香艳丽勃发,色彩夺目。
赛义德走在大道上,花香扑鼻,夹杂着少许泥土与清晨的鲜草味儿,赛义德沐浴在花香之中。
一股异样的香味儿从郁金香芬芳中脱颖,直接钻进赛义德的鼻腔,这是一种比花香更馥郁的味道,香味穿透赛义德鼻腔,直刺中枢神经,小伙子实在禁不住对香味的好奇,停住了脚步,侧脸寻找香源。
正是旭日东升时分,博斯普鲁斯海峡海面上已经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海边埃米尔甘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