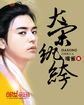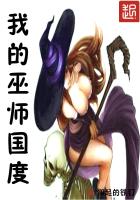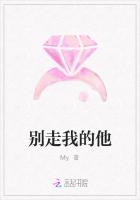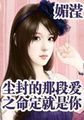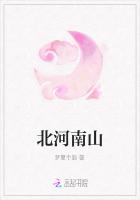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法·都德
母语的特点与语文教学
语文教育是指导青少年学习母语最具民族特色的教育,不管语文教育改革如何发展,但成功的语文教学总是建立在母语特点之上的。离开了母语的特点侈谈语文教学或改革,那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我们要成功地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必须首先研究母语的特点,以及在这个特点基础上所形成的系统有效的教学方法和优良传统。
母语的符号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形、音、义三结合的表意文字,这是汉语的第一个特点。汉字的象形字是构成汉字的基本部件。有些字到现在还基本保留其形象特征,有直接表意的功能,字本身就可以传达出意义信息。而且,大部分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简单汉字组成的合体字,掌握了较少的简单汉字,就能基本掌握大多数汉字的写法与读音。特别是占汉字80%的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体,它用形旁表示事类,用声旁——同音字表示字音。这一特点不但使汉字在人们学习和使用时能据义定形、据形度声,举一反三,以少驭多,提高效率,而且有助于学生智商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西方国家已有实验成功地表明:学习汉字可使人产生多种联想,治疗儿童“失读症”和提高老年人康乐水平。这种优势是其他文字所望尘莫及的。汉字从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3400多年历史,仍保持着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汉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但楔形文字在公元前第四世纪、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公元第五世纪都分别结束了它的生命,唯有汉字至今生机勃勃。
在人类进入电脑时代,汉字仍能在高度现代化的信息公路上畅通无阻。汉字是方块字,书写占用面积小,使用灵活,它可以横写,可以竖写;可以从左至右写,也可以从右至左写。汉语追求简约,言简意赅。有许多句子不用主语,甚至没有动词,甚至只有一堆名词而所写的意象清楚明白、生动感人。名句“鸡声茅店月”、“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汉字是世界上最简洁、最富有表现力的文字。
用汉字印刷的文件、书籍比用其他文字薄得多。1991年,一位学者在《汉字文化》座谈会上宣称:“汉字科学易学,是智能型的,国际性的优秀文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汉字不仅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书体斑斓、风格各异、具有和谐美、线性美、节奏美的书法艺术。这种艺术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词多义
汉语一词多义,由一个单音词的本义不断引申,可以派生出一串义项,并由它作为语素可衍生出一族词语。这是汉母语的第二个特点,由一个单音词派生出众多的义项和词语而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最简单的“一”,《现代汉语》里就有最小的正整数、同一、另一、全或满、专一等9种义项,并衍化构成了305个词语(包括成语)。因此,汉语词汇异常丰富,无论多么复杂的事物、细腻的思想感情,都有最恰当、最生动的词去表现。拿表示手的动作来说,汉语里就有100个以上的词语,如“打”、“拉”、“拨”、“扯”、“拍”、“按”、“抢”、“抱”、“扶”、“提”、“推”、“摇”、“揉”、“抓”、“拂”、“接”、“擎”等,它能精确表达与手相关的100多种动作。而且,汉语以字组词的能力很强。对新出现的事物,往往以有可解性的合成词去表现,不像英语等其他语言需另造新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以法治国”、“四有新人”、“一国两制”、“绿色食品”等词语就是例子,这些词都是根据原来的字、词或词素重新加以组装而成的。
富于形象性
汉语最富于形象性,能具体、鲜明、生动地表现客观事物和人的思想感情,含有丰富的神采和无穷的韵味。这是汉母语的第三个特点。因为汉语的构词也常用具体形象表现事物的特点,如灯泡儿、鼻梁、眼眶、木耳、佛手、榆钱、海带、砂糖、雪白、天蓝、杏黄等;而量词特别能表现被修饰的事物的形象,如一朵花、一缕烟、一阵风、一条河、一片树叶、一张报纸等;还有成语、谚语、歇后语,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抽象的意思,如百花齐放、万马齐喑、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等等;而且许多名言警句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富于音乐美
汉语最富于音乐美,这是汉语的第四个特点。汉语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汉母语的第一个音节即每一个汉字都有独特的语音结构,它一般不把两个辅音或两个以上辅音放在一起拼读,且一般将辅音置于元音之前,只有极少数的辅音如n与ng可以跟在元音后面。它的每一个音节多数可分为两段,前面的辅音部分叫声母,辅音的后面部分叫韵母。只有少数字没有声母只有韵母,如衣、爱、鹅等。由于声带是使气流乐音化的器官,发音时声带颤动的声音就是乐音;而元音发音时声带都带颤动,且又是每一个音节的一部分,所以每个字的读音都带有乐音。
其二,汉语具有四声,古有平上去入,今有阴阳上去,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声调,或平或仄,平声“如击钟鼓”,仄声“如叩木石”,文章读起来具有高低起伏、抑扬顿挫、长短徐急的特点。杨振宁先生说:“中国字有平上去入,这是西方文字里没有的。平上去入使诗句对仗、音节铿锵,这是西方的诗里没有的。”因此四声是形成汉语音乐美的一个条件,也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一点在古代诗词赋及对联里表现尤为突出。
其三,汉语里有大量的双声词、叠韵词、重迭词,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具有一种和谐美、韵律美,极富艺术情趣。朱自清先生就是善于运用双声词、叠韵词与重迭词的高手。这也就是他的《荷塘月色》等散文成功的秘密之一。单以重迭词而论,这一篇散文里写了“蓊蓊郁郁”的树,“曲曲折折”的荷塘、“隐隐约约”的远山、“脉脉”的流水、“静静”的月光、“薄薄”的青雾、“田田”的荷叶,共有了25个重叠词。此外还用了“袅娜”、“仿佛”、“斑驳”与“宁静”、“独处”、“苍茫”、“零星”等10多个双声词与叠韵词。这样,就使文章悦耳动听,韵味无穷。
千百年来,正是母语的这些特点,在母语的教学与运用的实践中,才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这主要有:咬嚼法、诵读法、涵泳法、文道统一、多读多写与多思的统一。这些方法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1.咬嚼法
咬嚼法,即咬文嚼字法。咬文嚼字是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传统的语文课尤其是这样。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备读写听说的能力。如果忽视甚至抛弃了咬文嚼字这一特点想达此目的,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通过咬文嚼字,才能使学生对每一个字、词达到会读、会写、会讲、会用,从而有意识地、大量地积累词语,并按其一定的特点、结构、用法,引导学生进行梳理、编码,找出一定的规律,贮存于记忆仓库,以备随时提取运用;同时,在阅读中咬文嚼字,经过反复比较辨析、思考,才能沿波讨源,披文入情,增强语感,引导学生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进入作者营造的特殊语境与特殊意境,体味某一词语在特殊语境中的表层意义,隐含意义或弦外之音,从而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依依”不单写表层的“杨柳之态”,而且写出深层的隐含的“离别之情”;同样“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又有晴”,“无晴”与“有晴”,不单写出浅层的天气的变化,而且含蓄写出了因爱之深对恋人情感微妙变化的感受。在写作中,对语言的锤炼、推敲和选择更离不开咬文嚼字。古人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讲的是为了获得名诗佳句,达到出语惊人的语言功力,必须咬文嚼字以至到了“性僻”的程度;“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讲的就是古人咬文嚼字所下的苦功和付出的代价。“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为敲定一个“绿”字,费尽了心血;“僧敲月下门”,贾岛为选定一个“敲”字,也几乎将“胡须”全捻断了。
2.诵读法
诵读法亦是体现我们汉民族语文教学特色的传统之法。此法要求对课文,尤其是对诗词散文进行反复吟诵、朗读、背诵,以至烂熟于心,背诵到“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的地步。诵读法与涵泳法不同,就在于诵读更重于“声”,涵泳法更重于“意”罢了。通过诵读,使之书声琅琅。这是学校的特点,更应该是语文课的特点。诵读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通过诵读,理解了思想内容,感受到文章的气势,领悟了文章遣词造句之功,谋篇布局之妙。通过诵读,能够沟通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使学生培养语感,积累语言材料,提高表达能力。这是因为,通过诵读,不但能理解和掌握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领悟汉语言的和谐之美、韵律之美和音乐之美,而且可以在“喉舌筋肉下留下痕迹‘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到“自己下笔时,喉舌也自然顺着这个痕迹而活动,所谓‘必有句调奔赴腕下’”(朱光潜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为什么能“不会吟诗也会吟”?原因就在于此。早在40年代叶老就批评过那种忽视吟诵法的倾向。他说:“现在的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论的研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下的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现在,这种倾向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比40年代更甚了。学生在语文课上放开喉咙读一阵书,达到“人声鼎沸”的程度,教师也领着诵读,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鲁迅先生描写的这种师生“入情入景、物我两忘”的读书情景已很难看到了。统治着课堂的仍是以教师为主的讲析模式。这是违背母语特点的。中国古代幼儿教科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之所以历数百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音节整齐和谐,韵律优美,琅琅上口,易于传诵,充分表现了母语的特点与优势。
3.涵泳法
涵泳法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语文教学法。此法为宋代朱熹所大力提倡。我国古代语文教学向来注重对文章的整体观照。涵泳法即是整体观照法。所谓涵泳,即沉浸其中、深入体会的意思。与朱熹同为宋代理学家的陆象山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这种方法的特点和过程:“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意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需要急思量。”它的过程包含三点:一是从容诵读;二是进入语境;三是体察领悟,增强语感、文感。一言以蔽之,此法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直接体悟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方法,避免了支离破碎的繁琐分析,使文章失去了生气与活力,而以整体观照综合理解把握主旨作为起点和落脚点。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诗词、戏曲、散文的教学。清代学者曾国藩曾称涵泳为“最精当的读书之法”。
4.文道统一
文道统一是我们母语教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它是我国数千年来语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语文教学中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的科学总结,它符合语言文字与思想内容不可分割的实际,又符合教书育人的基本原则。它集中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又揭示了语文教学的特殊规律,对语文教学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继承。但这种继承必须建立在对“文”与“道”的辩证的理解之上。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将“文”与“道”二者割裂或对立。古人云:“道非文不著,道非文不生。”应该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怎么‘统一’呢?统一,不是‘文=道’,不是‘道=文’,也不是‘文+道’,应当是文中有道,道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掣肘,互相干挠。”(张志公语)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车失一轮不能行驶,鸟失一翼不能飞翔。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能成功地运作。当前语文教学上,往往不少问题的争论都是与此相关的。比如,对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各自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语文属工具性学科,在语言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是语文课的首要任务,但同时要认识到语文却又是人文性、思想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乃是语文教学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种教育“必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样,才能使语文和“人文教育”达到“适度”。这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也就是文与道的统一。
5.多读、多写、多思
多读、多写、多思。语文贫乏是形成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多读是古人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们主张博学审问,穷经通史,通晓诸子百家。不仅要多读,而且要熟读,以至达到背诵。如老一辈作家不管是鲁迅还是郭沫若,是茅盾还是叶圣陶,他们无一不是在“读功”与“背功”上花了巨大的精力与时间。
鲁迅在少年时代,背诵的任务很重,要求“月月清”、“年年清”,即月底要背一个月里上的课文;“待到年底,就要把一年里上的课文全部背下来”。
(林贤治《人间鲁迅》)
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言语材料,为“多写”奠定了基础。“多写”除练整篇文章之外,还进行“属对”训练,方法是所对的字数由少到多,先一字对,二字对,然后三字对以至多字对。如“天”对“地”,“雨”对“风”,“暮鼓”对“晨钟”等等。直到1932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招生拟定的语文试题,还有出句为“孙行者”这个对对子的试题。这是一种符合母语特点的高度综合的语言训练方法。既是字、词、词组和句子的训练,又是音韵、语法、逻辑的综合训练。然后再从这句子训练过渡到篇章训练。封建教育很重视文章训练,但到明清以后,文章训练就成为八股文的训练了。八股文虽然不足取,但它强调多写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此外,还要强调“多思”,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审问、慎思、明辨”,要让学生自己去体会、玩味、顿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一旦豁然贯通焉”,由知识迁移为能力,以至走向创造,因而中国才产生《离骚》、《红楼梦》、《阿Q正传》等震古铄今的艺术精品,和数以万计的如屈原、曹雪芹、鲁迅等举世闻名的语言巨匠。
回到母语温暖的怀抱
有没有一种专属于我们心灵、情感、思维和生活的表达方式,能够跨越地域的界限,疏通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脉络?或许只有她——汉语,我们的母语。热爱传承母语,在这习惯了颠覆的训代,的确道路艰辛。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融入这片涵养我们精神的土壤。更何况,教授母语的语文教师——传薪之责,心在其中。优秀教师应永远记得,决定学习质量的是人,不是方案。因此,语文教师,对母语该有怎样的敏感与审美?该怎样趁早为儿童的母语发育打下“黄皮肤、黑头发”的精神底色?或省说.该怎样让儿童知道母语的好处,高高兴兴地做一个说中国话,读中国文字长大的人?
请敞开怀抱,品尝母语的味道,体会母语的性情——给自己一个机会,感动于母语,感恩于母语。让我们面对世界,用汉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