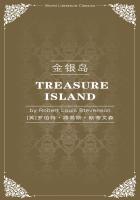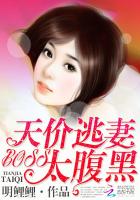混乱与困惑
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新锐分子对于欧美思想文化怀有景仰和遵从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之后,他们开始转向不信任,并且有意识地抵制西方了。在此之前,有关欧美的政治制度、经济方式、思想文化以及所有的一切,几乎都被看作是先进的,值得效仿和借鉴的。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共和制度,实际上就是对欧美宪政的模仿,直接拿来的,就是美国式的模版。虽然很少有人对宪政和共和有较深入的理解,不过他们仍笃信这种政治方式,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世界上的迅速崛起,主要是因为有着一个极先进的制度。可以佐证的还有日本,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日本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猛崛起,同样是因为他们拿来了西方的制度。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制度是灵丹妙药,只要改弦更张,中国就能很快改变落后面貌,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与中国处于相同境况的,还有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同样是全方位的——从政治与文化思潮来看,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主和宪政的思潮还占据着人类精神追求和社会变革主流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北方大国苏联在短时间内树起的样榜,以形成对这种思潮的挑战。即使是始作俑者的法国和美国,都对制度显示出很多不自信来。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原先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中间道路,是喝不醉淡啤酒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苏俄的社会主义试验,现在也开始不自觉地向左转了。
美国富有名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更是竭力推崇共产主义。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又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读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作,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着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
欧美杰出知识分子都如此不自信,更可以想象中国的情景了。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影响着中国人对于突如其来并且一直“夹生”的宪政制度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失望于大洋彼岸引进的代议制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制度的扯皮与低效让人失去信心和耐心,而跟中国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有着更多相似的俄国所诞生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适合于中国的。当然,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而言,五四运动之前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多半还不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内容,以社会革命为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当然,长期苦于专制和武力之害,渴望和平与平等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暴力、专政等等,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于俄国社会主义最难接受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这样的社会心态,决定了多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程度的戒备和警惕。受欧美资产阶段宣传舆论的影响,人们相信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残酷,而且过于专制。不过,中国面临的现实处境,很快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看法——巴黎和会上美国的态度,被更多中国人看作是对中国的背叛。在此之前,美国提出的“自由平等”、“民族自决”口号一直受到中国知识界欢迎;美国在光绪年间主动退还庚子赔款两千九百万美元用于中国教育事业,被很多中国人看作神话。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提出并始终主张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也使它赢得了超乎寻常的亲和力。很多中国人因而对陌生的美国产生好感,甚至把美国想象成童话中的救世主。辛亥革命后,中国全盘拿来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基于对“美国神话”的笃信。然而,巴黎和会上美国的态度,使得多年来堆积起来的公平正义的美好形象一夜之间像沙器一般坍塌,美国就像一个被扯破了画皮的骗子一样,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以前吹捧过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的陈独秀,这时候也奋笔疾书,痛斥“威大炮”背信弃义。陈独秀态度的转变,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态度。年轻的毛泽东也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否定美国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着新的偶像,而俄国革命以及俄国的做法,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个空白。穷途末路之中,不由得人们不相信背水一战的革命了。
现在,该谈一谈那个北方大国对于中国的影响了。如果说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备受欧美列强以及日本欺压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更是受到两个国家的钳制,那就是日本和俄国。对于北方大国俄国来说,对于将领土延伸到温热的亚热带,一直有着野兽般的渴望。这不完全是气候的考虑,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当俄国重心慢慢向东扩展的同时,它的注意力也向着东南扩展,如熊罴一样虎视眈眈窥视南方温热的土地。1901年,当清国屈辱地与联军们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各国陆续将自己的军队撤出,只有俄国按兵不动,盘算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他们甚至一直逼迫到清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病榻上。对于中国来说,这只凶猛而贪婪的北极熊就像是当年的蒙古,或者是入关之前的女真,而在某种程度上,它要比蒙古和女真更凶猛,也更贪婪。
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让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布尔什维克轻松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轻松取得了古老帝国的政权。通过十月革命上台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执政经验,一方面得面对陌生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还必须应付西方列强对于新生苏维埃的干涉。至少在1920年以前,新生的苏俄对于南方的中国,尚没有精力考虑战略上的布置与对策。直到所谓的十四国武力干涉失败,以及国内叛乱平息后,不再直接受制于西方围困的苏俄开始腾出手来,计划在世界范围之内寻找革命的火药桶,也寻找自己的帮手。苏联先是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在一些国家策划暴力革命,试图建立社会主义,以联合对抗虎视眈眈的资产阶级。不过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欧洲革命高潮低落下去,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先后被镇压,世界革命的火焰并没有像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所期望的遍地燃烧,而是不断遭到扑灭。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及时纠正革命初期就在西欧很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把眼光投向了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孱弱的东方,急于在此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这样,正处于转型动荡之中的东方大国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眼中的主战场。
可以说,苏俄对于中国的形势和格局是慢慢熟悉的,一开始,它对北京政府是陌生的,对于中国各政治力量,中国南北存在的两个政府——保守派、前朝旧臣组成的北京共和政府以及激进派、前朝旧臣组成的广州军政府,究竟采取何种立场也不清晰。在他们看来,北京政府虽然得到一些大国的承认,但其政治方针却不十分明确。应该视北京政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还是将其视为国际舞台上依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一个政府,因而是俄国潜在的盟友呢?俄国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然后才能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苏维埃俄国希望中国承认它,并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北京政府同样有一个观望和等待的态度。来自西方成员国的巨大压力,使得北京政府一开始没有与俄国签订外交关系,而是希望借助苏俄迫切建交的心理,谋取外交和领土上的利益,以挽回部分早期失去的领土和利益。因此,北京政府对于已经垮台的沙皇政权在中国的外交人员,仍进行承认和帮助,一直到1924年,北京政府才承认了苏联。北京政府对于苏俄的态度和行为,以及它背后的西方势力和理念,当然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于北京政府抱有浓重的敌意。在梳理清楚了中国各政治势力的关系之后,苏维埃决意利用中国复杂的矛盾,着手培养敌对势力,甚至以输出革命的方式,来对抗和反对摇摇欲坠的北京政府。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组织在莫斯科成立,意味着苏俄希望将革命推向世界,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中心。1920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指出:“共产国际的目标是: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性质上看,“共产国际表面上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都得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批准”。让列宁矢志不渝的是世界革命目标,就是要在落后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最终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也是列宁针对“威尔逊主义”提出的国际新秩序。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制定了东方战略,考虑有二:第一,出于在西方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希望的破灭的考虑;第二,出于远东边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考虑,主要使日本从它所占领的领土撤走,消除撤退到满洲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进犯威胁。
孱弱的中国夹杂在日本和俄国两个强国之间,就像夹杂在熊与狼之中的一头牛。双方虎视眈眈,一心想吃掉食物,同时也警惕对方的动态,力图占据先机。1919年7月,就在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饱受屈辱和悲愤之时,苏俄政府对华宣言,放弃旧俄在华侵略之权利及庚子赔款,并希望恢复正式邦交。这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由代理外长加拉罕署名,称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北方大国这一举动,让中国人激动万分,仿佛黑暗中发现了一些光亮,看到了真正的公平和正义。《钱江评论》上有一篇青年学生的文章是这样赞颂着俄国:“俄国人民啊!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在此之后的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声明八事:废除帝俄条约,交还各种权利,恢复商务,取缔旧党,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互派外交官。因为此声明仍由加拉罕署名,所以称为第二次“加拉罕宣言”。苏联的这一次宣言,再次引起中国社会群情激荡。后来的事实表明,苏俄对北京政府的示好,显然别有深意。在当时情况下,那些名义上准备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大都操纵在俄国旧党谢米诺夫和日本人之手,苏俄对华宣言的真实意图,除了示好,同时也激起北京政府采取联苏反日和反白匪的行动。到了1922年下半年,由于已基本收回这些领土,苏联申明的口气也相应发生了变化。11月6日,苏联在华全权代表向北京外交部申明,加拉罕两次宣言并非放弃苏俄在华之合法利益,该宣言亦非永久有效,除非中国不再漠视俄国利益,俄国或将不得不考虑其所给予之许诺。
苏俄两次“加拉罕宣言”表明的态度,经报纸公布之后,引得了全中国知识界的好感。尽管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太不同意在中国照搬俄国的做法,不过整个舆论界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已迅速“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已经有人公开欢呼起俄国革命来了,主张在中国也应该实行那“有人类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阶级的命”,革种种落后风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为的命。大批进步学生和青年学生,迅速地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力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主张中,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足以救国救民的理想出路。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人们的救国主张也日趋分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不由自主地“左转”,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坚定地自以为找到了另一条可行之路,不是回归传统,也不是模仿西方,而是走俄国革命的新道路。俄国革命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范例,那就是传统的农业专制社会怎样通过一次大胆行动一跃向前的突变。很多中国人乐观地以为,这是一种速成法,也是一种点金术。革命就像涅盘,只有先行毁灭,才能得到新生。对西方社会幻想的破灭,1911年之后对于西方宪政民主不愉快的体验以及俄国道路的警示,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才能成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中国陷入困惑和迷茫的同时,新成立的苏俄伸出强有力的手,迫切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飞越传统社会的愿望。《泰晤士报》的一篇新闻就说,来自北方的苏俄已经暗示中国民众,苏俄红军已做好准备,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戏剧性的直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