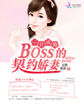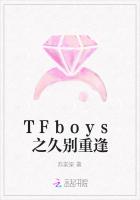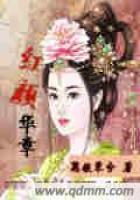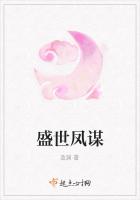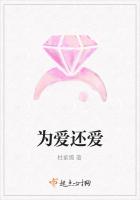无奈英雄
(小说)
题材类型:当代题材
题材范畴:都市,家庭,情感
故事核心:民事案件
写作形式:影视描述
故事发生地:中国东北百湖市
发生年代:2006——2015年
(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引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主角
人物简介
王一平:妈妈,45岁,会计,总经理。17岁时未婚先孕,“降格”嫁给了一个初中文化的木工师傅。性格特立独行,是个绯闻不断的女人。
简少东:爸爸,61岁,性格温和;话不多,图平静。
简亮:哥哥,33岁,新速路建公司技术部副主任。对外服从领导,对内服从妻子。
孙月:嫂子,31岁,邮局职工。
简阳:大姐,26岁,车祸后以轮椅代步。
简梅:小妹,25岁,新速路建公司局域网总监,真真假假,一切都写在脸上。
简单:小弟,25岁,简梅的双胞胎弟弟,保卫科工人,一个貌似混混实则单纯善良的年轻人。
刘锦华:52岁,心胸有点狭窄,新速路建公司总经理,简阳的生身父亲。
韩小凤:54岁,护士长,刘锦华的妻子,一个管不住老公也管不住儿子的女人。
刘唯军:25岁,简梅和简单的同学,刘锦华夫妇的养子,酒店领班,高大英俊。
赵可萱:26岁,简阳的同学,在刘、简两家的恩怨中,她是个局外人,也是个知情者,很多事可说可不说,岁月蹉跎间,赵可萱永远在徘徊……
徐发发:34岁,《纠纠报》记者,在他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死刑犯也曾经善良过。
刘小英:女警,徐发发同学。
第一章“魔鬼的尖叫”
1、二○一一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从桥上下来,刚拐了弯打算从前面的巷子里穿过去回旅店,一声比“海豚音儿”还要高八度的尖叫睛空霹雳般刺了下来——我吓得魂儿都没了,贴到巷子的墙上,身子僵硬。那个恐怖的声音再次叫起来时,我才听清是一个女人在喊“救命”——与其说这是一个救命的呼唤,不如说魔鬼的尖叫,简直是破了音儿的高分贝话筒,一下子散播到空气中去。那个声音象个魔咒一放一收,象要拨出我的心脏去。我伏下身子什么也做不了,眼睛也睁不开。随后我就听到身边有很多只脚往前跑。“杀人了!”“杀人了!”的叫喊不绝于耳。
先前的惊吓症状给这个气氛下的现场秒杀掉了,我突然站了起来,一边掏手机报警一边手登脚刨象打了鸡血似的挤进人群。呼救的女人披头散发躺在地上,脸只露出一小部分,惨白地对着路灯,身旁有一摊血。110,120很快赶到,设防护栏,劝离人群,送受害人上医院。警察问我话的时候,我心不在蔫地一边回答,一边盯着医生给受害人处理伤口。
“你说你第一个看到受害人的,可有人说你是后冲进来的,这是为什么?”
“哦……啊?啊,对,是我报的警。”我看都没看跟我说话的人……受害人有点面熟,不对,不仅仅是面熟……医生护士们动作迅捷,有条不紊;那个差点没把人吓死的受害人听到有人跑过来时就没再叫了,躺在那一动不动。昏暗的灯光下医护人员转来转去令她的身体一段一段地隔开、重合……
“你怎么听三不听四的?”我耳边又有人在说,“待会跟我回局里做笔录。”我扭头看了一眼一脸正气的小警察,“这可不行,受害人是我亲戚。”(这个谎撒的有点怪,我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小警察拿出对讲机叫他们的头过来,好象要抓我走。
这时,医护们用担架把受害人送去上车,小警察一个没看住,我就甩掉他冲过去,象“亲戚”那样帮着忙活,“我是她外甥,”我向旁边的医生说,又转向护士,“我是她外甥。”谎话变成了真话,他们不回答,也没阻止我上车。
那张对着路灯的脸令我愰忽;现在,这张脸离我如此之近,几尺远……时空的错乱,或是我的错乱,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场梦境中突然冲出的某些片断令人莫名其妙。
我有点兴奋,这个女人的又有故事来了,或者一直都有,只是我不知道。水泥钢筋造的屋子,楼上楼下都不知道谁是谁,断了音讯,照不着面也就真的断了。她是个例外,心里老存着一点愧疚,就老是在某些时候记起。多年不见,她还是那么年轻,一点没变。欧式的大波浪卷发把她的脸掩得小小的,很像出演了《潘多拉的盒子》的路易斯?布鲁克斯,一个中式的路易斯?布鲁克斯——看上去完全不象是结了婚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
一个人长相再出色,如果穿着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魏老师的衣服会是什么样?这个女人的性格,你打死她也不会穿成那样,衣服可以不值钱,但绝不能不合体,不能不时尚。
这样的与众不同,你可以把她想象成各种人,气质上你又无法断定她究竟是怎样的。
这会儿是七月中,正是热的时候,她穿着一条长过膝盖的绿裙,有领有袖,那种绿在120车里的灯光下显得特别耀眼;高跟鞋由几条流线穿插成一个花色,可能是漆皮的,我不太确定,很亮,也是绿色的……时空倒转了……
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算上才认识那会儿,已经过去了九年,尽管之后四年失去联系,再见也是延续——很有可能,而不是重来。
“徐发发!”她突然叫了声。“我是王一平,你看清楚喽,我是个孤儿,从来没有外甥!”
我吓了一跳,条件反射状立起身,一下子对上了前面的女护士回头支过来的大方脸。
2、我是个骨子里挺自私的人,付出后得不到,我会很郁闷,会喝酒。再做事就要重新设定操作规程,用经验说话。我不觉得自私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人会在心里保证他从没有自私过,碍不着别人保护了自己,有什么不对。
所以二○○六年夏天那个车祸的案子我一接手就跟那家人一起迅速蹿红,那是我工作第二年的事。
不,我不是法官,我说的“接手”是指我对事件做了全程报导,那半年多我一共发了二十几篇稿子,有特写,有最新参事,有大家谈,也有人物专访,都是来自这起案件。那年无论我走到哪,几乎都有人问:“简阳到底是不是英雄?”
因为这起案件我成了报社的金牌记者,这才最是我想要的,当官做企业我都不感兴趣,学的就是新闻,我只会干这个。
有些事做了未必会得到所有人的满意,跟了大半年的事件,没有给出当事人一个真相,我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记”。
虽然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完成任务,也还是没有脸红的意思,那不过是我的一项工作而已,到达一个层次就得收关。再说了,也不是我一人说了算,头顶有当官的呢。
上个月我随警方去祥和区实拍一个房产纠纷的案子,很自然地想起这家人,几年不见,那个受伤致残的女孩儿简阳该成大姑娘了,她的失忆症好了吗?还有她继父带来的哥哥,帅到骨灰级的大四学生,这会儿也该参加工作了吧。
小掉简阳一岁、同母异父的妹妹简梅,因为长的象爸爸而时常苦恼,很妒嫉姐姐象妈妈。出事前本来她是和姐姐他们在一起的,为了买到一个头卡她先行离开,采访时我听到她几次提到这个细节,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摘清自己,不得了,那年她读初四,十五岁。
简梅的双胞胎弟弟简单当时没有跟出去玩儿,和几个同学去了清龙泡抓鱼,回来的时候大姐正在抢救,他在外边急的火上房;看到姐姐全身插满了管子,嚎啕大哭,拼了命地往里挤。比简梅高出半个头的这个男孩扬言要杀了那个开车的司机。我就纳了闷了,双胞胎啊,咋谁也不象谁呢!这会儿他们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学习吧,我想。
王一平,简阳和她双胞胎弟弟妹妹的生身母亲,一个土掉了渣的名字,与其本人的天生丽质完全大相径庭;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她身上散发的是一种令人惊艳的东西,类似于“媚”这个字眼儿;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丈夫,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可以成为一起生儿育女的夫妻。简阳出事后,家庭单位两点一线的她,一下子成了类似于政府发言人的角色,时不时会负责向媒体播报事件的进展,她意图非常明显地要把事情闹大,层层扒皮,还女儿清白,也还自己的清白。“我不是PX,刘锦华才是,坏人必须付出代价!”她这样说完,就把脸伏到臂弯里哭,刚哭两声又猛地抬头看着我说:“刘锦华,他要把我害死了。”然后继续哭。
这就是王一平,一个经常让我这个采访过无数女性的记者抓狂的女人,这个“PX”(破鞋)就让我石化了好半天,那个年份用字母代替词语的很少,报上也不常见,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满腹冤屈呢?有些人很会演戏,外表给人的感觉,王一平就是个会演戏的人,甚至她浑身上下都透着“演”的细胞。(她要扒别人的皮,反被人挖出多年前和刘锦华之间的“糗事”来,传得满天飞。)
小范围变成了大范围,事情闹大了,王一平的丈夫简少东几天没有说话,这么没面子的事捂还捂不过来,竟然撼不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孩子他妈。
男人无论他是专情还是多情,没一个愿意老婆拿顶绿帽子扣自己头上的。相安无事过了这么多年,刚咂摸出味儿来,冷不丁飞来块石头,这锅汤全撒了,周边的人全被烫伤,一个也没跑得了。
那期的采访任务结束后,留给我的就是这种感受,印象特别深。
王一平当时一手撑着桌面,一手比划着往外指:“我输了发发同志,你不用再来了。”
3、刚送王一平进了医院急救室,气儿还没喘匀,她的儿女们就到了。
“我妈呢,她怎么样?”简梅不知是问我还是问警察,这个二十岁的女孩儿长高了,脸瘦瘦小小的,带着她妈妈的那股子媚气,模样还是爸爸的款。
简单的个头很猛,一米八的样子,超过了也说不定。他推着姐姐简阳,说话粗声粗气:“劫匪抓到了吗?我他妈弄死他我!”
“黑社会”来了。这孩子还那样冲动,很正气很可爱,当年我俩是哥们儿,这会儿他和他的姐姐们好象都不认得我了。
随后到的是简亮,他和我想象的差不多,还那么帅气,只是成熟了很多。四年了,这家人是不是都变了?还在纠缠往事吗?还是已经走出了阴影?
我注意到,除了这四个孩子,最该出现的人——那个遗传给了简单高大身躯和简梅模样的父亲简少东没有出现。为什么他没有出现?是生病了,还是……已经不在人世?与王一平和简阳没有血缘关系的简亮神态平静地跟警察说话,一付大局的掌门人姿态,他和爸爸一点也不象,特别帅气的一个大男孩,不象爸爸,那就是象他的妈妈了吧。
看着有点乱,或者很乱是吗?是的。最初与这家结缘,我也陷入了迷团,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方格城,有入口,没有出口,每一个格子我都进去过,左冲右突,寻找真相,最后灰头土脸地顺原路返回来。
所以我说过当年的那场战争,我没有给出当事人一个真相,把这家人的隐私曝光后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我没有为此脸红过;此时站在一边的我无事可做,内心却突然升腾出一缕些微的歉疚。
劝解或帮助他人,我们往往会有充足的理由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而要说服自己,很难。
王一平的受伤不能不让我觉得,当年的故事可能真就没有完结,更确切地说是在继续。
明摆着给人的迹象是一个普通的劫案,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难道这种事我们不是经常可以从报导中看到过吗?
感觉是从我听到那一声“救命”的“女高音儿”而来。
王一平从来都不是个省油的灯,在她据理力争而得不到结果的时候,她的情绪经常会突然失控。
看到小警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也觉得再留在这也没意思了,里边的人出来的时间不确定,外面的人都不搭理我,不管什么原由都是令人尴尬的事。在跟着小警察回警局的路上,我深深地陷入莫名的失落中。人家都不认得我了、或者认得也装不认得,干嘛还要冒充人家的亲戚?脸皮真厚。
小警察把我交给了女警刘小英——我中学时的同学,一个出了名的假小子。上一起案子我跟随采访,她一直陪着我。
我们按程序做好笔录,然后她问我家住在新湖那边,为什么出现在龙华区的这个巷道里,两地怎么算也有四十里地。我说我来采访一个案子,本来决定今天一早回去,可是稿子还差点没写完,出来转转就遇到了这事。
“看来我暂时回不去了,还有要问的吗?我想去医院看看。”(刚才还觉得该走了,突然又想去看看,职业的本能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