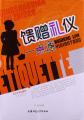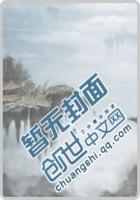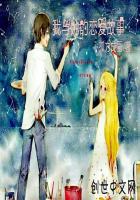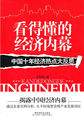重信守约,铸就“世界第一商人”
犹太商人重信守约的作风在国际贸易中可谓众人皆知。许多国家的商人与犹太人作生意时,对犹太商人的履约有着极大的信心,因为犹太人对自己的履约守信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不允许有任何不守合约的情况出现,哪怕是在别的场合出现。犹太商人的这一素质对整个商业世界可谓影响深远,真正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日本东京有个自称“东京银座犹太人”的商人叫藤田田,在一本推销自己的书《犹太人生意经》中多次告诫没有守约习惯的同胞,不要对犹太人失信或毁约,否则,将永远失去与犹太人做生意的机会。
犹太人的一个古代事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有一个犹太人老板和雇工订立了契约,规定雇工为老板工作,每一周发一次工资,但工资不是现金,而是工人从附近的一家商店里购买与工资等价的物品,然后由商店老板到这位犹太人老板处结清账目,领取现款。
过了一周,工人气呼呼地跑到老板跟前说:“商店老板说,不给现款就不能拿东西。所以,还是请你付给我们现款吧。”
过一会儿,商店老板又跑来结账了,说:“贵处工人已经取走了东西,请付钱吧。”
老板一听,给弄糊涂了,反复进行调查,但双方各执一辞,又不能证明对方谁在说谎。结果,只好由老板花了两份开销。因为他同时向双方作了许诺,而商店老板和该雇员并没有雇佣关系。
犹太商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守约本身这一义务,而不是守某项合约的义务。他们普遍重信守约,相互间做生意时经常连合同也不需要,口头的允诺已有足够的约束力,因为他们认为“神听得见”。
犹太商人的重信守约给他们带来了积极效果。
现代商业世界极为讲究信誉。信誉就是市场,就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所以,以信誉招徕或留住顾客也成为许多企业共同使用的招数。
在商业领域中,第一个奉行最高商业信誉“不满意可以退货”的大型企业,是美国犹太商人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的“希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这项规定是该公司在20世纪初推出的,在当时被称为“闻所未闻”。确实,这已经大大超出一般合约所能规定的义务范围——甚至把允许对方“毁约”都列为己方无条件的义务!
极高的商业信誉对犹太商人事业发达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守信是最有远见的“理性算计”。
犹太商人早在“宫廷犹太人”时期,就开始经营奢侈品,至今最主要的几项奢侈品几乎都仍为犹太商人所垄断。钻石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而钻石行业从开采、贸易、磨制到零售,几乎都掌握在犹太商人手里。妇女服装,尤其是时装,更是一项易过时的高档消费品,而在美国,女装的生产和销售一度曾达到95%被犹太人所控制。其他诸如裘皮、箱包之类的小行业(利润不薄)也均被犹太商人所控制。所有这一切奢侈商品的经营,都对长期守信这一点有极高的要求,借用犹太钻石商海曼·马索巴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经营钻石,至少要制定百年大计,一代人是完成不了的。而且,经营钻石的人须是受人尊敬的人,钻石生意的基础是取得人们的信赖”。
也正是凭着重信守约这种传统,犹太商人才游刃有余地纵横捭阖于世界商海之中,并充当了商业世界经济秩序的台柱。
犹太民族是一个重信守约的民族,在他们看来,契约是不可毁坏的,因为契约源于人和神的约定,犹太人信仰的源泉《旧约》就是上帝与人类之间订立的“古老契约”。
而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叫合同,是交易各方在交易过程中,为维护各自利益而签订的在一定时限内必须履行的责任书,合法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在世界商界中,犹太商人的信守合约是有口皆碑的。在他们看来,毁约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也是不可宽恕的。契约一经签订,就得设法遵守。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在读者心中或许是一个老谋深算、惜财如命的吝啬鬼,但实际上,这或许是莎士比亚对犹太人持有成见或心怀嫉妒。夏洛克的行为是现代契约精神所倡导的,也是犹太人遵守契约的一个表现,他面对破产的安东尼奥的朋友提出的各种有好处的条件,一直坚持原来的契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报复基督教徒,一方面也更是为了维护契约的神圣性。
犹太人的经商史,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契约的签订和履行的历史。
犹太人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一旦签订了契约就一定执行,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与风险也要自己承担。他们相信对方也一定会严格执行契约的规定,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因为他们和上帝签订了存在之约;如果不履行契约,就意味着打破了神与人之间的约定,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因此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签订契约前可以谈判,可以讨价还价,也可以妥协退让,甚至可以不签约,这些都是自己的权利,但是一旦签订了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折不扣地执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犹太人对违约之人深恶痛绝,一定要严格追究责任,毫不客气地要求赔偿损失;对于不履行契约的犹太人,大家都会唾骂他,并与其断绝关系,并最终将其逐出犹太商界。
恪守合同,绝不毁约
犹太人做生意十分注重合同。有一位出口商A与犹太商人B签订了10000箱蘑菇罐头合同,合同规定:“每箱20罐,每罐100克。”但A出口商在出货时,却装运了10000箱150克的蘑菇罐头。货物的重量虽然比合同多了50%,但犹太商人B拒绝收货。A出口商甚至同意超出合同重量部分不收钱,而犹太商人B仍不同意,并要求索赔。A出口商无可奈何,赔了犹太商人810多万美元后,还要把货物另作处理。
此事看来似乎犹太商人B太不通情理,多给他货物竟不要。这种在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事,在犹太商人心里是自有道理的。
首先,因为犹太人极为注重合同,犹太人可以说是“契约之民”。
犹太人生意经的“精髓在于合同”。他们一旦签订合同,不管发生任何困难,也绝不毁约。当然他们也要求签约对方严格履行合同,不容许对合同不严谨和宽容。
犹太人对合同的如此重视,与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有关。犹太教有“契约之宗教”的称誉,《旧约》全书就被当作“神与以色列人的签约”。犹太教认为,“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神签订了存在的契约之缘。”犹太人相信此说,所以犹太人不毁约,一切买卖只笃信合同。
相反,谁不履行合同,就会被认为违反了神意,犹太人是绝不会允许的,一定会严格追究责任,毫不留情地提出索赔要求。
第二,犹太人精于经商,深谙国际贸易法规和国际惯例。他们懂得,合同的品质条件是一项重要条件,或者称为实质性的条件。合同规定的商品规格是每罐100克,而A出口商交付的每罐却是150克,虽然重量多了50克,但卖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规格条件交货,是违反合同的。按国际惯例,犹太商B完全有权拒绝收货并提出索赔。因此,犹太商B此举是站得住脚的。
第三,上述案例中,还有个适销对路问题。犹太商人购买不同规格的商品,是有一定商业目的的,包括适应消费者的爱好和习惯、市场供需情况、对付竞争对手的策略等。如果出口方装运的150克蘑菇罐头不适应市场消费习惯,即使每罐多给50克并不加价,进口方的犹太商人也不会接受,反而打乱了他的经营计划,有可能销售渠道和商业目标受到损失,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第四,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可能会给买方犹太商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假设犹太进口商所在国是实行进口贸易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如果进口商申请进口许可证是100克的,而实际到货是150克,其进口重量比进口许可证重量多了50%,很可能遭到进口国有关部门的质疑,甚至会被怀疑有意逃避进口管理和关税,以多报少,要受到追究责任和罚款。
由此可见,合同是买卖的极为重要的要件,违反合同规定,对买卖双方会产生严重后果。犹太人深知其利害,故强调要守约。
事实上,合同不仅受犹太人重视,而且成为世界各国商业活动普遍重视之事。所谓合同,即通过交易的洽谈,一方的要约被另一方有效地接受后,合同就告成立。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就成为约束双方的法律性文件,有关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双方都必须遵守和执行。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规定,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签订合同的任何一方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合同。
守约,一种形式上的公正守法背后的智慧
犹太商人继承了犹太民族的传统,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他们不但严于守法,而且还非常善于守法。在两千多年的商业实践中,他们不但恪守了“契约之民”的民族教条,而且还智慧地创造性地大量积累了利用法律,通过契约达到自己目的的经验。说他们善于守法,是指他们有能力在严格遵守法律或契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哪怕这一目的在实质上是不符合法律或契约的规定,有违法律和契约原来的精神的。也就是说,借法律或契约之形,而行非法或非约之实(注意不是违法或违约之实),因为他们可是守法遵约的楷模。这种强调形式下守法守约的精神,大量地体现在充满智慧的犹太寓言中:
古时候有一个贤明的犹太人,他把儿子送到很远的耶路撒冷去学习。一天,他突然染了重病,知道来不及见上儿子最后一面,就留下一份遗嘱。上面清楚地写着:家中所有的财产都让给一个奴隶,但是在这些财产中,假如有一件是儿子所想要的话,可以让给儿子。不过,只能一件。
这位父亲死了之后,奴隶很高兴自己交了好运。便连夜赶到耶路撒冷,向死者的儿子报丧,并把遗嘱拿来给他看,儿子看了非常惊讶,也非常伤心。
办完丧事后,儿子一直在盘算自己该怎么办,但总是理不出头绪来。于是,他跑去见拉比,拉比是犹太人中非常聪明,而且极具智慧的人。这位儿子说完情况后,便发起了牢骚。拉比却对他说:从遗嘱上可以看出,你的父亲十分贤明,而且真心地爱你。
拉比让他好好动动脑筋,只要想通了父亲的希望是什么,就可以知道父亲给他留下了可观的遗产。
可这个当儿子的还是听不明白这样做对他有什么益处,拉比见他还是反应不过来,只好给他挑明:
“你不知道奴隶的财产全部属于主人吗?你父亲不是说给你留下了一件财产吗?你只要选择那个奴隶就行了,这不是他充满爱心的聪明想法吗?”
年轻人终于恍然大悟,照着拉比的话做了,后来还解放了那个奴隶。
很明显,这位犹太人实实在在地使了一个小计谋,给奴隶吃了一个中国俗话说的“空心汤圆”。遗嘱所给予奴隶的全部权利,都建立在一个“但是”的基础之上,前提一变,一切权利皆成泡影。这样一个机关暗藏的活扣,就是这个犹太人智谋的关键。
然而,这则《塔木德》寓言所蕴含的智慧,并不仅止于此,作深一层探究的话,还可以发现犹太民族在订约守约方面的独特智慧。
这位犹太人的遗嘱在形式上是自我完善的,只要遗嘱整体作为一项合法文件得到尊重,儿子作为继承人所享有的那一前提性权利要求,也必定能够得到满足。从这里不难看出,犹太人的智谋在于不借助外部力量,在严格履约的同时就可以避免合约中所规定的不合本意的安排,却不背上毁约的名声。
守约,一种形式上的公正
犹太民族素来看重契约,并以信守合约为立身之本。连与上帝的关系也被看作为一种合约关系,而不是像其他民族一样,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然而,合约一旦设定,具体的限定便马上有了“无条件”和“绝对”的性质,再也不能更改。显然,合约的这种严肃性较之合约中的主导方任意更改、毁弃合约的情形,总要多体现一点公正性,在合约双方出于自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然而,这种公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正,它并不意味着合约内容上的公正。无论何种合约,立约双方总会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想方设法加上于己有利的规定。在上述场合下,一方处于明显劣势,便无法拒绝另一方变本加厉的要求。
于是,既要保证合约形式上的公正性,又要加强或者抵消内容上的倾向性,便成为立约双方互作攻防的一个狭小舞台。不过,舞台虽小,对双方的用智来说,已经留出了很大的余地。从生活起居开始,在一切方面都颇为拘泥形式的犹太民族,自然就向着形式的方向,发挥、发展着自己的立约智慧。靠着这种智慧,理应对他们约束最为厉害的形式,却正好约束了他们的对手。那个奴隶之所以不带着财产潜逃,除了没看破遗嘱中的计谋之外,更大程度上还在于对犹太人守约所持的信任吧。
可是犹太民族的福祉恰恰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完备性,正好同人类社会形式合理化的一般历史要求相吻合,合约形式的公正正好同现代法律形式上的公正相吻合。由同作为合法权利之主体的立约各方,所自愿订立的合约,即使其内容不公正,只要在一定的限度内,从法律上说,仍然是公正的。事实上,在今日社会生活中,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首先成为智慧的主体。在现代商界中,较之那个奴隶远为自由、自主的人中,最终只能享有比该奴隶好不了多少的结局的,也不乏其人。仅就此而论,富有立约守约智慧的犹太民族在当今世界中的繁荣昌盛,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犹太教在中国有个俗称,叫“挑筋教”。因为犹太人的习俗是不食牛羊腿筋的,必需把它去掉后才能食用。
犹太人之所以不吃牛羊的腿筋,是源自《圣经》中的一个传说。
古犹太人的12支脉原是同父兄弟12个所传下的血脉,而这12兄弟的父亲便是雅各。
雅各年轻时曾去东方打工,依附于其舅舅的门下,并娶两个表妹为妻。后来,在神的允诺下,携妻带子返回迦南。
途中的一个夜间,来了一个人,要求同雅各摔跤,两个人一直斗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雅各,便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当时,雅各的大腿就扭了。
那人说:“天亮了,让我走吧。”
雅各不同意,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雅各便把名字告诉了他。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角力都得了胜。”“以色列”作为今日犹太人国家的名称,其含义是“与天神摔过跤的人”。
堂堂正正的耶和华上帝在同人进行比试之时,却使用不规范的小动作。这对于老是责备以色列人不守约的上帝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举动。但犹太人为何偏偏要把这一条记录在树立耶和华上帝绝对权威的《圣约》正典之中?是否对上帝有些不恭?
也许,古代犹太人角力之时,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可摸对方的大腿窝,上帝不过钻规则不清的一个漏洞罢了。而作为上帝子民的犹太人,把这么一个上帝钻漏的典故记下来,完全可能是出于将“钻漏洞”这种合法的违法之举或者违法的合法之举加以神圣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