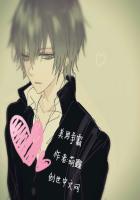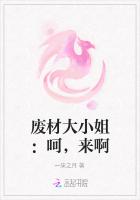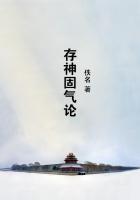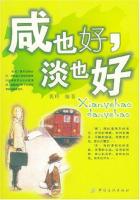一、布衣境遇与谢榛诗法
据于慎行《李符卿墓志铭》所言,当年“结社赋咏”的诗人里,就有李攀龙、谢榛和王世贞。这三人成为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中坚。谢榛和李攀龙一样是王世贞所尊重的“友师”,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被视为“力逐二子”的人物。在王世贞《明诗评》这本“明代诗人排行榜”里,依次排列的前几名诗人是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徐祯卿、谢榛、高叔嗣、边贡、郑善夫、薛蕙,反映出嘉靖三十年代初期复古派文人的自我认知。谢榛在后七子的思想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世贞说:“谢榛十诗九不道,布衣吾侪甘折节”,又称颂其“布衣风格,从古未有”。布衣谢榛与“李生同志,实深琢磨”,共同奠基了后复古思潮的诗学架构,这是被王世贞认可了的史实。
嘉靖二十六年以来,谢榛因其卓荦的诗歌才华,跻身京都名流,嘉靖三十一年春被李攀龙等招入诗社。但是,嘉靖三十三年,谢榛前往顺德府拜访李攀龙时发生冲突,被削迹于“五子”,成为复古派的边缘人。李、谢之争是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历来众说纷纭。要者有二:一种是来自复古阵营的看法,指责谢榛的人格和诗格。一种则认定李、谢之争的实质缘起于缙绅先生与布衣的身份鸿沟。这种看法源自于徐渭,一个嘉、隆之际更为卓尔不群的“布衣”。
布衣不是缙绅。徐渭《二十八日雪》说:“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他所提示的缙绅与布衣的身份鸿沟仍然是我们切入谢榛精神世界的重要视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吴山人扩》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此后接迹若市人矣。”布衣谢榛又叫四溟山人,山人并非一定是布衣,但是山人文化构成了布衣文人的基本生存面向。黄卓越认为,正、嘉间山人文学寓意着山林与台阁的分离,其文化旨趣指向道德主义的目标。其实,这只是山人文化内涵中的一个侧面。“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道德意蕴与“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的功利旨趣,从来并存于山人文化之中。终南自古就是捷径,“山东布衣”李白以山人自许,其实是立志要做终南捷径的受益者。以隐逸山林而博名求仕,几乎是山人文化的题中之意。自古以来,道家的隐逸旨趣始终是山人文化的精神指向,迄于明代,由于陈白沙等儒者的活动,山人文化里道德主义的旨趣确然变得醒目起来。但是,江南商业经济的发展中,不甘寂寞的布衣一山人同样异常地活跃。王世懋《王承父后吴越游诗集序》说:“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早于谢榛的五岳山人黄省曾就是就是以诗干谒的典型代表。《列朝诗集小传》说:“勉之倾心北学,游光扬声,袖中每携诸公书尺,出以夸示坐客,作临终自传,历数其平生贵游,识者哂之。”谢榛同样以布衣诗人的身份干谒名公,炫耀诗法以博名利是他的本能。也是他的权力。吴国伦说:“今天下布衣之士能言诗者不少矣。乃独弘、嘉间孙、谢二子诗最近古,又率附当时诸名公以传,遂得贾重一时。”如果不站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上,儒者以“立德”来博取生命的不朽或许是高尚的,诗人以“立言”来博取现世的机遇与身后的声名,也未必就是可耻的。
嘉靖二十七年,李攀龙、王世贞调任刑部,谢榛因而与白云楼社的诗人们频繁唱和,切磋诗法。其《诗家直说》记载:“己酉岁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鳞、王元美及予赏月。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掏予手,使勿言。予愈觉飞动,亹亹不辍。月西乃归,于鳞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机?’予曰:‘更有切要处不言。’曰:‘其如想头别尔。’于鳞默然。”时为嘉靖二十八年中秋。在刑部,作为新来乍到的低级官吏,李攀龙仿佛一直是沉默寡言、站在边缘的不起眼的人物。如同后来对吴维岳的排斥一样,李攀龙对这些前辈诗人大概总是心存隔阂的。何文焕说:“吾人诗文一道,非秘密藏也,特恨不肯来学耳。谢山人论诗,李于鳞责其太泄天机,殆风雅中小人哉。”当然身处吴中诗风弥漫的诗学语境,李攀龙对不肯“舍所学而从我”的诗人三缄其口,也并非不可理解。然而,孤介自赏的缙绅先生显然不能理解以诗干谒的布衣。对于山人文学这个族群来说,三缄其口原本不是其行事风格,以诗干谒,以便名著当世、托于不朽才是其生存本色。
诗歌和诗法是谢榛与缙绅先生倾盖相交的资本和依据,孤介自赏和三缄其口原本就不是“山人”的行事风格。谢榛《诗家直说》里“沾沾自喜”和“太泄天机”的掌故不胜枚举,这成为他与李攀龙交恶的导火索。李攀龙《戏为绝交谢茂秦书》直言:“时尔实有豕心,不询于我,非其族类,未同而言;延颈贵人,顷盖为故,自言多显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弟将疏间之,我用恐惧贻尔。”说明二人生隙的原因,一是未同而言,一是延颈贵人。谢榛旅居京都,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以声律之学请益”和“折衷四方议论”。《诗家直说》说:“予昔游都下,力拯卢槽之难,诸缙绅先生多其义,相与定交。草茅贱子,至愚极陋,但以声律之学请益,因折衷四方议论,以为正式。及出诗草,妍亦不忌,媸亦不诮,此虚心应接使然。”他以诗学立命,一技束心,正是要博采众长,以为当代诗学之“正式”,以诗歌和诗学博取平交名流的地位和不朽的声誉。因此,他对于孤介自赏者,斥之为“性褊尤甚”,自言:“予客京师,有一缙绅相善。”尝谓予曰:‘每见人恶诗,予意憎之而不乐交也。’曰:‘予则异于是,若以诗定交,海内宁几人邪?若有不读书者,知我为诗人而加礼,岂可沮其诚邪!缙绅先生与布衣如是不同,“缙绅”把诗歌当做与人交游的底线,凡是诗歌不佳或不肯“舍所学而从我”者都“憎之”,谢榛却以“诗人”的身份沾沾自喜,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
谢榛不仅倒处炫耀诗法,泄露天机,还喜欢点窜古人名篇,并把自己的诗歌拿来让名流品评和修改。他说:“凡造句已就,而复改削求工,及示诸朋好,各有去取,或兼爱不能自定,可两弃之,再加沉思,必有警句。”“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郑国凡作辞命,必经四贤之手,故见重于列国。予因之以为诗法,每有疑字,示诸社友定正,工而后已,能受万益而不受一损,其立心何如也。”但这种请益或炫耀的作法却博得了缙绅先生的嘲弄。《诗家直说》云:“凡以诗求正者,在乎知己,否则无益,徒有自炫之诮。”“近有词流,与人一字之益,每对众言之。其不自广如此,及出所作,称之则快意,议之则变色。虽杜少陵更正,亦不免忌心萌焉。夫偶定人之未安,何其自矜,竟沮人之有益,甘于自误。嗟,彼何人哉!”毋庸置疑,这些“词流”里有李攀龙,或者还有王世贞。在致李攀龙的信里,王世贞说:“老谢此来何名,狼狈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且不轻用常人态责于鳞,彼不记《游燕集》中力,真负心汉。遇虬髯生,当更剜去左目耳。”四溟山人又号眇君子,一目,王世贞看他目中无人,便想把剩下的一目也“剜”去了事,怪不得山人要叹惜道:彼何人哉!当谢榛与李攀龙在嘉靖三十三年于顺德府不欢而散以后,缙绅先生与此布衣终于渐行渐远而分道扬镳。
无论“缙绅”还是“布衣”,诗歌和他们的生命旨趣已然融为一体。缙绅先生可以拒斥俗流,可以相互标榜,他们已经据有了缙绅的身份,并且可以相信不朽的诗歌。但是布衣山人总是喜欢炫耀诗法,平交名流。诗歌是其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方式,没有诗,他就在历史的这一页里消失了。缙绅和布衣的生存态度原本是不同的,或许缙绅先生不肯随波逐流,坚持信念,也算是高尚其志,但对谢榛来说,这是莫名其妙的。缙绅先生可以对山人的人格和诗格横加斥责;布衣山人只能对缙绅的咒怨三缄其口,唯以诗法,孤介自赏。《诗家直说》便是布衣谢榛对诗法的旁白。
二、“夺其神气”与“提魂摄魄”的酿蜜说
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的思想,尝试在复古的框架里推进文学创作的创新机制,其语源来自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其诗学精神很可能受到谢榛“三要”说的影响。谢榛说: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予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成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公笑而然之。这则材料受到钱谦益、朱彝尊等文学史家的普遍重视,并被清修的两部煌煌大典采用。《四库全书总目》说:“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定称诗三要,皆自榛发。诸人实心师其言也。”张廷玉《明史》说:“其称诗旨要,实自榛发也。”前七子的复古文学在正德、嘉靖之际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发展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但是,伴随着复古思想的出现,“剽窃”的指控就不绝于耳。李、何虽然并称为复古运动的宗匠,在嘉靖初年却标识着不同的思想向度,李梦阳是杜诗学的象征,而何景明指向初唐体与个体情性的言说,李、何之后的文学有意地避开杜甫的沉郁雄伟的写作风格,探索适宜于个体性情的表现方式,六朝、初唐体成为流行的写作范式。因而,就有了初唐十二家诗集的盛行,有了杨慎关于“见其学少陵者,其诗必不佳”的论断。嘉隆七子是弘正七子的嫡子,其孕育过程中先天地烙上了前辈们的思想胎记。如何弥补前七子留下的文学思想的裂痕,如何超越“剽窃”的指控,如何恢复盛唐诗歌的荣光?成为诗论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夺其神气的熟读说即为答案之一种。
谢榛说:“作诗最忌蹈袭。”“专模拟,非其本色。”又说:“《三国典略》曰:‘邢劭谓魏收之文剽窃任昉,魏收谓邢邵之赋剽窃沈约。’盖六朝习气如此。近有剽窃何、李者,其二子之类欤!”后七子在讨论“孰可专为楷范”的问题上,必须正面回应剽窃的历史共业。所谓“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又谓:“莫画少陵神自合。”谢榛的“三要”和“莫画少陵”便是后七子欲回向盛唐和超越“剽窃”指控所达成的共识。杨慎等人避开杜甫和盛唐,另辟蹊径,鼓吹溯流讨源,回归唐诗的源头,谢榛等人却以杜诗学为中心,拓宽取材范围,并且希望通过种种诗法来重构盛唐诗人兴象玲珑的意境。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于鳞成进士,有意于诗,与其友请教于谢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铮铮者,而未有见于唐人者也。教以取唐诗百十篇,日夜咏读,仿其声光以造句。于鳞从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谢榛认为,通过对十四家之“神气”、“声调”和“精华”的融释,便可以超越言辞模拟的形式桎梏而优入圣域,在同与不同处获得对盛唐诗歌的呼应和发展。据说,这种指向继承而且超越了何、李的诗学观念,成为“七才子”独具的创作取向。
“三要”说突出对初盛唐文学典范的“熟读”,这本是宋人学问的成法。杜甫是宋代江西诗派和明代复古派共同尊奉的典范,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写作精神,已经敞开了宋明诗学的门径。黄庭坚《答王观复书》说:“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其《论作诗文》说:“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这是东坡、鲁直“作诗文”的家法,为江西诗派所遵循。但是,这种方法在严羽那里成为反对江西诗派的利器。严羽《沧浪诗话》说:“功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段话里包含着“熟读”、“悟入”和“从上做下”的典范选择等多重意味,具备了谢榛诗学的基本要义。谢榛说:“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老杜不欺人也。”便是复古诗人文学精神的夫子自道。从杜甫到苏、黄,再到严羽,以至谢榛,熟读说始终是继承诗学传统而求发展的基础。
谢榛强调要对“十四家”熟读涵咏,融冶一炉。不执一家,不泥字句,要取其神气,以获得“其味自别”的意趣。他说:
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学子美者,则未免蹈袭,亦有不喜子美者,则专避其故迹,虽由大道,跬步之间,或中或傍,或缓或急,此所以异乎李杜而转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诸公之所共由者,予则曳裾蹑履,由手中正,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辩也。
子夜观李长吉、孟东野诗集,皆能造语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并夺搜奇想头,去其二偏: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坠,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崖冰雪,见者靡不惨然,予以奇古为骨,平和为体,兼以初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与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蕴。
从花粉到蜂蜜是一种辛勤酝酿的过程,从熟读典范到创作也有着长的路要走。如严羽指出“向上一路”一样,谢榛便是要“曳裾蹑履,由乎中正”,堂堂正正地走上“盛唐诸公之所共由”的大道上来。当然,面向盛唐,还要超越盛唐,超越的办法便是“酿蜜法”。谢榛说:“专于陶者失之浅易,专于谢者失之饾饤,孰能处于陶、谢之间,易其貌,换其骨,而神存千古。”专学一家是笨拙的方法,写诗如同酿蜜,必须在百花园里博采萃取,才能酝酿出最甜蜜的芬芳。又如同调羹,必须在五味调和,才能其味自别。唐顺之偏嗜淡乎无味之至道,要求文学作品表现“天然真味”,并且认为“好文字与好诗亦正从胸中流出,有见者自别”;谢榛要求文学书写应当“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前者从心源开始,后者从典范开始。谢榛认为,通过对众多典范的揣摩熟读,既可以避免“生剥少陵”式的剽窃问题,又可以博取众长,酿造出属己的味道来。
“酿蜜法”是“熟读以夺其神气”的具体展开,谢榛又称之为“提魂摄魄之法”。蜜蜂所采撷的是花的芳馨,这是内属于花蕊的花之精魂;诗人从典范里采撷的是诗歌的“神气”,这是由语言所承载却内蕴于诗人灵魂的品格。谢榛认为,“诗无神气,犹绘日月而无光彩。学李杜者,勿执于句字之间,当率意熟读,久而得之。此提魂摄魄之法也。”“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也。”谢榛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