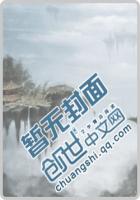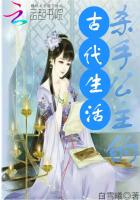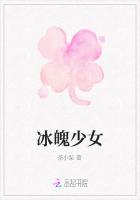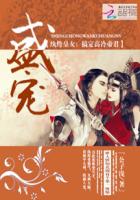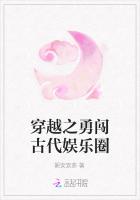当年,红军缴了两河口敌人的械,张啸虎跑了,胞儿子也溜了号,大太太和二太太四太太都去了成都,跟儿子的跟儿子,找女儿的找女儿,三太太更加现实,跟了一个做生意的,做了老板娘。一家人散了,金银首饰私房钱没了,张金铃和两岁的女儿妞妞到哪儿都讨不到舒心的日子过,不得已就留了下来。
庄园作了红军的司令部,也没有赶金铃母女走,那些人在庄园里出出进进,对她母子俩倒是客客气气的,像老赵一样还没有尝过荤腥味的小伙子们,平常总爱拿眼光在她身上扫来扫去,她晓得他们想要啥子,但终究没得哪一个人敢特别靠近她。
一个多月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有时,拥着妞妞睡不着觉的时候,金铃就有意识地把那些总爱拿眼光扫她盯她瞄她剜她的人,按眼睛的亮度,眼色的浓度,目光的热度排成一串串,一个一个地比较,同时也一个一个欣赏。在她看来,那些人都还不错,一个个意气风发,一个个充满了阳刚之气。
那个赵连长眼睛最馋,目光最损,每次有意识无意识地遇上了,那目光就像刀子一样,剜得人生痛,浑身都不自在。每次到了大天井,只要她在屋子里,他总要绕道从她门前经过,有时还要在门前停一停,鬼眉鬼眼地往屋子看,看屋子里的她。
有一次赵连长居然进了房间,向她要水喝,无话找话地问她在做啥子,娃儿有多大了,生活方不方便,一双眼睛亮光光的,热辣辣地盯着她的身子看,搞了她一身的鸡皮疙瘩。
时间长了,她就慢慢地熟悉了那些眼睛,适应了那些目光,扫就扫呗,盯就盯呗,瞄就瞄呗,剜就剜呗,她知道女人生出来就是要男人们眼馋的,如果哪一天男人们对你不再眼馋了,那你就没得了光彩,就失去了新鲜。
红军撤离的那天晚上,金铃刚刚躺在床上不久,就听到集合队伍的哨音响起,只听一声令下,那么多的人,好一阵的脚步声响后,庄园里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她心里顿时觉得空落落的。她觉得这一个多月的时光值得留恋。她明白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用那样眼神看她了,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她那么友好,那么客气了。
没想到,赵连长杀了一个回马枪。当时,偌大的庄园里,除了猫啊狗的,就只剩下金铃母子俩是活口了,他带人进来只是为了抢东西吗,只是为了把那些猫啊狗的都撵出去吗。不是,一定不是。他那一回马枪肯定是专门针对她来的。不然,他怎么会独自闯进她的屋子里,进屋后怎么会直戳戳地就扑上了床。
金铃开始觉得很害怕,后来又觉得很兴奋。
赵连长是那么急切,狗急跳墙般地气喘吁吁,又是那么笨拙,七进八出而难得要领。
作为一个过来人,金铃分明感觉得到赵连长是多么的饥渴,又是多么的燥烈。他可笑的笨拙,可畏的燥烈,唤回了她的知觉,唤醒了她的敏锐,唤起了她的欲望。她非但没有避让,没有抗拒,反而亮出五脏六腑,敞开七门八户,尽情地迎合着他,也纵情地享受着自己。
哪曾想,吃下赵连长那只饿老虎的满膛枪弹,肚子竟然消化不了,金铃以为那是因为他贮藏了三十年的种子一定不比寻常,它的生命力真是太强了,仅仅匆匆忙忙的那么一回,就大见其效,十个月后居然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就是她的第二个娃娃小虎。周围的人并不晓得事情的缘委,只是一个劲地帮着她痛骂那个卷了她全部私房钱跑了的男人,而她心知肚明,有时不由在心里还为那个男人抱不平。
金铃抱着女儿出了庄园大门,到了通往两河口场镇的大路上,回头再望庄园时,庄园上空已是烈焰滚滚了,不禁两眼泪水涟涟。她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步一回头,失魂落魄地沿着大路向两河口场镇走去。她见赵连长那伙人又追了过来,以为还要找她啥麻烦,躲是来不及了,就侧身让开道,站在路旁。
赵连长来到面前,扫了金铃和怀中的娃娃一眼,也没言语,把那床羊毛毡和缎面棉被放在她脚边,仍然挂着那个临时用床单做成的包袱,领着那些战士跑步穿过了场镇。
整条街的铺面没有一间打开,人们彻夜未眠,都躲在屋子里侧耳听着街道上一队又一队的红军通过。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忽然又响起一阵杂杂踏踏的脚步声。人们并不晓得这最后的脚步声早已被庄园熊熊燃烧的烈火所淹没,再也不会重新响起。
金铃跌跌撞撞地来到街上,见唐老先生独自站在老乡情客栈门前,望着庄园方向滚滚的浓烟发着呆。她以前是认识老先生的,见整条街上只有老先生一个人,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来,直愣愣地跪倒在他面前,凄凄惶惶地喊了声,爷爷,我们母女以后的日子咋个过得下去哇。
老先生见是张家大小姐,赶紧扶起她,把她让进屋里,扶她在板凳上坐下,问她到底发生了啥子事。
金铃抽抽搭搭地把早上她所听到的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告诉给老先生,赵连长的那些个人作为她当然难以启齿。
老先生看了看在金铃怀中仍在安睡中的娃娃,很是感慨,安慰她,姑娘,天无绝人之路,你看啦,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这娃娃仍然能够安睡如常,你也一定不要着急,没安顿好之前,先就暂时在客栈里住下,在这里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们母女,以后的事情再慢慢来办好了。
在危难时刻,老先生不但安顿好了金铃母女临时的生活,而且还帮她请人整理好房间,借钱给她购置了锅碗瓢盆生活用品,直到真正像个家了,能够过日子了,这才让她带着女儿离开客栈,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好在金铃她妈妈大太太当初不愿在家吃闲饭,拿私房钱在两河口场镇最繁华的地方盘下了一爿店铺,雇人经营些油盐酱醋等日用杂货,在她成家时,妈妈作为嫁妆送给了她。
那爿店铺前面作铺面搞经营,后面还有好多的房子,还可以招客做旅社。红军进入两河口前,店铺成了丁德隆驻军的副食专供点,赚了不少的军费。
金铃是庄园里的大小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都不用她来做,什么都不用她来管,佃户每年应该交多少租子,场镇上有多少铺面应该交纳多少房钱,店铺里到底赚了多少钱她一概不知。现在,她只有靠店铺的收入维持母女日后的衣食住行了。
红军前脚离开,田颂尧的队伍后脚就跟到。他们进驻两河口后,并没有组织有效的追击,而是以搜查流落红军伤病员为名,对两河口场镇店铺及周边地区的全部民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店铺里所有值钱的货物,特别是粮油之类的物资,周边地区农民的家禽家畜,包括猪牛羊这些农家最重要的资财都在劫难逃。人们看到他们到来,犹如羊群看到虎狼,唯恐避之不及。一时间,搞得许多原先在场镇做生意的人不得不逃往外地,或者躲避乡下,两河口场镇的店铺纷纷关门大吉,市场一下子显得十分的萧条起来了。
两河口地处川陕甘结合部,虽是战略要津,历朝历代都会派军把守,但真正设置过行政衙门的时候却是无据可查,田颂尧的队伍给两河口送来了这一特别新鲜的事物,衙门就设在戏园。
有衙门就有县长。县长在两河口亮相时,七沟八梁的人们,不顾那些虎狼之兵的侵扰,纷纷涌到两河口,争相一睹民国时期两河口历史上第一任县长的风采。
那天天气晴好,时近中午的时候,戏园里已经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比上演任何一出大戏都还热闹,县长在他的全班官员的簇拥下,登上了戏台。
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大声欢呼着,呼喊着。
县长瘦高身材,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左上侧衣袋上挂着一支钢笔,大分头,头发盖住了两只耳朵,黑边眼镜挂在一张瘦脸上,很不协调,小胡子稀稀拉拉,显得不够精神。他望着黑压压的人群,举起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人们安静下来。待人群稍稍安静了一些,他习惯性地抬起右手,将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沿着鼻梁向上推了推眼镜,再将双手剪在背后,挺了挺小肚子,直着嗓子喊,父老乡亲们,鄙人作为清水河县第一任民国县长,从今天开始就要履行职责了。
噢哈喝唉,人群再次沸腾起来,完全淹没了他的声音。原来,人群中有人认出县长就是本地人,是张啸虎的二儿子张银川,那个在成都教书的二娃子,不由大声喊了一声二娃子,其他人也跟着喊,场面再次喧闹起来了。
二娃子张银川是搞教育的,信奉教育救国。他做清水河县长,全靠大娃子张金川运作得力,省政府力挺他荣耀还乡,以光宗耀祖。他做了县长自然要推行他的施政纲领,包括清除匪患、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振兴教育、积极推进新生活运动等等。清除匪患是驻军的事,发展生产,活跃市场做的都是官样的文章,他唯独把振兴教育拿在了心上。
上任伊始,张银川就开始筹划在两河口小学堂的基础上,办一所完全新式的学校,他亲自担任了新式学校筹建董事长。他通过同学关系在成都聘请来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搞规划设计,选派专业人员监督施工,不到半年时间就修建了一所可容十五个教学班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的学校,命名为清益公学。
学校建成了,张银川亲自兼任校长,遴选了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担任学校教师,于当年底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为了保证生源,他下令关闭了县城周边地区的全部私塾,动员和鼓励有条件上学的儿童都到新学校上学,家庭困难的儿童还可以享受到一定的助学金。
新学校对学生实行梯次教育,把招收到的学生按年龄,兼顾已经接受教育的程度,分成若干年级教学,首开了男女生同校同班上学的先例。学校以此为基础,每年再增设一个年级,达到十个年级的规模。川军名将王铭章前往抗日前线,路过两河口时,张银川以校长的名义,组织全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川军抗日去了,接防的是胡宗南丁德隆的队伍,随军又来了一个新县长,二娃子的县长当然做不成了,成都也不回了,就干脆留在两河口做了清益公学的专职校长。
有二娃子做县长的面子,市场再萧条,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她大小姐张金铃的店铺照开不误。她不会经营店铺,生意上的事情只得雇用原来的老雇主帮着打理。店里要进啥子货,定多少价,赚多少钱,她什么都不过问。尽管小虎出生后,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但有店铺比较稳定的收入,维持她们母女母子的生计倒还问题不大。
两河口这地方人心不坏,有一些老佃户在张金铃看来非亲非故,她连人都还认不实在,每当逢场天就有人送来一些新鲜蔬菜,在夏收冬藏时节,或在年头岁尾,还有人送给她一些粮食腊肉之类的东西。当然,她也学会了打理人情世故,对上门来的人,按着年纪,大爹大妈表叔表婶哥哥嫂嫂弟弟妹妹叫得亲亲热热,渴了的有水给喝,饿了的有饭给吃,远山远岭当天回不了家的,管吃管喝还给住宿。如果哪家有了红白喜事,她只要晓得了,都会准备一份礼物送去。就这样,你来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情厚重了,尽管她由庄园里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但感觉日子比在庄园里还过得舒心。
抗战了,两河口一下子涌进了许多的人,街道增长了,场镇扩大了,店铺也增加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了,店铺的收入自然越来越少了。为了生计,金铃就在庄园废墟旁,开了一块蔬菜地,在这块菜地里打发平常的日子,按季节栽种一些萝卜白菜葱葱蒜苗之类的东西,以减少家庭开支。
当初,在金铃生活最无望的时候,老先生给了她许多帮助,许多照顾,还给了她一个长辈对晚辈的爱。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娃娃伤风咳嗽了,感冒发烧了,磕倒了绊倒了,少不了要老先生给医治,给拿药。有些时候,老先生还会买些杂糖给两个娃娃吃。两个娃娃对老先生也特别的亲热,人前人后祖祖长祖祖短甜甜地叫着,经常结伴到客栈来耍,有时耍忘了,老先生就给他们弄吃的,店里的事忙不过来了,就掏钱叫他们到街上去买零食。老先生的疼爱换得了两个娃娃的更加亲近,自觉不自觉地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近几年来,老先生的年龄一天比一天老了,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了,金铃就干脆到客栈里来帮忙。
金铃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男人是她爹给看中的。她并不喜欢那个男人。他个子那么矮,胖胖的,活像一个大大的冬瓜,在那支丁德隆的驻军里当司务长,整个驻军百多号人要吃要用的东西都要经过他的手买进卖出。
金铃她爹见他脑子很活套,很会整钱,时不时地给家里送东西,嘴巴也甜,见了爹妈就大爹长大妈短地喊得他们心热。她爹就把她嫁给了他。
婚后,金铃感觉不到幸福,也感觉不到不幸福,反正还和爹妈吃一锅饭,住一个大天井,除了晚上睡觉多了一个人外,其它的还和以前是一样的。
妞妞出生了,那男人见没有给他生儿子,对金铃再没有了那种粘粘糊糊的热情了,整天就算计着如何整钱。
红军进了两河口,一家人四散而去,金铃以为他不会丢下她和妞妞一走了之,哪知他那么心狠,不但卷走了家里那么多的东西,还偷去了她的全部首饰。她好像掉进了一个大大的冰窟窿,心冰了,整个身子都冰透了。当时,如果不是妞妞,她真不知道她会怎么活下去。
都是当兵的,金铃就没见过那些红军战士欺侮过人。这些人的年龄有的大,有的小,看到她都一样的心跳脸红眼睛发绿,总是围着她嘤嘤嗡嗡地打转转,大姐长嫂子短地喊得她沁心又润肺,受用极了。虽是孤儿寡母,有他们在,她从来没感到过无依无靠,有他们在,她没有担过一挑水,没有挪过一梢柴。他们走了,她一时真不习惯,有时做梦还会见到他们关公似的大红脸。
庄园烧掉了,家没有了,都是赵连长他们作的孽,但金铃对他们却恨不起来。
金铃生小虎时,才二十出头,多少好心人劝她再找一个男人,老先生也劝她再安一个家,她都以有女有儿了,以后有靠了,不想再自添麻烦为由拒绝了。
实际上,金铃始终觉得要等一个人,到底要等哪个呢,为啥要等呢,等他有啥价值呢,她又说不清楚,等那个人成了她冥冥之中一盏希冀的灯,成了她的一种信念。时间长了,把成家的事淡忘了,把男女之事也淡忘了,把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唯独这一信念不但没有淡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信念更加坚定了。
那天,金铃在军管会第一眼看到老赵的时候,不禁眼前一亮,头脑中的那一信念立刻幻化成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但是,女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尊,又迫使她不但不能以正常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愿望,反而还有意识地抑制了自己的冲动,忽视了这种现实,她故意以那种极不友好的态度对待他,拒绝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