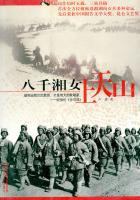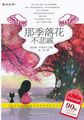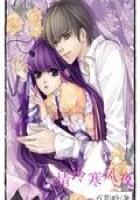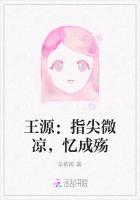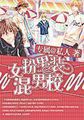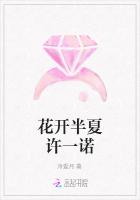在大雪纷飞的农闲季节,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秦人,用舞台的形式弘扬着秦文化,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尽情宣泄着秦人的情怀。王者豪情的呐喊,女子如泣如诉的哀婉,达官贵人心花怒放的喜悦,演绎在三尺舞台上,秦人陶醉在舞台下的美梦中。遇到哪个村子搭台唱戏,人们蜂拥而至,台下人头攒动,小商小贩也趁机红红火火,大人们或站着、或坐着、小孩子或攀岩到房顶或者树枝上,或者留恋在小商贩香喷喷的小吃摊前。这是一个忘乎所以的节日,贫富平等,贵贱不分,童叟皆醉。
不堪回首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那年,吃糠咽菜都是奢望,青黄不接时到地里找无毒的野草,聪明的办法是牛能吃的草人就能吃。有一种牛喜欢吃的野草叫“刺靳”,肥胖的叶子边上长满了小刺,我们把它和豆腐渣蒸在一起,尽管很难咽但能充饥。那时候,院中那棵较粗的古槐树结的槐角,就是我家和亲戚家渡过灾荒的救命树。
到了冬天,为了填肚子,我们除在门前的窑洞里挖观音土吃外,就是剥树皮煮着吃,去刮能吃的几种树皮,最好吃的是榆树皮,榆树的树皮均被剥光,树干都呈白色,能吃的野菜、树叶都被采光,就像闹蝗虫一样,能吃的都吃光了,吃得很多人都浮肿,更有人不慎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中毒。
而我最难忘的是农民自已发明的一种食物——“淀粉”,加工“淀粉”的主要原料是干玉米芯子,先用锤子把玉米芯砸碎,再用水浸泡一天后,用布包上用力的把液体挤在盆里,将液体沉淀,这沉淀物就是所谓的“淀粉”,用“淀粉”和糠、麸皮混合做的窝头又干又硬,非常难下咽,最可怕的是,吃了以后根本排不出来,特别是老人和孩子们,整天憋得难受,哭哭啼啼,真是惨不忍睹。
如今的故乡,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三农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精彩雄壮,还有那释放着朗朗书声的学校,那一间间琳琅满目的小百货商店,都记录着故乡的历史进程。村村通公路工程、户户通电工程的实施。有线电视进入农村、新村扩建、旧村改造工程的实施。家乡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回忆是多情的。回忆家乡的点点滴滴时,我的脸上总带着笑容。这片多情的土地养育了我,养育了我的父母,我的祖辈,我的父老乡亲。潺潺流水,诉不尽童年的故事;满目青山,写不尽故土恋情。我更想说的是,我的根在故乡那片土地里,这片肥沃的土地收获着我,收获着喜悦,收获着希望,收获着人世间绝无仅有的乡邻乡情。
映象秦腔
秦腔是西北人民的精神支柱,是西北历史文化的灵魂。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脚下踩着帝王之气浸润过的黄土,身上带着陕西高坡浓浓的泥土气息;血管里流淌的是秦腔的音韵,脉搏里跳动的是秦腔的音节。富饶而美丽,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养育了忠厚善良、情感丰富、吃苦耐劳的秦人,他们为自己钟爱的黄土地抛洒血泪的同时,用高昂的秦腔吼唱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之歌,用高低舒缓的曲调表达了自己普通生活的喜怒哀乐。在凄苦的年代,秦腔作为唯一的精神食粮和抗拒苦难的力量,让饱经风霜的祖辈们渡过了艰难困苦,练就了家乡父老钢铁般的脊梁。
我爱秦腔,从会说话起就学着唱秦腔。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在夏天的夜晚,独自一人坐在大树底下,抽着旱烟,唱着秦腔,我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外面的吼声就像是催眠曲伴我入眠;稍大后,趴在戏台子底下听秦腔;再大些,晚上或者雨雪天不下地干活,在生产队的饲养室、磨房,挤到大人堆里听他们唱秦腔,如醉如痴。真正期盼的,还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大人们不会像日常那么随意地弹唱,总是郑重地搭建起戏台,戴上各自角色的帽子,穿起宽大的戏服,脚上套着厚重的戏靴。锣鼓一响,戏迷将吃了一半的饭碗撂下赶往戏场是常有的事。
那时候我还小,父母对我学秦腔并不支持。大冬天,我怀里惴一个凉红苕,早早来到后台,主动去拉幕帐、摆道具、提示台词……在后台学唱,戏后和大人们交流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并利用下午放学干完农活后的时间,跑到村后面的小山丘,练习吊嗓子。面对空旷的大地,自那一声秦腔吼出,内心顿生心旷神怡、六根清净之感,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就是在这样耳濡目染下,我先学会哼调,熟记所有戏词,逐步学会了唱、念、做、打、舞、技,虽不专业,但也能唱出秦腔戏曲的骄傲和来自黄土地的自豪。再后来,大人们就让我救场,跑龙套。
那时的年月虽然平淡,但却真实,不知有多少夜晚我是守在父亲身边度过的。曾记得父亲对我说:相传唐玄宗李隆基曾经专门设立了培养演唱子弟的梨园,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就是陕西民间艺人,他所做的《秦王破阵乐》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其后秦腔受到宋词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成为梆子戏。可见,秦腔艺术的源源流长。
秦腔之所以受人民喜欢,是由于它产生于民间,能够生动的反映出人民的愿望、爱憎、痛苦和欢乐,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因而有着深厚的根基。史料上说,秦腔也称“乱弹”,唱腔音色高亢激昂,要求用真嗓音演唱,所以保持了原始豪放的特点,角色可分为:老旦、正旦、小旦、花旦、武旦、媒旦、老生、须生、小生、大净、毛净、丑角等十几种,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经秦到明历代发展日趋成熟,明末清初盛行于南北各地,对许多剧种都产生了影响。主要流行于西北各地,深受群众喜爱,所保留的剧目达700多个,为各剧种之首。
秦腔中故事情节很常见,但是它却浸透了传统的文化,更寄予了人们对社会的期望。从一出又一出的秦腔戏文中,乡亲们自小就接受了忠、孝、仁、义、礼、智、信的熏陶。别看不识字,唐、宋、元、明、清朝代更替搞得清清楚楚。说理劝架、批评教育小辈,肚子里有的是戏,张口就是一段戏文。
再大一点,“文化大革命”来临,就在1970年,一场全民学习革命样板戏,演出革命样板戏的政治运动在三秦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很快秦腔《红灯记》就问世了,《红灯记》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是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战胜利而不惜牺牲生命进行英勇战斗的真实写照,它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剧中展示出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对敌斗争的坚贞不屈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在马额中学上初、高中时参加了文艺演出队,在戏里扮演李玉和。舞台上,当李玉和说出那句“铁梅,扶着奶奶,我们一起走”,三个背影走上那节残垣断壁的刑场,我完全融入其中。李玉和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永远是激励着我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坚持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且积极投身于实现理想的伟大实践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组建了文艺宣传队,任队长,并主演《山鹰》、《杜鹃山》。在周边的乡村巡回演出,我把当时的八个样板戏背得滚瓜烂熟,我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秦腔,让我感悟最深的还是在秦腔样板戏中所学到的知识与领会到的精神,戏中的英雄人物一直激励着我。
1977年,西安率先在全国恢复演出传统戏。这时的我虽然离开了农村,但秦腔中的众多经典曲目,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不厌倦。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在《劈山救母》中懂得亲情的可贵,在《白逼宫》中感受汉献帝的凄凉,在《双关诰》(《三娘教子》)中了解母爱的伟大……特别是在《周仁回府》中,周仁为杜文学而献妻救嫂、被误解受杖责、到亡妻坟头哭诉的场景深深地感染了我,也让我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兄弟互助的情义,并时刻怀知恩图报之心。我把自己融入了秦腔,以自己的声音吼出秦腔的精神和气节。
这么多年来,无论我身居陕西,还是远离家乡,我都离不开秦腔,在1985年第一次离开陕西时,专门用120元钱买了一部三洋录放机,用磁带设法录上秦腔戏,才踏踏实实离开家乡。2005年,当我又一次踏上异乡的土地时,行李箱里除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大堆自己录制的秦之声VCD,披着岁月的尘埃,穿过厚厚的历史,吼一声“祖籍陕西韩城县”,唱出了秦腔戏曲的骄傲,更唱出了来自黄土地的自豪。听秦腔不仅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休息,更是一种反省与洗礼!
我爱那古老的秦腔艺术瑰宝,胜似爱过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