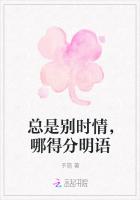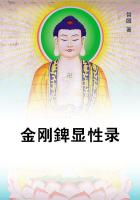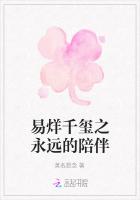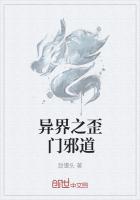2004年1月写于华东师范大学一村
仁者蔼然
周克希
想起辛老,眼前就会浮现他满含笑意的脸容,心头也会漾起一丝令人怅惘的暖意。
因和圣思同在华东师大,有幸结识了辛笛和文绮先生。当时我在数学系任教,但热衷于翻译文学作品,可以说正在兴头上。译林版《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后,我和其他多位译者同赴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行前去向辛老辞行。他知道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就主动为我写了两封引荐信,一封给冯亦代先生,一封给汪曾祺先生。到北京后,我按辛老的叮嘱,拿着他的名片和信,分别去二位府上拜访。心仪已久的前辈的勖勉,坚定了我投身文学事业的决心。
下一年,我改行离开数学,调到出版社担任文学翻译的编辑工作,这样一来,就跟从事文学翻译的初衷“虽不中,亦不远”了。
隔没多久,我应约准备翻译《追忆逝水年华》节本(书名换了一字),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去看辛笛先生。我现在还记得,他在桌子那头笑眯眯地望着我,那笑容使我感到温暖。我觉着,尽管我笨嘴拙舌的,但我的思绪他是洞明的,我的感受他是理解的,我的忧虑他是体谅的。我俩谈了很多。最后辛老建议我多看看废名的小说。辛老把普鲁斯特小说的语言特点归结为“缠绵”,而废名的作品,在他看来有相似之处。
过了些年头,我痴心未泯,又着手重译普鲁斯特巨著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辛笛先生静静地(带着智者的微笑,我相信)关注着我和我的译事。我偶尔有些不值一提的文章见报,几乎每次他都会在当天或第二天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读了小文后的感想。漫长的译事使我感到寂寞甚至压抑,辛笛先生的话,犹如为冷寂的心田引入一股暖流。
如今,再也接不到这样的电话了。而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每当走过南京路陕西路,我总会在那条弄堂口驻足。以前我常在这儿打电话上去,说已在弄堂口了,问这就上来好吗。我真想再当一回这样的不速之客。可是我明白,即使登了门,也见不到二位长者,见不到那蔼然可亲的笑脸了。
2004年10月
叹辛笛
锺文
我与王辛笛老人的“认识”最早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每周末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拐一次福州路,泡在旧书店里淘旧书。这是一周中最幸福的时间,用穷学生仅有的零用钱买几本便宜又喜爱的书,如同阿里巴巴洞穴中寻宝一样的刺激。
我记得那天是已近中午了,在一大堆混杂着书香与霉气的书堆里,我突然发现了一本薄薄的书:《手掌集》,作者辛笛。随手一翻,是一首《航》: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
当时默念着这几句诗句,心里突然有一种心灵猛被刺醒的感觉,有一种开启了一个新天地的冲动……但这个名字———辛笛,老师、课堂、书本从未提及过,这是哪方神圣?
当时我沉迷于中国现代新诗,从《尝试集》到徐志摩,几乎能找到的诗都拿来拜诵。但从来还没见过一个诗人是这样写诗的:如此的意趣,如此的遣词,如此的意象,明明白白是一幅法国印象派大师的画作。那么造新,那么刺激,在我阅读新诗的经历中有此感受的并不多。
我视这本《手掌集》是一个宝贝,连续翻了两遍,吟了又读,几天时间陶醉在这本薄薄的诗集中。辛笛这个名字就像这样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我很疑问,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当时的诗歌评论的刊物也没有提及这个人。按捺不住之下,我问了当时我认为在现代文学上还有些研究的一位老师陈瀚先生,他的反应很快,说:“这个人四十年代写过一点诗,后来就不见了,不知现在安在。”我又问:“他的写诗方法非常奇特,怎么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他的名字呢?”陈瀚回答:“你不懂,你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去作这种钩沉寻秘,那就有大把的说不清了。”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那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来,又盘旋去。一个完全用如此创新手法写诗歌的人,怎么竟然在中国文学史上连个提名字的地方都没有呢。以上是我第一次认识王辛笛老人,但不是与他本人见面,而是首次读他的诗被冲动了。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封面是九片绿叶的嫩绿。王辛笛的名字,赫然在第一位。我才知道,他们是一批“出土文物”,被埋葬了整整四十几年,终于出土了,而且是这么一批有全新创造,特殊风格的群体。后来又从朋友那里知道了,王辛笛不但活着,还活得很不错,住在上海南京西路花园公寓。经朋友介绍,我拿着当年觅到的宝贝《手掌集》敲门访见了王老和他的夫人———一个让人能够有天然亲和力的,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曾是个大美人的徐文绮师母。记得那天谈了很多很多,从诗谈到人,从人谈到这个世界。总之这是一顿思想的大餐。接着的午餐是在他家旁边的梅龙镇饭店吃的淮扬菜。王老把《九叶集》中的很多人的联系电话、地址给了我,于是我很快地就进入了他们这批与我年龄有蛮大距离,但在艺术趣味与做人爱好上又距离很近的这么一批老人。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摄于北京陈敬容陋狭的房间里的一张合影。里面有郑敏、袁可嘉、唐祈等。几个老人与一个中年人挤在陈敬容的床沿边合的影。陈敬容虽然清瘦孱弱,但笑容灿然;郑敏气质高雅,挤在床边作含笑状;唐祈作为年轻时的美男子,一点不减当年的神态;袁可嘉是弥勒佛似的笑态……今天,其中不少人已走了,默默无闻地走了。偶尔拿起这张照片,真让人唏嘘不已。
1985年,香港召开一个香港文学研讨会,大陆就邀请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王辛笛。我们不约而同地去了香港,又同住在香港大学招待所的一个套间里,接触的时间长了,当然谈的话也多了。从他的出身,家庭,到出国,到解放,“文革”等等。
总的来说,王老的一生相比较他这样年龄的知识分子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虽然“文革”中抄过家,但总体,比较平平稳稳地过来了。问题是:如此一个英美文学的海外留学生,一个诗才,一个学贯中西,古典修养深厚且西学也特别精通的人才,在整个中国文学界也是翘楚中的翘楚,但解放以后却去做了啤酒花的采购工作。
我把此问题问王老,王老说是自愿的。自愿的!这是一种怎样的自愿?那是不是惊吓于时代周遭的环境与压力,品出了悲与欢的因果无常关系以后,不得不为之的自愿吧!他突然从一个文学之神的崇拜者转而生活到一个只是偶尔写写古诗,也不传之于人这么一个份上去了。他的确是谨慎得很,胆小得很,但从深处想,还是很有道理,也很有远见,所以才换来了平平稳稳,没有大的坎坷,没有大的痛苦的一生。对时代而言,这真是一个浩叹。对他个人而言,则又是一个万分的幸运。王辛笛,从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作及当时一帮世界级的现代诗人,如艾略特、霍普金斯、奥登对他的直接影响,直接的文学哺育。有如此的天赋,又有如此好的后生教养,理应是能开一个中国现代诗歌潮流的大师,但刚刚开了个头,就引身而去了,不知去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知道他这几十年是隐身在一个国家公司里做啤酒花。
1985年我与王辛笛在香港文学的研讨会上,都作了长篇发言。我讲了当代的中国新诗的状况,与香港的当代诗歌作了一点比较。王老的发言是把香港文学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这一辈诗歌的承继关系作了比较。出席这个研讨会的人大多都知道王辛笛,因为基本都读过他的诗歌《手掌集》等的香港“盗版”(“文革”间,不知从何渠道获知王老被“革命”而死,香港的诗迷们于是从互相传抄《手掌集》到干脆自己影印《手掌集》。)香港的这帮王老的崇拜者(包括香港当代文学中颇有声名的黄继持教授、卢玮銮教授、梁秉钧教授、叶德辉先生等。据他们介绍,他们在“文革”中曾得到消息,说王老被红卫兵斗死了,于是他们在香港还开了一个王辛笛追悼会,缅思王辛笛的生平与诗作。他们还介绍台湾著名现代派诗人痖弦先生十足是王老的追随者。据痖弦自己向外人说,他当年抗战爆发开始逃难,匆忙之中什么东西也来不及拿,就怀惴了一本《手掌集》出外流浪了。痖弦的诗作开了台湾现代派诗的先河。恐怕追溯起来,这个弄潮儿的发动现代诗潮的最早源头可能就是《手掌集》中的《航》吧。)这次研讨会上有不少人是从香港报章报道王辛笛参加“香港文学研讨会”而寻来拜会这位世纪老人的。开会、发言、宴席,五天时间我们就这样紧紧张张地过了。王老那时已经七十几岁了,说话有哑声,但中气还旺。
只是一天晚上被香港朋友宴请回来,我看他的脸色阴沉,心情不佳。第二天他告诉我,昨天见到的是原来他在上海金城银行做襄理时候的一个部下的部下,这次闻听王老来港,这位银行里人摆出一个香港金城银行负责人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宴请原来的上司。王老肯定对此联想对比多多,当然形成了坏心情。王老当年是可以随银行去香港的,但他为爱国留下了。还把家里人的全部在海外的遗产十五万美元捐给了国家。当时的政府开始还不敢要这笔巨款,王老一家坚持再三,政府才收下。记得20世纪80年代这个消息方始在报纸上宣传,但这一宣传却使王老应接不暇了。写诗人大凡是穷的多,“诗之工后穷”嘛。听闻这个消息,不少年轻人纷纷给王老写信,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资助。他们的推理很简单———你当时捐了十五万美元,肯定是自己留下了大块,给政府捐了小块。那么,王老无疑是诗界的特大富翁。无奈之下,王老还是资助了不少。据我了解,他那时候经济状况已有点窘迫之感了。拿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工资,生活按八十年代的生活指数,窘迫了还不敢说。
我亲自听唐祈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老的确是上海滩文艺界有名的孟尝君,家里有车夫、厨师、保姆。那个扬州厨师还烧得一手好菜,于是千里有朋友常来他家白吃白喝白住。唐祈向我自夸,他就是个中人。联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王老与我见面时,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连买书订报都要计算而又计算了。当然,王老夫妇是乐观人,2003年初,我又去拜见这两位老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跟我说,他们要比赛活到九十九岁,我听了由衷地高兴。
后来两位老人相约而去,只相差四个月不到,在另一个地方他们还要笃爱相伴,可见他们是必须相伴而生的。
实在而言,我认识他们,面对他们丰富又可敬的一生常有后生有愧的感觉。但是另一层感觉是,隐失一个中国现代诗派的当然领袖,多了一个做啤酒花的经理,这人生的颠倒也实在让人气结而可叹。
又记:不作笔耕已十五有年,手疏得都让自己生气。向读者致歉。
2004年9月
你是我们中间的先知
———纪念诗人辛笛先生
子张
一
说来惭愧,我最早接触辛笛先生的诗竟是在大学毕业,教了四年中学语文之后。回想原因,可能是1979年前后的“新文学史”教材中还没有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内容供我们阅读,课堂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我读的是专科,1981年6月毕业后,随即被分配到基层中学,与同年7月出版的《九叶集》也失之交臂。而那时的中学语文教材更是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
1985年初秋,我奉召返回母校,跟随刘增人老师为新生讲授“现代文学史”并参与编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按照作品编选要求,我负责两卷书中的“下册”,给每篇入选作品配上几百字的“题解”,这才第一次读到《风景》这首写法很别致的诗作。我很惊讶,怎么可以把“铁轨”想像成“中国的肋骨”?又怎么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特别是结尾那个斩钉截铁的否定:“都是病,不是风景!”更是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象。
那个时候,图书馆里已经有了《辛笛诗稿》,但是《九叶集》却仍然没有找到。后来读到这本书,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山东师大进修的时候了。
其实,我相信类似我这种阅读经验,在当代一定有相当的普遍性。回头来看,自从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何曾有过一部新文学史客观提及或评价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作?即使到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八十年代,限于人们观念的偏差、态度转变的艰难以及图书发行等工作的滞后,文化中心地区以外的普通读者要想及时了解文学界的最新动态,又谈何容易?
即以辛笛先生和他的著作而言,他在1948年的《手掌集》《夜读书记》出版后,在大陆就出现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出版空白期。然后在1983年诗人七十岁以后,才陆续有《辛笛诗稿》《印象·花束》等新集问世。迨至更多诗选集和旧诗、散文随笔集印出,诗人已步入暮年。这固然也表明了辛笛先生创作生命力的强盛,但同时不也折射出世事的某种荒谬性?正是这种荒谬性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作家创作力量的极端不平衡性。一些作家未老先衰,另一些作家的创作力则呈马鞍状,开端和结局尚好,中间最宝贵的黄金时段反而是一片空白。当然,能够赢得一个平静、安适、智慧的老年毕竟是幸运的,但仍然无法不为他们被迫丧失的年华而深感惋惜。
二
辛笛先生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大都属于后者。他们共同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写作观念使得他们的创作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他们也像热爱诗歌一样深爱着祖国和人民,但还是不能避免被疏离、被边缘化的政治命运。因此,在一个排斥个性、拒绝理性而崇尚迷信的时代,辛笛和他的诗友们群体性地消失了。
然而,当历史发展恢复常态之后,作为诗人的辛笛,在他的老年却以不多数量的诗歌作品受到海内外诗界高度的尊重。他和他的早年诗友们的写作经验不但得到青年诗人的垂青,也成为诗学学者们再三研究的对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对《九叶集》诗人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显学。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些诗人诗作所具有的先锋精神和独一无二的个性魅力倾倒了新生代的诗人和学者们。
这使我想到一句话:众芳之中,以特色之花最为珍贵。
关于辛笛诗歌创作的个性,人们已经做了许多总结和探究,这里不拟多说。我只是觉得,在现有的成果之外,仍然有许多观察角度可供选择,也仍然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