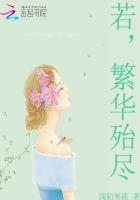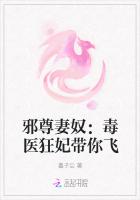在这种情况下,杰克·伦敦理所当然地自认为强者、超人、英雄、良种,对兽性充满快感,面对生活中的弱者,鄙视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情不自禁的习惯,即使对美国本土受压迫的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的同情都夹杂着蔑视的成分。他和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没什么区别,极力主张白种优越性,认为白人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地球的一半和海的全部都是它的世袭财产”,白种命定永远统治红种、黑种和黄种,甚至宣称“社会主义不是为一切人类所设计的理想制度,乃是为一种族的幸福设计的,设计的目的在给那些优秀民族以更多的力量,以便他们在弱小种族绝灭时存续和承继世界。”
毫不奇怪,由于头脑中白人优越论的不断膨胀,当杰克·伦敦面对那些在美国被压得直不起腰来的中国劳工时,很自然地视中国人为“劣等的民族”和“黄祸”。这是他最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同时同生活经验也有关系。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和西部海岸的中国移民有接触,了解到有关中国和唐人街的事,当然都是些负面的印象,像中国人靠捡破烂过日子、出大价钱买野猫肉好有力气打群架之类。17岁时,他从窃牡蛎的小海贼摇身一变为巡航队的海警,曾赤手空拳与一条中国船上的10多个冒险者搏斗,最终出奇制胜,得到100美元的奖励,这次侥幸的胜利也给了他蔑视中国人的资本。不用说,19世纪中后期美国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的排外主义和反华排华浪潮也为他的偏见提供了一个历史语境。但杰克·伦敦本人的视野是最关键的,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他的态度和马克·吐温截然不同。
丑陋的《中国佬》
杰克·伦敦涉及中国和中国人题材的作品有《白与黄》(1906),《黄手帕》(1906),《中国佬》(1909),《空前的入侵》(1910),《陈阿春》(1910),《阿金的眼泪》(1918)等六篇。虽然数量不多,却从各个方面描写了中国人的丑陋形象,也暴露出他本人的恶劣心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中国佬》。
《中国佬》的情节很简单,但中国佬的形象却很鲜明,让人难以忘怀,杰克·伦敦非常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劳工逆来顺受,让人震惊的精神麻木的形象。故事发生在太平洋上一个法属小岛上,愚蠢残暴的白人法官没有抓住真正的凶手,却将几个目击者判了死刑和其他徒刑,蒙冤者和500名劳工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却私下里秘密达成协议不出来作证,因此无人肯吭声。杰克·伦敦紧紧抓住中国劳工的一个显著的精神特征——沉默,这个特征在面对与白人发生冲突时尤其明显,正如一群羔羊面对一群饿狼时一样,杰克·伦敦将中国人放在一种沉默的牺牲者的角色上。
当错误的判决作出以后,中国劳工像木偶一样,没有表情,那些蒙冤者被押回监狱时既不感到震惊,也毫不悲哀。始料不及的审判,在他们与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已习惯了,中国人不可能期望别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种并没犯罪遭到的惩罚并不比白人对他们平时所做的稀奇古怪的事更奇怪。被判死刑的阿周(AhChow)坦然地接受一切,照吃照喝照睡,并不担心时间缓缓的流失。中国劳工的唯一表现,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因为他们觉得任何申辩和反抗都是徒劳的。惹恼了白人洋鬼子,只能遭受更大的灾难,他们在异国他乡从来就是无助的,从来就没有期望也不可能期望得到什么,唯一的方式就是认命,保持沉默。这是何等悲哀的民族!杰克·伦敦在小说中反复描写和渲染中国劳工哀而不怨,麻木不仁的神情——一种无表情的神情,活画了中国人沉默的灵魂。
在这群沉默的劳工中,目击者阿卓(AhCho)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个。
凶杀与阿卓本来没有关系,但因为他出现在现场,所以被判了20年徒刑,对此,他心中未能激起半点愤慨,他的态度就是接受它,并不感到烦恼,20年就是20年,他还很年轻,亚洲人的忍耐性铸就在他的骨头里,他完全可以等20年,即使他的青春已经消失。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狱中的牢头却将他和被判了死刑的阿周混淆起来,错认他是凶手。当他进行辩解时,反而遭到了残暴的鞭打,于是他不再作任何辩解。他非常清楚“白鬼子”对中国人的态度,这不过是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件,命运的主宰对他所做的一切,他只有接受。对于中国劳工来说,他们对白鬼子的理解之少,就如白鬼子对他们的理解之少一样。尽管如此,阿卓在被当做死囚押往刑场的最后一刻,仍作了最后一次毫无用处的申辩,但立即他又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本来不属于他的可悲安排。阿卓明白,在这群野蛮无理、愚蠢残暴的白鬼子面前,中国劳工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和阿周谁死都一样,而且他无论死或活也都是一样,因为中国人的生命在白种人的眼中一文不值。所以,阿卓最后被绑在行刑板上时,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他没有愤怒和悲哀的表情,也没有做任何徒劳的挣扎,就像在做游戏,地平线在他眼前倾斜,他倒下去,自然而然地闭上眼睛,仿佛平常在黑暗中睡觉一样,既无面对死神的恐怖,也没有“20年后又一条好汉”的感慨。他茫然到极点、出奇的平静。杰克·伦敦特意描写了阿卓临死前最后一瞥的幻觉:
阿卓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花园,这是他的天堂,在这天堂里风儿轻拂着他的身体,从远处飘来小铃铛柔和悦耳的响声和婉转动听的鸟鸣,还有那田园上缥缈的牧歌,农家鸡欢犬闹的交响乐……
这个流落异国他乡的可怜人,在沦为冤死鬼时尚有如此美好的憧憬,这应该让人们感到悲悯呢?还是觉得他愚蠢?无论如何,杰克·伦敦笔下的字里行间,多多少少含着一点同情,但更大程度是以一种厌恶和鄙视的心理叙述着中国人的懦弱和麻木的。这种叙述带着残酷的成分,它对读者的心理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作用,无论对白人,还是对中国人,都是一个抹不去的火红烙印:中国人竟懦弱和麻木到如此不可救药的程度!
在杰克·伦敦看来,中国人不过是在荒野中被凶猛的狼群包围着的可怜而无望的羔羊,根本无法改变自己可悲的命运,只能充当历史舞台上麻木的沉默的看客和被杀头示众的标本,这是劣等民族必须接受的现实;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弱国子民的悲惨境遇,使他们精神上无法强大起来,他们可以忍受自身在别人看来无法忍受的痛苦,却没有能力改变主宰自己命运的外在的力量,他们唯一能采取的方式就是忍受、沉默。尽管不在沉默中爆发,那就将在沉默中毁灭,但他们仍宁肯选择沉默,因为觉得爆发也无济于事。
杰克·伦敦视野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一定程度上确实是19世纪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日益衰败到极点时的一种镜像。这种镜像在稍后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笔下也有描绘。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就不止一次见到了那些沉默得可怕的看客,和同样沉默得可怕的示众者:《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药》里的华老栓,还有如鸭子一样伸长了脖颈张大了嘴的群像……但根本的区别在于,鲁迅怀抱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他描写这些,是要做醒国人的灵魂。杰克·伦敦却绝无此意。虽然他的作品客观上也反映了华工在西方世界悲惨命运的真实,并将这种悲惨命运形容到极致,反映了中国劳工和统治与惩处他们的法国殖民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如中国劳工始终叫法国人“白鬼子”),但从不曾也不可能考虑过如何让移民而来的劳工在政治上觉醒的问题。他对中国苦力精神状态准确而带着自然主义色彩的描绘,始终未偏离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半步,在把握中国人的沉默灵魂时显然夸大了中国人的弱点,使其成为“白人优越论”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形象化注脚。杰克·伦敦这一类小说里的中国人形象是丑陋的,他自己的心态也同样是丑陋的。
事实上,中国人面对压迫和侮辱,并不如杰克·伦敦刻画的永远只剩下沉默。至今在旧金山海湾天使岛上当年关押遭刁难的移民的小木屋的墙壁上,还保留着蒙难者写下的控诉诗行:
为何来由要坐监?只缘国弱与家贫。
椿萱倚门无消息,妻儿拥被叹孤单。
纵然批准能上埠,何日满载返唐山?
自古出门多卑贱,从来征战几人还!诗中,“椿萱”喻父母,“唐山”指中国。这首无名氏的诗作,感叹着国势家运,惶恐着前途的不测,可谓字字血泪,不正是对美国当局对中国移民的无端歧视的有力抗议吗?历史还告诉我们,1904年4月,当美国国会准备将1884年订立、1894年延长有效期的排斥华工的禁约进一步永久化时,在美华侨、华商和华文报纸立即表示反对,并要求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最终爆发了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以抵制美货为手段的抗议运动。中国人民怒吼了,只是被野性堵塞头脑的杰克·伦敦似乎充耳不闻。
“黄祸”的梦魇
杰克·伦敦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描写,当然不限于中国劳工,他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指向所有的中国移民,甚至整个中华民族,这种倾向在文学想象中,最终发展为将中国人妖魔化成“黄祸”,让黄种人最后战胜并吞噬白种人。杰克·伦敦仿佛患上了狂想症,幻想着来自中国和中国人的威胁。正因为如此,他作品里的中国人性格并不作为某个个性特征、某种心灵世界的负面而遭人嫌弃,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总体性格遭到仇视和憎恨,个别中国人永远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堕落民族的总代表。这显然是极端化的偏见。
《白与黄》和《黄手帕》两个短篇,是杰克·伦敦根据他当巡航队海警时与中国人发生的那场遭遇战的经历写出来的,在他扭曲的眼光里,中国人继续是怯懦、凶残、狡猾、丑陋的一类人。其中一篇用了“白与黄”的标题,显而易见具有象征性,意指着白种人、黄种人之间不同种族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陈阿春》中被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小说写一个中国商人在夏威夷与一个白人妇女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送到哈佛等名牌大学接受教育,而他自己最终却抛弃妻子儿女,只身回到中国,因为他离不开那里的故乡。这是最早描写中国人与白人通婚的故事,某种程度反映了实际生活中不同文化族群混融的现象(通婚是造成这种混融的最常见途径)及导致的问题,所以有一定价值。但杰克·伦敦侧重表现的是中国人无法适应西方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守土重迁”的劣根性导致不同文化结合的失败,把不同文化冲突的不可调和归咎到中国人身上。《阿金的眼泪》则夸大突出中国人逆来顺受的懦弱性格。主人公阿金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母亲信奉“棒打出孝子”的信条,总是用棍棒来教育他,而他从来不反抗,但终于有一天母亲打不动他了,阿金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痛哭失声,因为阿金就像长不大的孩子,离开了棍棒的教训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找不到自己的生活方向。这篇小说其实也是一个恶毒的寓言,无非影射中国同样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幼稚民族,除了接受别人武力的教训,不配有任何别的出路。在这里,杰克·伦敦一贯以盎格鲁一撒克逊高等民族自居,而居高临下地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丑恶嘴脸暴露得再充分也没有了。
然而,尽管杰克·伦敦对中国和中国人满心眼的瞧不起,他仍然忧心忡忡,警惕着有朝一日“黄祸”会蔓延。这种矛盾的心态集中体现在《空前的入侵》这部小说中,也可能是从1904年一直延续到1906年初的抵制美货运动让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触发了0他的隐忧。但和其他中国题材的作品不同,《空前的入侵》具有科学幻想的性质,类似今天的科幻小说。在这方面,杰克·伦敦当之无愧是个发明家。除了所擅长的阿拉斯加故事,他短暂一生开创了许多小说新题材,如史前史、启示性灾难、未来战争、技术统治下的乌托邦等。不过无一例外,这些作品基本都反映了他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除个别作品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外,意在强调天生优越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有无限开阔的上升空间,以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法性。
《空前的入侵》把杰克·伦敦一贯的思想结合到可怖的“黄祸”的主题里。时间定格在1976年,这一年是美国独立200周年,但纪念和庆祝活动被推迟了,原因是中国和世界的尖锐矛盾达到了顶点,一触即发,危在旦夕。其他许多国家的计划和安排也由于同一个原因而被打乱,全世界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中国原来是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家,土地富饶,人们勇猛好斗,依靠他们的勤劳和日本在亚洲传播的技术,突然之间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但威胁首先来自人口。在杰克·伦敦的想象里,中国仅仅靠众多的人口,就危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存在。无数的中国移民定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这股恐怖的泛滥的洪水,即使常规战争也毫无作用。于是科学家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细菌战的方法,将传播瘟疫的细菌设法从战船上射向大洋彼岸,然后疾病、骚动、饥饿阻止了中国人的侵略野心,来自中国的威胁被排除了,整个中国也成了一个地狱般的场所,并陷入消亡。通过这个构想,杰克·伦敦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的偏执见解:中国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潜在的危险,一旦中国变得强大了,就会引发战争,而中国移民就是侵略的别动队。
在杰克·伦敦对中国充满怪诞想象的预言中,中国的可怕还在于其文化,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组织是用完全不同的东西编织而成的,他们对于白人来说是精神上的异己。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的进步与成就不曾给酣睡中的中国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办法把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人的头脑。中国继续沉睡,西方文明的进步与成就对她来说是一本合上的书,即使是西方人也不能为之打开。在这里,杰克·伦敦充其量是重复了某些顽固僵化的传教士的谰言,继续攻击中国人冥顽不化,似乎只有武力征服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