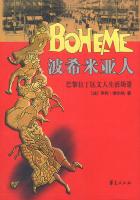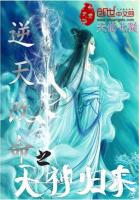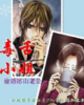就像斯诺说的,新的生命总是先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蠕动,新的文明也总是先在思想和情感的层面孕育。通常以为,文明的积累和创造要经过物质劳动而实现,却往往忘记了劳动者是有心灵和感受的人。当人们日复一日似乎在重复最基本的劳作和活动时,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渴念也就油然而生了。由此导致了激发和构想、反观和沉思、欣悦和痛苦、想象和梦境等种种可能性。
有一种文化的沟通,就是在哲理和诗美的领域发生的。可以认为那是超越于实际利害之上的,或更确切地说,离开功利得失的计较更为遥远。在这种情况下,审视异己文化的眼光就换成了审美性质的,也更多体现出偶像化的倾向。它会集中从对方发现符合自己意愿的理想,或者自以为是理想的东西。有时也表现为排他性的选择,只摘取合心意的东西,其他的就一概视而不见。用现实的眼光看,那多少有点缥缈,有一点玄虚,却是一不同文化之间最真诚的契合,因为事关心灵,排除了别的东西的干扰,直逼人类最隐秘、也最可能是相互共同的天性。
这一沟通过程也更多地渗透了思想的创造和精神的飞跃。外来的文化因素更像星星火种的触媒,燃起一场熊熊大火后,从灰烬中哄要起飞的是双翅鼓动着全新神采的凤鸟。不过仔细辨认,依然能够在亮丽的羽翼下,找到所吸纳的异域精华。当然,那些精华已融贯在血液中,化为了精魂,就像盐入于水。同样的道理,哲学家或诗人还有别的众多的思想渊源或艺术宗师,还呼吸着世界范围的新空气。即便哲理和诗美彼此携起了手,也不会是简单的一对一。
1.超验的隔连:爱默生和孔孟之道
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是较早为中国古典文化吸引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在创建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接触并钻研了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对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不过他对同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则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作为19世纪美国优秀文明的代表人物,爱默生独特的个人文化立场,是相当耐人寻味的。这表明,美国的作家在接触中国文明的最初时刻,就并不只带着单一的视点。情况的复杂并不是某一个简单的文化交流模式就能说明的。
心灵信仰之需
爱默生属于以自己的天分感应时代潮流的先知先觉者。他一生的经历,既鲜明地体现了他不同寻常的个性,又极为典型地反映了19世纪中期美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觉醒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同加尔文主义清教中继续束缚人的传统教条进一步决裂,二是对正在兴起的城市工商文明保持警觉。爱默生倡导的先验主义和在他影响下深入发展的后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
爱默生出生于美国东部波士顿的一个神职人员世家。这里属于新英格兰,是清教徒涌入北美大陆的最初登陆港口,也是他们按照加尔文的训条建设政教合一的新社会的大本营。父亲威廉继承先辈的志向,在当地最有名的属于“一位论”(Unitarianism)派的第一教堂做牧师,母亲是虔诚的信徒。爱默生先在波士顿拉丁学校学习,然后从哈佛大学毕业,进了该校神学院研读了一段时间,不久离校担任神职,接着进波士顿第二教堂当初级牧师。他才思敏捷,善于辞令,很快赢得了教堂会众们的好评。不过人文思想也和宗教信仰一样,交织在年轻的爱默生心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冲动,有时他雄心勃勃,“要在神学方面有所建树”,有时又在《日记》中公然写道:“蔑视祖先是我的禀性。”在传教布道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爱默生性格中的首创精神和反叛因素越来越发展,终究导致了他同保守的清教势力乃至整个教会的决裂。
爱默生不想被动地接受现有的观念和思想,在哈佛神学院求学期间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反思了基督教的精神传统,在主要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清教进人北美两个多世纪后,考察了它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现存的教会已离开了真正的基督教,只能称为“传统的”或“历史的”基督教,故而存在着两大弊病:一是对个别人物和形式仪式过分夸大;二是将启示看做“久远已毕之事,好像上帝已经死去”。所以教会只会照搬福音的词句,却不会遵循它的精神。他毫不留情地指出“神坛已经被形式主义者所窃取”,对“各教派和教会所遵循的虚弱的常规、纯粹的文字学问和礼仪之道”表示蔑视,尖锐地指出:“时过境迁,我们却仍然按照祖宗的死规矩在礼拜。”他认为,目前的教会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权宜之计,而非精神所需;对教徒而言,教会不过充当了警察的角色。牧师们的布道方式也极其枯燥无味,不是出自灵魂,而是出自记忆,根本不具有把人引向上帝的真信仰,相反满口俗套导致对上帝的亵渎。因此他对牧师职业充满反感,即使是他自己担任的牧师之职,也认为是他自我中最不足道的部分。
为了让人们重见“道德真理的神圣之美”,爱默生提出,历史的基督教必须取消,而代之精神的基督教。所谓“精神的基督教”,实际就是人的灵魂对道德情操的追求,灵魂的内在光明才是直接受之于上帝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那灵魂的名字,那灵魂处于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中心,而我们的存在就是他的证明”。上帝也即等于真理、生命、良心、道德理想,“心灵深处的精神悟性”。由此,个人与上帝的交流中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人,包括教会和牧师的存在都纯属多此一举。
基于以上见解,爱默生从当牧师开始,就采取了一种在普通人看来是非常规、非正统神学的风格。他第一次布道,便宣布教会的工作在于教导如何正确地生活,而不在于传授宗教信条;第二次布道时,又明确表示他无意充当教会的警察。1832年,在担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三年后,更进一步向教会当局正式提出要求,停止按当时通行的方式来主持圣餐仪式。这一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接受,随后他递交了辞呈,并最后一次作了题为《圣餐》的告别布道。
辞去神职后,爱默生怀着寻求新的思想理念的憧憬,去欧洲游览。短短一年时间里,他结识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并同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建立了终生友谊。通过这些交往,他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的影响,更坚定了自己张扬个性、激发个人心灵力量的信念。1833年秋从欧洲回国后,他开始了演讲者的新生活,四处宣传自己的思想见解,并于第二年回到祖籍所在地康科德,在他度过了童年及后半生的地方创立了“超验主义俱乐部”。1837年,他在哈佛神学院的布道演讲中对现有教会制度展开了最猛烈的攻击,公开宣布了他的新思想。这次演讲犹如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惹恼了哈佛神学院的保守派,大批教会人士群起而攻之,也意味着爱默生与教会最后的决裂。从此以后,母校哈佛将这个逆子拒之门外达30年之久,爱默生也再没作过一次布道。他既然作出了选择,当然义无反顾。
爱默生的做法具有离经叛道的性质,也从观念上和体制上对清教势力的统治秩序提出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是孤立的。19世纪初期,美国宗教界内部已再次出现改革的势头。相对于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它也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遍及于各个教派,基本倾向仍是通过富于煽情色彩的传教布道,让信徒投入到情感的兴奋中,以此体验上帝的存在(为此也叫“兴奋运动”)并皈依宗教,不过要求做得更理智更有节制,以避免上一次“大觉醒运动”过分放纵感情的缺失。“第二次大觉醒”本身就是对逐渐僵化的某些清教教条的冲击,它继承和发扬的情感主义以主观情绪和体验代替客观的公理标准,使信仰的对象、内容和仪式都转向相对化,暗中销蚀着教会组织的绝对权威,当时在各教派内都引起了分歧和争议。爱默生的挑战可以说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另外爱默生的反叛思想,也是一种信仰逻辑的必然发展。他和他父亲所属的“一位论”派,原来就是清教自由主义的一翼,反对人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说”,批评加尔文主义的人类获救与否由上帝决定的“预定论”,强调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得到拯救。爱默生把道德理解为宗教的真髓,并依靠个人心灵悟性的努力以实现和上帝的沟通的主张,实际和上述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爱默生的贡献在于把信仰和道德问题从教会的范围中解放了出来,将它们归结为纯粹属于个人的事。这一个人通过灵魂和大自然发生联系,而大自然就是上帝无处不在的沉默的福音,世界也就是沉积下来的心灵。这就是超验主义的要旨,在爱默生心目中相当于有待建立又一新宗教。在这里,除了浪漫主义的自然崇拜和卡莱尔式的神秘唯心论外,相当鲜明地突出了作为美国文化精魂的个人主义。人为着自己的德性,从自然获得启示,并对上帝负责。但这一个人又是开放的,正是有鉴于清教各教派的狭隘和浅薄,他需要冲破所有的限制,踏平基督教和异教、东方和西方、现代和古代之间的垄沟。就像爱默生大声疾呼的——
为了表达德性的本来含义,我们有必要大大越出自己的环境和习俗。否则的话,它立即就会同可怜的体面和空虚混为一谈……由此,我们飞向异教徒,引用苏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琐罗亚斯德的名字和有关人事……
于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在超验主义的旗帜下,爱默生进一步把目光放远到欧洲以外的国度,从更广阔的天地汲取有益于道德建设的思想养料,包括东方和中国。如同西欧的浪漫主义一样,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萌生了强烈的异国情趣,对东方文化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钟爱。爱默生和他周围的朋友们作出极大的努力去了解地球另一边的世界,他们博览群书,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异教的东方。在这个令人激奋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对那块遥远的大陆产生了亲切的感情。爱默生甚至为他的妻子莉蒂亚找到一个爱称:“我的亚细亚。”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刊物《日晷》专门开辟了题为《各族圣经》的专栏,连续发表了东方圣哲们的语录,其中包括印度波罗门教的《摩奴法典》、佛教的《佛陀经》、波斯教的《琐罗亚斯德神谕》、中国古代儒家的《论语》和“四书”等。爱默生和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们俨然成了东方各异教的传教士。
究竟是什么让爱默生胸怀如此开阔,兼收并蓄地包容东方不同的异教世界呢?关键是爱默生对于宗教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基督教的单一的狭小门户。在他看来,种种宗教信仰原不过是共同的人类关注和道德情操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共同的人类关注和道德情操“便是一切宗教的欣悦与结果,便是将所有形式去除后一切宗教留下的内核。这是律法中的律法,是吠陀、琐罗亚斯德、古兰经、毕达哥拉斯的金诗、圣经、孔子”。爱默生深信,每种宗教都是道德法的一个不完善的版本,基督教也不例外,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他广泛地搜集“世界圣经”。他欣喜地说:“我在亚洲人的词句中也找到了与生活的类同。东方的天才们不是戏剧性或史诗性的,而是伦理的和沉思的,琐罗亚斯德神谕、吠陀、摩奴和孔子使人愉悦。这些无所不包的格言就像天堂里那些完美的时刻。”
通向中国古典的遥远道路就在这一过程中开启了。在很长时间内,孔子是爱默生唯一熟悉的中国先哲,后来他也读到了孟子,成为他全新的灵感源泉,他认为中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贡献也包括孟子在内。爱默生曾以诗人的妙笔,这样形容自己阅读那些东方圣经时的体会:
它崇高如炎热、如夜晚、如屏息的大海。它包含着逐个拜访了这些高尚而诗意的心灵的一切宗教情绪,所有伟大的伦理。永恒的需求、永恒的补偿、深不可测的力量,持续的沉默——这便是她的教义。
超灵和一以贯之
爱默生在哈佛神学院的著名演讲中告诫过美国人,真正的民族独立不能以建国制宪为满足,还要赢得心智和文学艺术的自主。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听从欧洲文雅有礼的缪斯女神们,实在时间太久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寻求美国在文化上的独立,让民族的精神从英国和欧洲的传统下解放出来。
显然,像爱默生这样独立意识强烈的智者,是不可能在摒弃西欧女神的同时,又转而拜倒在东方圣哲的脚下的。他在创立和宣扬先验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借鉴和吸收了东方的智慧,但并不曾在赞赏东方圣经时迷失自己。他只是吸取精华为我所用,而古老的东方哲学在超验主义诞生的过程中借以恢复了活力。爱默生的过人之处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魅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东西方各位先哲的精神在爱默生开放的思想体系中汇入同一个宇宙之灵时,爱默生向往的“精神基督教”也就宣告诞生了。这其中,代表东方智慧的孔子是不可或缺的。对爱默生来说,孔子是“民族的光荣”,“绝对的东方圣人”。他不仅需要以孔子学说作为思想素材来构建一个新的信仰,也需要通过引用孔子的学说证明自己的超验主义是普世正确的。
爱默生通过英译本研习孔子的学说,最初接触到的有约舒亚·马施曼编译的《孔子著作》和考利翻译的《中国古典:四书》,以后又有机会读到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学者王韬协助下翻译的更为详尽翔实也更为著名的《中国经典》。尽管如此,爱默生所接受的孔子,却不可能是扎根在中华民族深厚文化背景里的那位“万世师表”,因为爱默生只能从他的文化立场出发,寻找那些引起他共鸣,使他感觉认同或有启发性的思想。因此,他在借用儒家经典的词语的同时,又脱落了它们的历史语境。而在母文化中,词语及其背景是永远无法分隔的,一个人用语言无论表达什么,都无法脱离产生它们并永远伴随它们的各种语境。但另一方面,一旦词语离开母语,被移译到异域,反而有机会获得新生,即在异国文化的背景中,被重新解释并获得新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爱默生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借鉴,恰好使孔子再生出现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