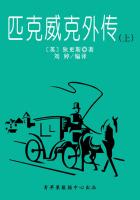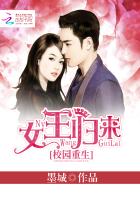第四部分“西宫”主要描写叙说者的姨妈月兰的不幸遭遇。月兰生活在香港。她丈夫30年前就离家来到了美国,之后一直靠书信来往保持联系,也时常寄钱回家供养妻子生活。在母亲英兰的安排下,月兰万里寻夫,来到太平洋彼岸。但丈夫早已与美国太太结婚生子,月兰得知事实真相后,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惨死他乡。作者刻画的是由移民和不同的婚恋观,给家庭生活造成的损害和个人心灵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女斗士》的最后一部分“胡茄颂”,写的是叙述者回忆的从幼儿园到成人的成长过程,显然有作者汤亭亭自己的体验在里头。“幼儿园的三年我沉默到了极点,我画的画全是黑色的。”但她的美国老师说得对,喜欢黑色并不表示她精神上有问题。“我在画一个舞台幕布,黑色正是帷幕升起前的景观。接下来的是灿烂的阳光和精彩的节目。”全书以蔡淡和番作为结尾,以历史上汉、番的和好,来标志中外不同文化和睦相处的前景,其中寄寓着作者希望不久的将来中美两国能和平共处,两种文化能相互沟通和交融的美好心愿。
书中的“母一女”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女儿既从母亲那里接受祖族的优秀传统,感受上一代人的辛酸和血汗,汲取积极向上的动力,同时也以另一种眼光打量着古旧的事物,体会到和自己心胸的格格不入,不由自主地采取了逆反甚或拒斥的态度。母女之间既枝叶相连,血脉相通,又有各自存活的土壤和空间,充满了张力。像姑妈的故事,母亲是作为沉痛的前车之鉴来教育女儿的,希望她能悟守中华民族古老的妇道,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循规蹈矩,不要像美国的少女那样放任自由,而且再三叮嘱女儿不要对外人讲,以免败坏了家庭的声誉。但在女儿看来,姑妈的作为可敬可佩,姑妈的遭遇可悲可悯,以死抗争正是对扼杀人性的封建伦理的最有力的抗议,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所以她偏偏告诉了别人,要让大家都知道,完全违背了母亲的初衷。
即使在以个人的努力和奉献博得大家尊敬的母亲本人身上,女儿同样以自己的目光发现了不少问题。母亲是学过医学的,按理说思想应该比较先进,然而受传统文化的深重影响,仍保留着迷信的陋习。例如药店的小伙计把别人服用的药错送上门了,母亲就认为不吉利,是咒她的家人生病遭灾,于是逼着小女儿向药店老板讨要糖果,因为要来糖果就能逢凶化吉了。小女儿觉得母亲没道理,无奈又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喝令。药店老板见华人小女孩吞吞吐吐的样子可爱,就给了糖果。母亲反而感到道理都在自己这边。两代人的隔阂虽然是通过揶揄的笔调写出来的,所揭示的东西却是发人深省的。
《女斗士》这部作品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处在双重文化影响下的“香蕉人”的境况。他们从小在家庭和社会两种不同背景中长大,时时刻刻感受到双方的拉锯和突兀。某种程度上,社会的影响(那代表着白种人和现实中的美国)要大于家庭的影响(那代表着黄种人和记忆里的中国),只要走出家门,就会强烈感觉到这一点。但一旦回到自己的家里,又始终驱赶不走在住宅的每一角落都影影绰绰地能有形无形地感觉到的祖宗先灵们。这些先灵的鬼魂们使他们既不习惯也不舒服,但又挥之不去。结果他们只有设法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特殊的文化和种族上的双重身份提供了理解和沟通两种文化的有利条件,也孕育了让东西方两种文化从冲突、撞击走向交融、汇通的良好愿望,但这愿望能否真正实现,仍有待于时间的证实。
女斗士的群像
《女斗士》书中每个故事都由女性充当主人公。Warrior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专属男性的,汤亭亭特意给它加上个定语,却并非出自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凭借着华语文化上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书中作为中心人物来刻画的女剑客、现代的“花木兰”。作者从母亲那里听到的“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个民间故事,在中国原是家喻户晓的。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疆场12载。她奋勇杀敌、战功显赫。战争结束后她不爱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脱去战袍,回到故里,换上女装,孝敬父母。她的勇敢、机智,不爱荣禄、独爱和平的高尚情操受到了世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成为世世代代传颂的佳话,也在汤亭亭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立志要像花木兰那样,长大做一名女英雄,而不是像母亲说的,女人天生就是奴役般做人妻。书中,花木兰为另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 女剑客所代替。她在战争后匡扶正义、替天行道的事迹明显超出了花木兰传说的内容,而这正是作者的意图所在。她并不想要她们之间完全吻合,而是表现新一代的女性英雄如何冲破传统的束缚。这其实也是汤亭亭成长过程的一个侧面反映。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而且统治人们的头脑时间十分漫长。在旧社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汤亭亭降生的那个年月,重男轻女的传统封建思想在中国赴美的早期移民中影响同样十分严重。“养了闺女还不如养只鸟”,“生丫头在替人家忙”,“养女儿还不如多养些牲口”,书中的女孩子,从一出生就被这些歧视性的议论和看法包围着。她时常受到与弟弟们不一样的对待:家中男孩的照片被寄回国内,向爷爷、奶奶们报喜,而她的照片却被搁置一边;大伯带弟弟们出去玩,给他们买东西,却将她留在家中;小时候也不教她学英语……这一切激发起她的反感,一听到那种歧视女孩子的话就大哭大叫,但母亲反而将她看成是只会哭、不听话的坏丫头。“我不是坏丫头,我不是坏女孩。”她竭力地申辩道,还经常与父母对着干:“我偏不烧饭。每次我洗锅刷碗,我总要给摔坏一两个。”甚至对父母常给她讲述的祖辈和老家的故事,那传递着文化根源的最重要的方式,她也公开拒绝了。她向父母亲嚷嚷说:
我再也不听你们的故事了:它们没有逻挥,把我的头脑搅乱了。你们用故事撒谎。你们讲故事时,不说“这是真故事”或“这是假故事”。我分不出真假来,我甚至不知道你们的真名实姓。我分不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你们捏造的。
其实,故事不必分真假,真实或虚构的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积淀和表述,但幼小的心灵不会懂得这么深的道理。她只希望能有力量抵御强加给她的她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与此同时,她在社会上也面临着同一类异己的压力。她曾经在美术颜料专营店打过工,老板常污蔑性地叫她“黄鬼”,她明白无误地告诉老板:“我讨厌这个词。”但她弱小的声音丝毫不起作用,老板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她的称呼。她也曾在一家土地开发协会工作,因为白人老板不采纳她的意见,她愤而拒绝为他打邀请信,结果遭开除。双重的文化身份,实质上导致的是双重的文化重负和责任,必须同时面对两种文化传统,同时面对其中的正面和负面的因素,同时在两条战线展开对其中的糟粕或腐朽部分的斗争。
这就是汤亭亭呼唤传说中的女剑客,希望有现代花木兰现身而出,摧枯拉朽地扫除一切障碍的真实动机。她既必须向中国古老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宣战,也需要同美国现实生活中的种族主义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正当的生存,她不得不两面出击。
《女斗士》中女剑客的原型花木兰,就是一位英勇、善战、有胆、有识的奇女子。她敢于女扮男装、代父参军足以说明她不凡的胆量与智慧;她像男人一样驰骋疆场,充分表明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这种向男权社会大胆挑战的精神由女剑客继承了下来,她同样女扮男装,从戎杀敌,屡建战功,最后回到家乡孝敬双亲。但女剑客与巨怪格斗,以及铲除地方恶霸的业绩,是原来传说中没有的。作者展开想象,在故事情节上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得女剑客这个形象更加丰满,也突出了她以小对大、以弱胜强的英雄气概。这无疑是寄托了汤亭亭全部理想的中心人物。
然而,在汤亭亭心目中,不仅女剑客,也不仅虽有缺点但也奋斗过的母亲和更加自觉抗争的叙述者本人,而且连姑妈和姨妈这样的不幸女性,也应该称之为“斗士”,因为她们也以她们弱小的身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出了抗议之声。实际生活中她们也许是失败的弱女子,但她们在精神上不屈不挠,称为“斗士”,也是当之无愧的。
汤亭亭提到《女斗士》“白虎”一章时说过:“这不是中国的神话,而是改造过了的美国寓言。”她所关注的,仍然不单是一段遥远的古老的光荣与梦想,而也是实际生活里中美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或更确切地说,以中国文化传统适应与改造美国文化精神的可能。这从全书最后一部分“胡茄颂”中更充分地反映出来,体现了作者的精心安排,带有全新的文化喻义。
“胡茄颂”和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中国女性蔡淡(字文姬)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是公元2世纪东汉末期声望卓著的诗人和政治家蔡琶之女,是位女诗人。朝政的不稳和社会的动乱给她婚姻带来了一连串不幸。第一次婚姻以丈夫的早亡而结束,没有后嗣。大臣董卓因叛乱而被杀之后,她的父亲也受株连而死在狱中。随后关中地区发生混战,兵荒马乱之际,蔡淡被匈奴士兵抢去,成为左贤王之妃,从此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在东汉末年的混战中雄踞一方的曹操以恢复汉室为号召,注意网罗前朝人才,扶持文化事业,将她赎了回来,但她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匈奴。回到中原后,曹操又将其赐嫁给幕僚董祀为妻。在她身不由己的接连不断的婚姻变故中,最为痛苦的是她作为一个汉族女子,生活在一个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完全不同的异域的漫长岁月,和即将回到故国却又不得不与亲生骨肉分离的戏剧性遭遇。蔡淡留下了三首诗作,咏叹了她颠沛流离、求死不能、艰难度日、备受折磨的经历。其中尤以按骚体创作的《胡笳十八拍》著名。全诗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叙述了作者流落他乡的凄切悲伤的矛盾心情:落人匈奴的囚禁一般的生活中,她日夜思念着家乡;望着南飞的大雁,她多么希望能让鸟儿带上她的思乡之情告慰家乡父老;生活在异乡,虽逐渐习惯,总摆脱不掉无名的惆怅。终于,有机会重新回到汉家天下,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国,满怀的兴奋难以言表,但与亲生骨肉生离死别,又使她肝肠寸断,心如刀绞……
但在汤亭亭笔下,蔡淡的忧愁和哀伤已经荡然无存,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能够适应异邦生活的女子。蔡淡不再是穿着兽皮衣裳就浑身发痒,而是“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也能勇猛拼杀,锐不可当”。尽管胡人的乐器声,时而是刺耳的尖叫,时而是凄凉的低鸣,搅得她没法安宁,但是她最终还是加入了这支队伍,唱出了自己的歌。“胡兵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歌唱,歌声洪亮而清晰,好像在唱给自己的孩子听。这曲调与他们的笛声非常的合拍。”“她似乎在用汉语歌唱,但胡人能理解她歌中的愤怒和忧伤。”即便是她的两个孩子开始不懂她的语言,只是机械地模仿,有时只是笑,现在“不光是笑,最后当母亲冬天走出帐篷,来到舞火旁,坐到匈奴士兵们中间歌唱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一起唱”。
汤亭亭的蔡淡完全是典型的重新建构,她像战士一样勇敢,排除了文化障碍,达到了互相的理解。这是另一种理想的境界。女斗士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而是要用自己母爱的歌声,达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最终相互的理解与和谐。在女斗士锋芒毕露、锐气逼人的宝剑周围,有祥和的瑞云在飘荡。
男人的世界
《女斗士》的成功使汤亭亭赢得了女权主义杰出作家的名望,但这多少有点误会。1980年汤亭亭的第二本书《中国佬》(ChinaMen)出版。作者自己专门作过解释:“《女斗士》和《中国佬》本来是一本书,我原来打算将两本合写成一本大部头的小说。”但后来决定“将叙述男人们的故事抽出来,写一本有关‘父亲们’的书,这样正好与前面‘母亲们’的故事相匹配。”这表明,从一开始她就无意专门关注女性或女权的主题,相反她的文学想象也亲临了男人的世界。
就像汤亭亭说的,《中国佬》是“一本有关‘父亲们’的书”。它追述了那些不远万里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寻求发展的父亲一代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经历。和《女斗士》一样,作者将历史事实、传奇故事、神话和个人的遭遇糅合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了这些被污蔑性地称为“中国佬”的男子汉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生活勇气。作者的父亲、亲属及其他父辈们,或者出于自愿,或者由于被迫,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等待他们的,却是美国移民法的刁难的排斥,社会上有形无形的种族歧视,和监工、老板的虐待与剥削。书中,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中国早期移民是美国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他们在洗衣房、建筑铁路、开凿矿山、种植甘蔗、开垦农场、部队服役等诸多领域为美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作者无疑是在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向美国声明,这些早期的华人移民有权被认为是美国的合法公民。
相比之下,《中国佬》的历史文献质更强一点。书中有较多的早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的民俗和社会风貌的细节描写,也包括按日期先后出台的歧视中国移民的一系列法规,和第一批中国移民反对种族歧视而获得胜利的纪录。对这本书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一方面继续好评如潮,如在问世的第二年就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来还获得普利策二等奖,1988年又获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得奖提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9月29日授予她全国人文学科奖章讲话时,还特别赞扬了此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从未见到过的世界,但我们又会立即感到它的真实存在”,从而将“美籍亚裔的经历,生动地展现在百万读者的面前,也鼓舞了新一代作家将他们独特的心声和经历告诉亿万读者”。当然,也有的批评家抱怨,作者重新构建的中国的传说和神话离开本来的面貌太远了,对此汤亭亭的回答是,她并不打算再现中国的文化,而只是想描述自己的体验,描述父辈们对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