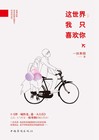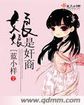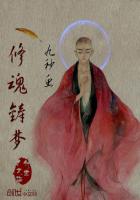新诗或白话诗,和白话文,都脱离了那多多少少带着人工的、音乐的声调,而用着接近说话的声调。喜欢古诗、律诗和骈文、古文的失望了,他们尤其反对这不能吟诵的白话新诗;因为诗出于歌,一直不曾跟音乐完全分家,他们是不愿扬弃这个传统的。然而诗终于转到意义中心的阶段了。古代的音乐是一种说话,所谓“乐语”,后来的音乐独立发展,变成“好听”为主了。现在的诗既负上自觉的使命,它得说出人人心中所欲言而不能言的,自然就不注重音乐而注重意义了。——一方面音乐大概也在渐渐注重意义,回到说话吧?——字面儿的影象还是用得着,不过一般的看起来,影象本身,不论是鲜明的,朦胧的,可以独立的诉诸感觉的,是不够吸引人了;影象如果必需得用,就要配合全诗的各部分完成那中心的意义,说出那要说的话。在这动乱时代,人们着急要说话,因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小说也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它的使命比诗更见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写,只靠对话,说出所要说的。这里面神仙、武侠、才子、佳人,都不大出现了,偶然出现,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的,这时候的小说的人物,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这是平民世纪啊。至于文,长篇议论文发展了工具性,让人们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说出他们的话,但是这已经成为诉诸理性的了。诉诸情感的是那发展在后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标榜“生活的艺术”,抒写“身边琐事”的。这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图着教人“百读不厌”的,确乎也风行过一时。然而时代太紧张了,不容许人们那么悠闲;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谓“软性”,丢下了它去找那“硬性”的东西。
文艺作品的读者变了质了,作品本身也变了质了,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压下了快感。这也许就是所谓“硬”的解释。“硬性”的作品得一本正经的读,自然就不容易让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于是“百读不厌”就不成其为评价的标准了,至少不成其为主要的标准了。但是文艺是欣赏的对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感的,怎么“硬”也不能“硬”到和论文或公式一样。诗虽然不必再讲那带几分机械性的声调,却不能不讲节奏,说话不也有轻重高低快慢吗?节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够高度集中。文也有文的节奏,配合着意义使意义集中。小说是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但也总得有些契机来表现生活和批评它;这些契机得费心思去选择和配合,才能够将那要说的话,要传达的意义,完整的说出来,传达出来。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义,才见出情感,才让人乐意接受,“欣赏”就是“乐意接受”的意思。能够这样让人欣赏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读不厌”,可以不论。在这种情形之下,笔者同意:《李有才板话》即使没有人想重读一遍,也不减少它的价值,它的好。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笔者都读过不止一回,想来读过不止一回的人该不少吧。在笔者本人,大概是《阿Q正传》里的幽默和三部曲里的几个女性吸引住了我。这几个作品的好已经定论,它们的意义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这里说的只是它们让笔者“百读不厌”的因素。《阿Q正传》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部曲的主要作用也不在铸造几个女性,但是这些却可能产生让人“百读不厌”的趣味。这种趣味虽然不是必要的,却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过这里的幽默决不是油滑的,无聊的,也决不是为幽默而幽默,而女性也决不就是色情,这个界限是得弄清楚的。抗战期中,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读众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读者,他们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感。扩大了的读众,有着这样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就是这个要求的反应,因为篇幅长,故事就长,情节就多,趣味也就丰富了。这可以促进长篇小说的发展,倒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作者却因为这样的要求,忘记了自己的边界,放纵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吸引读众,这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读这一类低级的软性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说不上“百读不厌”。“百读不厌”究竟是个赞词或评语,虽然以趣味为主,总要是纯正的趣味才说得上的。
写作杂谈
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若是我也可说是有作风的话。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在大学里学的原是哲学。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虽然幼年就爱好文学,也倾慕过《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但总不能深入文学里。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知道对于小说没希望,尝试的很少。那时却爱写诗。不过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一点儿也不能超群绝伦。我只是一个老实人,或一个乡下人,如有些人所说的。——外国文学的修养差,该也是一个原故。可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的情感和想象虽然贫弱,却总尽力教文字将它们尽量表达,不留遗憾。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已故的刘大白先生曾对人说我的小诗太费力,实在是确切的评语。但这正是一个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
后来丢开诗,只写些散文;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所以写得也多些。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原是对“正论”而言;一般人又称为小品文,好似对大品文而言,但没有大品文这名称。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又不需要小说的谨严的结构,写起来似乎自由些。但在我还是费力。有时费力太过,反使人不容易懂。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有一处说到“无可无不可”,有“无论是升的沉的”一句话。升的“无可无不可”指《论语》里孔子的话,所谓“时中”的态度。沉的指一般人口头禅的“无可无不可”,只是“随便”“马虎”的意思。有许多人不懂这“升的沉的”。也许那句话太简了,因而就太晦了。可是太简同然容易晦,繁了却也腻人。我有一篇《扬州的夏日》(在《你我》里),篇末说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有些穿上长衫,有些只将长衫搭在胳膊上。一个朋友说穿上长衫是常情,用不着特别叙出。他的话有道理。但这并不由于我的疏忽;这是我才力短,不会选择。我的写作有时不免牵于事实,不能自由运用事实,这是一例。
我的《背影》、《儿女》、《给亡妇》三篇,注意的人也许多些。《背影》和《给亡妇》都不曾怎样费力写出。《背影》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话。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亡妇一生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她。写《给亡妇》那篇是在一个晚上,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虽然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当时只靠平日训练过的一支笔发挥下去,几乎用不上力量来。但是《儿女》,还有早年的《笑的历史》,却是费了力琢磨成的。就是《给亡妇》,一方面也是一个有意的尝试。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给亡妇》用了对称的口气,一半便是为此。有一位爱好所谓欧化语调的朋友看出了这一层,预言我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我也渐渐觉得口语不够用。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愿意称为现代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所以我义回到老调子。所谓老渊子是受《点滴》等书和鲁迅先生的影响。当时写作的青年很少不受这种影响的。后来徐志摩先生,再后来梁宗岱先生、刘西渭先生等,直接受取外国文学的影响,算是异军突起,可是人很少。话说回来,上文说到的三篇文里,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背影》里若是不会闹什么错儿,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原故。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
国文教师做久了,生活越来越蒲松龄夜撰聊斋。(当代王仲清怍)狭窄,所谓“身边琐事”的散文,我慢慢儿写不出了。恰好谢谢清华大学,让我休假上欧洲去了一年。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和一些《伦敦杂记》。那时真是“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已经腻了,而且有人攻击。我也觉得身边琐事确是没有多大意思,写作这些杂记时便专从客观方面着笔,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但是客观的描叙得有充分的、详确的知识作根据,才能有新的贡献。自己走马看花所见到的欧洲,加上游览指南里的一点儿记载,实在太贫乏了,所以写出来只是寒尘。不过客观的写作却渐渐成了我的唯一的出路。这时候散文进步了。何其芳先生的创作,卞之琳先生的翻译,写那些精细的情感,开辟了新境界。我常和朋友说笑,我的散文早过了时了。既没有创新的力量,我只得老老实实向客观的描叙的路走去。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这大概是经验和知识还不够的原故。但是自己总不甘心,还想尝试一下。于是动手写《语文影》。第一篇登在《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平明》上,闹了点错儿,挨了一场骂。可是我还是写下去。更想写一些论世情的短文,叫做《世情书》。试了一篇,觉得力量还差得多,简直不能自网其说似的,只得暂且搁下。我是想写些“正论”或“大品文”,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正”不住我的笔,也得再修养几年。十六年前曾写过一篇《正义》(见《我们的七月》),虽然幼稚,倒还像“正义”,可惜没有继续训练下去。现在大约只能先试些《语文影》。这和《世情书》都以客观的分析为主,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
我的写作的经验有两点也许可以奉献给青年的写作者。一是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入手。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本领。据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讲究文字,却也成为大小说家。但是他若讲究文字,岂不更美?再说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大才力,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为一般写作者打算,还是不放松文字的好。现在写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无论他们的理由怎样好听,吃亏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不是别人。二是不一定创作,五四以来,写作的青年似乎都将创作当做唯一的出路。不管才力如何,他们都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戏剧:这中间必有多数人白费了气力,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这也是时代如此,当时白话文只用来写论文,写文学作品,应用的范围比较窄。论文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经验,青年人办不了,自然便拥挤到创作的路上。这几年白话文应用的范围慢慢儿广起来了,报纸上可以见出。“写作”这个词代替了“创作”流行着,正显示这个趋势。写作的青年能够创作固然很好,不能创作,便该赶紧另找出路。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出路,便是新闻的写作。新闻事业前途未可限量,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现在已经有青年记者协会,足见写作的青年已找出这条路。从社会福利上看,新闻的写作价值决不在文艺的写作之下,只要是认真写作的话。
短长书
书业的朋友谈起好销的书,总说翻译的长篇小说第一,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二;短篇小说和散文,似乎顾主很少,加上戏剧也重多幕剧,诗也提倡长诗(虽然诗的销路并不佳),都可见近年读书的风气。这些都只是文学书。这两三年出版的书,文学书占第一位,已有人讨论(见《大公报》);文学书里,读者偏爱长篇小说,翻译的和创作的,这一层好像还少有人讨论。本文想略述鄙见。
有人说这是因为钱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书少。钱多,购买力强,买得起大部头的书;而买这些书的并不一定去读,他们也许只为了装饰,就像从前人买《二十四史》陈列在书架上一样。书少,短篇一读即尽,不过瘾,不如长篇可以消磨时日。这两种解释都有几分真理,但显然不充分,何以都只愿花在长篇小说上?再说买这类书的多半是青年,也有些中年。他们还在就学或服务,一般的没有定居;在那一间半间的屋子里还能发生装饰或炫耀的兴趣的,大概不太多。他们买这类书,大概是为了读。至于书少,诚然。但也不一定因此就专爱读起长篇小说来,况且短篇集也可以很长,也可以消磨时日,为什么却少人过问呢?
主要的原因怕是喜欢故事。故事没有理论的艰深,也不会惹起麻烦,却有趣味,长篇故事里悲欢离合,层折错综,更容易引起浓厚的趣味,这种对于趣味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消遣心理。至于翻译的长篇故事更受欢迎,恐怕多少是电影的影响。电影普遍对于男女青年的影响有多大,一般人都觉得出;现在青年的步法、歌声,以至于趣味和思想,或多或少都在电影化。抗战以来看电影的更是满坑满谷,这就普遍化了故事的趣味(话剧的发达,也和电影有关,这里不能详论)。我们这个民族本不注重说故事。第一次从印度学习,就是从翻译的佛典学习(闻一多先尘说):现在是从西洋学习。学生暂时自然还赶不上老师,所以一般读者喜爱翻译的长篇小说,更甚于创作者。当然,现在的泽笔注重流畅而不注重风格,使读者不致劳苦,而现在的一般读者从电影的对话里也渐渐习惯了西洋人怎样造句和措辞,才能达到这地步。
现在中国文学里,小说最为发达,进步最快,原已暗示读者对于故事的爱好。但这个倾向直到近年来读者群的扩大才显明可见。读者群的扩大,指的是学生之外加上了青年和中年的公务人员和商人。这些人从小学或中学时代的读物里接触了现代中国文学,所以会有这种爱好。读者群的扩大不免暂时降低文学的标准,减少严肃性而增加消遣作用。现代中国文学开始的时候,强调严肃性,指斥消遣态度,这是对的。当时注重短篇小说,后来注重小品散文,多少也是为了训练读者吟味那严肃的意义,欣赏那经济的技巧。这些是文学的基本条件。但将欣赏和消遣分作两橛,使文学的读者老得正襟危坐着,也未免苦点儿。长篇小说的流行,却让一般读者只去欣赏故事或情节,忽略意义和技巧,而得到娱乐;娱乐就是消遣作用,但这不足忧,普及与提高本相因依。普及之后尽可渐渐提高,趣味跟知识都是可以进步的。况且现在中国文学原只占据了偏小的一角,普及起来才能与公众生活密切联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取旧的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