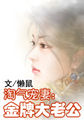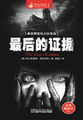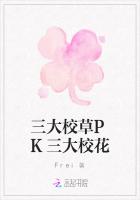(父亲这种愚昧的举动是想留住汪家最后一脉。但他终于没有留住,大约四五天后的傍晚,小床的摇晃声戛然而止,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汪家就此画上了惨痛的句号。)
眼看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也慢慢洇湿着中华大地,洇到举人湾时,堪堪快到过年时节。与林副主席朦朦胧胧粉身碎骨不一样的是,四人帮的粉碎如此清晰和令人振奋。前者像摔碎了瓦罐一样瓮声瓮气,后者则像摔碎瓷器般清澈明亮。
欢快之余,人们决定把生产队上养的猪全部杀掉,以庆贺北京除掉了奸臣。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场庆贺的牺牲品除了生产队上几头未成年的猪外,还包括快成年的黑豆。
我记得那显然是个清亮的天气,阳光早早就驱散了薄薄的雾气,春天的脚步清晰可闻,油菜花已经在散发着诱人的体香,麦苗显示出它们战胜寒冬后的英姿。腊月二十五这天,生产队长在公猪圈发出的分肉号召迅速被村民愉快地传递着。公猪圈养的并不是公猪,事实上,公猪圈是公共猪圈的意思,是一个生产队集中养猪的地方,公猪圈尽管修得十分庞大,光石砌的猪圈就有两大排,还不包括饲料房和人住的房子。可惜的是,这个猪圈像那个时代的任何东西一样大而无当,一直没养多少猪,偶有几只也跟人一样苟延残喘--那些岁月里,人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情喂猪。
自汪武夫妻死后,黑豆虽然还住在破房子里,但已经有意无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数百年汪家的血脉最终系于黑豆一身,我父亲怎么也不忍心这一脉断了。在我的印象中,黑豆永远黑着个脸,没有一丝笑容,而且还长着巨大的门牙。我曾经目睹过他啃竹子的雄风,他的门牙居然能将坚硬的竹子咬破撕成片儿。他永远不参与我和我哥的打斗,也永远不会劝架或帮忙,因为我们打斗时几乎见不着他。那个时候,他或许在哪个田边抠泥鳅黄鳝以充实永远饥饿的肚子,或许在农业社的某片田土里领着点可怜的工分,或许像浪子一样在天龙庙里转悠……反正我们只在重要的时候才能见到他和我们一桌子吃饭--比如过年。
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举人湾的人口下降得厉害,所以到了分猪肉需要细数人数时,生产队长和几个老人半天没回过神来,原本人丁阜盛的举人湾,如今只剩下一百四十口。人们一边摇头,一边扳头指头算,汪文是在五八年洪水死了的,那年走掉了一批;闵少卿是在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时死掉的,那年又走掉一批;曾经有五大房人二百多口人的闵家,如今只剩下不足五十口人……说不来呀说不来呀,人们一边缅怀死者一边计算各家各户的肉量。另外一张桌子上,大队书记和几个生产队长坐在一块打六红牌,他们被邀请来,心安理得地等待喝酒吃肉。
那个上午,我和一群小孩子自始至终踟蹰在猪圈四周,我们一直瞅着那个巨大的猪笼,关心那些放在大锅里煮的猪骨头什么时候扔进来。从第一根扇子骨碰到猪笼发出的声响开始,我们的目光就没离开过这个猪笼,我们沿着猪笼围成一个椭圆形,尽一切可能寻找可以吞下肚子的肉渣儿。大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慷慨,他们拼命地将骨头上的肉剔干净,先是用手撕,然后用刀铲,最后再用嘴过一遍,然后才将骨头扔进这个竹笼子里。此情此景,我们的遭遇就可见一斑了,幸存不多的肉末显然激发了我们的创造欲望。我们首先用嘴啃一遍,一个人啃了还会有其他人复检一遍,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挑战骨头与骨头间的肉和筋,我们用针、竹签、生锈的钉子拨弄着那一丁点儿肉末。多年以后我才想起,童年苦苦追寻的这点儿肉末其实并不比我成年以后从牙缝里挑出去的肉末多到哪里去。但在当时,肉就是肉,与量多量少无关,肉的感觉永远美妙无比。而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美妙的感觉。当骨头表面被我们的舌头掠过不知多少遍后,我们开始敲骨吸髓。可我们没有想到,由于火候不到,骨头里流出的却是一片鲜红……
这个时候,黑豆提着笨重的大木桶出现了,按照我父亲早晨的吩咐,黑豆来领他和我们家的肉。我们家的成员包括:奶奶,爸爸,妈妈,我,二岁的弟弟。我和弟弟合起来算半个大人的量,加上黑豆,差不多五个成年人的量,每个人两斤多肉,总共有十多斤肉。黑豆分到这些肉后,独自一人提着,慢慢往祠堂方向回了。与此同时,各家各户都分到了肉,不大一会儿,欢天喜地的炊烟就起来了,久违了的肉香在举人湾春天的空气中缓缓飘荡。
我本来想跟黑豆一起回去,但想起那些全是生肉,离煮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再加上我们平日里缺少交流,所以我选择在公猪圈继续寻找骨头上的肉末。快吃午饭时,父亲却寻到公猪圈,问我见黑豆没有。我们都说他早就提着肉回去了呀,父亲吃了一惊,说根本没见人和肉啊。正准备和杀猪匠吃饭的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等人吓了一大跳,饭也不敢吃了,急忙跟着父亲沿着回祠堂的路去找,我跟在大人屁股后边,边走边用棍子打划着田里清亮的水,试图发现藏在泥中的小鱼。从公猪圈回祠堂大约有三里地,其间大多是水田和冬麦,一览无余,哪有黑豆的影子。直到拐过一个弯,远远一丛湘妃竹林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扑了过去。
黑豆确实在这里。
等我看见黑豆时,他已躺在父亲的臂弯里,身上不断抽搐。我能清楚地看到他抽搐的动力来自肚子,这里的抽搐通过肌肉传遍全身,像一个永动机般停不下来,抱着他的父亲也跟着抽搐,最后不得不把他重新放回草地上。人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赤脚医生出身的大队书记见多识广,这个兽医兼作人医的家伙蹲在那个装肉的桶边看了一会儿,说黑豆是生肉吃得太多太急,把胃糟蹋了,现在啥办法都没有,只能抬回去慢慢看。然后他恨恨地说,一辈子没吃过肉!十来斤肉生吃了一半,神仙都救不活。
黑豆果然没救活。闵家祖传的草药方灌进肚子里,没用。他照样抽,花花绿绿的药水从哪里进去又从哪里出来;大队书记从县上要来一些针药,也没用,照样抽。父亲用竹子绑了个临时的小床,放在堂屋里,日夜看着他。那几天,黑豆这张竹子小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摇晃声远近闻名。人们一个接一个来看,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地摇着头走开。小床旁边,一直坐着我形容枯槁的父亲,他一直不停地在请观音菩萨保佑。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这种愚昧的举动是想留住汪家最后一脉。但他终于没有留住,大约四五天后的傍晚,小床的摇晃声戛然而止,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汪家就此画上了惨痛的句号。
十多年后,我再次见到这种奇异的死法。不过这次死的不是人而是我们家那条黄狗,身体健硕的它陪我度过了好长一段快乐的少年时光。无数个清晨,这只狗风雨无阻地陪我翻过一个又一个高高的垭口。无数个傍晚,放学归来的我紧紧搂住它的脖子,亲吻着它湿漉漉又富有灵感的鼻子。只是一块肉改变了一切。那天,父母赶集归来,手里提着两斤左右的肉。母亲让我把肉挂在厨房的墙上。为了防备大黄狗偷吃,我特地将肉挂在水缸后面的墙上,然后就跑到另外的屋子里分桃子吃。一会儿,母亲进厨房做饭,翻江倒海地没找着肉,连那根拴肉的麻绳也不见了。一会儿却见黄狗居然打着饱嗝,踱着方步从外边回来。我正要呵斥它点什么,一根粗大的棒子就呼的一声从我身边飞过,没有砸着但吓得它拔腿就跑。几天后,黄狗才回来,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般躲着不敢见我们,身子很不灵便,不断地抽搐打嗝,没多久就死了。
此后,我曾经无数次拨弄着碗里各式各样的肉食,它们被各种级别的大厨和香料伺候过,但我始终想不通黑豆在对待肉食这个问题上,何以跟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后来,我自信慢慢琢磨出了真相:黑豆和黄狗的抽搐应当是受到极度恐吓之后引发的生理反应,这种反应和胃里边的生肉相辅相依,终于导致不治。黄狗的极度恐惧来自那根粗大的棒子,黑豆的极度恐惧又来自哪里?肯定是边吃生肉边产生的恐惧,因为他知道他吃了本不属于他的肉,他也知道那一天,我们家所有人都渴望吃到肉。所以黑豆生肉吃得越多,恐惧就积累得越多,以致吃到后来,他已无法想像和承担被人发现后的结果,但他又实在无法拒绝面前这桶肉的致命诱惑……每每想到此处,我都不愿意继续下去。在这个被今人当作传奇的事件里,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浓厚的悲凉,它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我只敢触摸它的边际,从来不敢走近。我知道,以我脆弱的生命,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这种悲凉,无论如何。
祠堂的竹林里有一种只会直道而行的怪虫子,无论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它们都会勇往直前永不逃避。我亲眼见它们罔顾面前的火堆,一个接一个爬了进去,葬身火海。我也亲眼见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进水坑,在无谓的挣扎中沉入水底……
人到中年后我才明白,我的父辈们就是这样的虫子。从那个痛苦年代过来的男人们,脚下其实没有多余的路可供选择,他们只能直道而行,纵然面前是刀山火海。面对困厄的家境和铁板一块的社会,除了付出自己的热血和挣扎外,别无选择。于是,英年早逝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举人湾,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七叔八爷们,很多都没有逃脱英年早逝的厄运。他们大多死在年富力强的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死因包括肝癌、肝炎、肺癌、糖尿病等等。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要奋发向上,除了我以我血之外,似乎别无他途。他们没有办法偷懒,没有办法巧取,只能背负重担,缓慢前行,直到灯枯油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