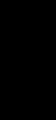刘立信毕竟是特工出身,短暂的慌乱后,很快冷静下来。这个女人肯定不是魏二寡妇,她究竟是谁?难道是党国潜伏下来的同志?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对付国民党潜伏人员上很有一套,先是土改,接着清匪反霸,然后开展“三反五反”,最近又搞了“反右”,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潜伏下来的同志死的死,逃的逃,活着的现在绝大部分在劳改队或者监狱,就像他这种,算是潜伏得比较好的,共党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曾经也想过,等满刑后找找组织,看看还有没有幸存的人,然后开展工作,继续为党国服务。可是满刑后他被强制留场就业,还是被监视、控制起来。
“你是?”他站起来,态度恭敬起来,迟疑地问。
“我给你说了,我是魏来男,魏二寡妇,魏铁匠的女儿,怎么,在劳改队呆久了,脑子不好使了是不是?”魏来男面无表情地说。
“是是是,你是魏来男,魏二寡妇,魏铁匠的女儿……”刘立信立正,重复她的话,然后眼珠一转,小心翼翼地试探说,“二姐,参加战斗的不光是他宋明远一个人,就算是他杀了‘三黑’兄弟,我们也不至于为了一个土匪引火上身吧?”
魏来男脸色一沉:“叫你杀你就杀,哪里那么多废话?你要是敢糊弄我,只要我写一封信寄给公安局,我看你还能活不?哼,你自己掂量掂量。”
到了这个眼骨节儿上,刘立信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眼珠一转,语气坚决地说:“如果是命令,我执行;如果是要挟,你现在就去举报我。”
说完,他紧紧盯着魏二寡妇的脸,试图从她脸上找出破绽,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行,至少,可以大体判断她究竟是什么来头。然而他失望了。
魏来男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只是连连冷笑,说:“你可以理解成命令,也可以理解成要挟,反正,老娘就是要他宋明远的人头。我给你一个月时间,现在,你可以滚了。”
刘立信楞了楞,转身就走。
“回来!”
刘立信心里一咯噔,不知道这女人还有什么花花肠子,转身问:“二姐有何吩咐?”
“你去给杂毛找点肉来。”
刘立信恼怒地说:“这年头,老子两个月都开不了一次荤。”
“人肉。”
“什么,你……你说什么?”刘立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人肉!”魏来男提高了声音。
刘立信慌忙摇手:“姑奶奶,你别这么大声好不好?这……”
“怎么?怕了?你在息烽时候,把一个共党活剥了,把人家的心肝炒了下酒,你那时候的胆量呢?”魏来男嘲笑说。
刘立信喜欢看她笑,即便是冷笑,马上就神魂颠倒了,可现在听她的笑声,心里却毛骨悚然。尽管寒气凛冽,但他额头上还是冒出汗珠来。
魏来男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嫣然一笑,挽起他的胳膊,嘴唇在他耳边娇滴滴地说:“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干,我那土匪当家的,临死前告诉我他一生积蓄的埋藏地点。那些东西,足够你偷渡到香港,到台湾与你老婆孩子团聚。”
说完,在他耳朵上轻轻吹了一口气。
刘立信立即浑身痒痒的,但是职业的敏感提醒他,眼前这个人很危险,便说:“你有钱,还怕没肉?”
魏来男推开他,从衣柜里抱出一个箱子,把手伸进去摸索了半天,拿出一块金条,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说:“好,你现在去给老娘买一斤,不,半斤肉,我只要你买半斤肉来,余下的算是你的跑路费!”
刘立信连忙拿起金条,掂量掂量,用牙齿咬了一下,双手恭恭敬敬地把金条放在桌子上。
“去呀?怎么不去了?”魏来男知道他已经相信了自己,但还是想继续激将他一下。
刘立信陪笑道:“这东西……好东西啊,可惜在两溪口用不了。二姐呀,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出来,要请假,要两人以上同行,规定了回队的时间。你明天就要,这哪能呢?”
魏来男笑道:“看来,共产党真把你的折磨惨了,脑子残废了。你们劳改队不是天天在死人么?”
刘立信无奈地说:“好吧,我试试。”
刘立信说完,走到后院,翻墙而去。
天色就像新媳妇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有一点惨淡的阳光,可转眼之间,太阳就躲进了云层。远处的天际,有一团黑云翻滚着,像柳溪和罗家溪在两溪口交汇时候涌起的波浪,看似没有一个定数,但又似乎总有一些规则,让人捉摸不透。风一个劲儿地刮,呜呜嘤嘤的,时而像嚎叫,时而又像是在啜泣。
宋明远与汪文丽分开后,他左思右想,实在是没有信心回就业大队,寻思等见着姚志海,请他帮忙去拿行李,于是朝四大队而去。刚刚到四大队的地界,远远看见三个人匆匆而来。等三人走近,他大吃一惊,那不是五爷和苏老爹吗?只是后面那个后生,他不认识。
“小五哥,苏老爹!”他兴奋地大叫。
三人陡然间听见他咋呼呼地喊,都吓了一跳,等认出他来时,五爷和苏老爹都不约而同地跑过来,与宋明远拥抱在一起。
宋明远问:“我托人送回去的药收到了吗?二娘的病好点了没有?”
“幸亏你送回来的药和钱,好多了,好多了……”五爷说。
“钱?我没送钱回去呀?”宋明远很诧异。
五爷也很诧异:“那就怪了,二十块啊。”
“啊?!”宋明远立即明白了,八成是杨雨荷给的,她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五爷说:“你真没有捎钱回来?那就是你的朋友了。明远,你可得好好感谢人家,多亏了那二十块钱……”
“你们怎么来了?”宋明远问。
五爷和苏老爹对视一眼,低头不语。
“有事儿吗?”宋明远追问。
五爷岔开话题说:“看到你没事,我们也安心了,天色不早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走了哈,走了啊。”
宋明远一把拉住他:“小五哥,出什么事儿了?”
“这……”五爷吞吞吐吐。
“说呀!”宋明远嚷道。
五爷见他急了,这才说:“你捎回来的钱呀,你二娘看到乡亲们过得苦啊,便捐献出来,托我和二叔去置办了一些粮食。乡亲们以为你们这里好过,这不,就托我们来找你们……哪知道,你们日子也不好过……”
“你们?还有谁?”宋明远有些纳闷。
“你们不认识?”五爷惊讶地问。
宋明远一下明白了:“你是说苏老爹的儿子吧?他是干部,我当时还是犯人,无缘相见。”
“他就是苏涛。”苏老爹把苏涛推到他面前,“苏涛,叫叔。”
苏涛突然暴怒起来,冲着他爹吼:“你干什么?我是干部,他是犯人!”
苏老爹气得浑身发抖,举手就打,骂道:“你这个不孝子,连你老子都不认了?”
五爷连忙拉住苏老爹,劝道:“算了算了,你消消气,消消气……”
苏老爹指着儿子继续教训:“我……我这气儿能消吗?开口干部,闭口干部,你当干部了,就不认你爹了?不认乡亲了?你给我记住,要不是他宋家,你还是个地主狗崽子……”
苏老爹越说越激动,脸胀得通红,一阵咳嗽。
宋明远走过去,扶住他,拍拍他的后背,说:“这天色要变了,我带你们去住店,明天再走吧。”
“我晚上还要值班呢……”苏涛咕嘟说。
苏老爹挣脱开宋明远的手,不声不响地走了。
五爷看看苏涛,轻声叹了一口气,跟了上去。
宋明远打量了一下苏涛,牵着马追上去,说:“小五哥,苏老爹,我送送你们。”
苏老爹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边走边说:“明远呀,我对不起你爹,我心里有愧呀……”
宋明远笑道:“你别唠叨了,我耳朵都听起茧疤来了。”
“要是我那逆子,有你一半醒世,我就知足了……”苏老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
宋明远安慰说:“他还小,等过几年成熟了,就对路了。你说是不,五哥?”
三人说着说着,又回到吃的问题上,五爷和苏老爹担心那些老人活不过这个冬天。宋明远心里沉甸甸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天天都是喜报,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怎么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呢?从红军开始就讲勒紧裤腰带干革命,一直讲到解放。解放后又说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建设,这话他不爱听了,在没有解放时,还说得过去,可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推翻了蒋介石为首的独裁政府,怎么还要勒紧裤腰带?国家建设就不能缓一点,先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人要是没有饭吃,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还能干革命么?真正的革命者,因为有信仰,可以饿着,可老百姓呢?在他们眼里,任何一个美妙绝伦的主义,都不如一碗饭实在……
他脑子很乱,越想越糊涂,想理清,可越理不清。
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就业大队外面,看见汪文丽在那里,就像遇到救星一般,大叫着跑了过去。
汪文丽奇怪地看着他。
“你身上……有……有钱么?借我……”也许是身体原因,宋明远上气不接下气。
汪文丽问:“你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汪文丽一愣,马上翻口袋,找出了十一块三角二分,递给他:“够不?不够我回家拿。”
“够了,够了。”宋明远接过钱塞给五爷。
这十一块三能买将近100斤大米啊。
五爷死活不要,说:“不行不行,你现在自身都难保,我们回去自己想办法,毕竟是乡下,偷偷开点荒地,也就对付过去了……”
“五爷!”宋明远说,“这天寒地冻的,开荒也要等到明年春天吧?”
宋明远这次没有叫“小五哥”,而是叫他五爷。
五爷一怔,连连道谢,接过钱,把钱卷成卷儿,装进一个小口袋,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又在棉衣外头摸索了又摸索。
汪文丽问:“明远,他们是?”
“这是我小五哥……不不,论辈分,他是我五爷。对了,这是苏老爹,他儿子叫苏涛,在四大队当干部……”宋明远介绍说。
苏老爹打断了他的话:“那逆子,不提也罢。”
“这是汪文丽,干部,直属二队队长。”
五爷和苏老爹客气地朝她点点头。
“五爷,是不是家里遇到难事了?”汪文丽问。
“一点点,一点点,给明远……给你添麻烦了,早知道我们就不来了……”五爷满脸歉意。
汪文丽说:“这说哪里话呢?我跟宋明远是同事嘛。不过,光有钱没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呀。你们等着,我去拿些粮票来。”
不待他们说话,她抢过宋明远手中的缰绳,翻身上马而去。
“这姑娘不错……”五爷望着她的背影,像是说给宋明远听,又像是自言自语。
苏老爹连连喟叹:“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三斗米而忘记廉耻仁德者,比比皆是,现在像她这样的人不多了,不多了……”良久又说,“我要是有这样的媳妇,前世积德呀……”
五爷不满地看了他一眼:“你儿子与她年龄差距太大了吧?”
“不然,不然,俗语有云:女大三,抱金砖。”苏老爹摇头摆手,好像汪文丽一定就是他的儿媳一般。
五爷生气了,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你这曰夫子,怎么老跟明远他家作对?”
苏老爹楞楞地看着他,旋即醒悟过来,看着宋明远笑道:“老朽有感而发,切勿见怪,切勿见怪。”
宋明远觉得好笑,把目光挪向别处,假装没有听见。
哪知苏老爹以为他介意了,冲着他连连作揖道歉:“老朽我口不择言,我那犬儿怎能配得上……”
“苏老爹,你刚才说啥呢?”宋明远故意问。
苏老爹问:“你刚才没听我们说话?”
“没有,我在想啊,还是找个机会把二娘接过来,在农场医院好生检查一下。可是现在我……唉,想当初我就不该那么冲动,我咋就那么冲动呢?”宋明远懊恼地说。
他们早就想问宋明远究竟是怎么搞的,提着脑袋终于熬到革命胜利了,却犯了罪,进了劳改队,但就是开不了口,现在他自个儿说起这事儿,五爷和苏老爹都全神贯注,可宋明远打住不说了。
三人沉默了一阵,五爷还是忍不住问:“丑牛(宋明远的小名),你……你咋就进了劳改队呢?”
宋明远黯然地说:“这事儿说来话长,等有机会慢慢给你讲……”
汪文丽骑马而来,跃下马,把粮票递给五爷:“五爷,我就找了80几斤粮票,这里还有10多块钱,你先拿着,等以后有多余的,我拿给宋明远。”
五爷激动得双手直哆嗦,连声道谢:“钱,我不能再要了,不能要了……”
汪文丽把粮票和钱塞到他手里,说:“我知道乡下苦,你就拿着吧。”
“姑娘,你可是我们高坡子的救命恩人……”五爷老泪枞横,连连抹泪说,“我没啥感谢你的,也不知道这钱粮能不能还上,我就代表乡亲们给你磕个头吧……”
他朝汪文丽跪下。
汪文丽大吃一惊,一把拉住他:“使不得,使不得,你老这不是折杀我这个晚辈么?”
苏老爹也劝道:“五爷,大恩不言谢,我们高坡子记着了。走吧,天色不早了,别耽误了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