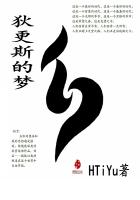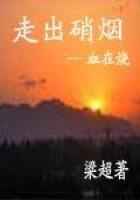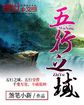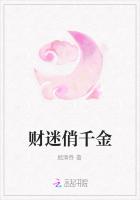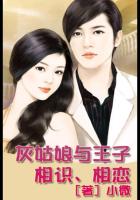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讲,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都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小说。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康弗认为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饶有趣味的小说,是梦的拼贴画,是美妙绝伦的艺术品”,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他关于“梦”的论断也完全切中肯綮。事实上,米洛拉德。帕维奇确实在《哈扎尔辞典》中构筑了一座“梦”的宏伟大厦,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
但是无论何种大厦,都必然基于其砖瓦柱石之上,就本文来说,米洛拉德。帕维奇妙若天成的语言正是这不可或缺种砖瓦。作为一本辞典小说,也许语言本身才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许多敏感的读者大概早已注意到这本小说语言的独特之处,这也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东西。
最独特的一点,我认为,是米洛拉德。帕维奇大胆而巧妙地赋予被叙物各种各样的性格与气质。有时,这种性格与气质和人物的心情或行为紧密联系,并随之变化而改变;有时,又毫不相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不过殊途同归,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使作者的叙述变得生动多元、奇丽奇幻。同时,自然也使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体验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奇妙感受。
或者说,在米洛拉德。帕维奇看来,语言也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有了生命,成了具有思想情感的独立个体,亦即作者在卷首语第八页用黑体字写的那样:“词句已成血肉”。
可想而知,以这种具有生命的语言来写人记事,其能够达到的语言效果自然非同小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不难理解《哈扎尔辞典》中那些极富颠覆性的狂欢式语句。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中以详实的例子予以佐证。
在《哈扎尔辞典》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影子”这个独特的形象,比如人的影子、屋宇的影子、山脉的阴影或者父亲的侧影、母亲肚脐的阴影。在米洛拉德。帕维奇笔下,影子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光学概念,而显然有其潜在的特殊含义。它们在语言环境下的具体角色,使它们拥有了丰富的人格,而不单单限于它们字面的意义。
在记叙哈扎尔国为俄国公爵斯维亚托斯拉夫所灭,建在伏尔加河口的都城在八夜之间被摧毁殆尽时,米洛拉德。帕维奇写道:“目睹者曾说,哈扎尔首都屋宇的影子好长一段时期内都萦然不灭,虽则屋宇本身早已被覆平。影子居然对着伏尔加河迎风而立。”显然,不灭的是哈扎尔人的灵魂,这才是“影子”的真正内涵。换言之,影子有其独立的人格和生命。
同样的情形也可用于写人,米洛拉德在“红书”中写到了博朗科维奇与合罕的相遇,作者说:“而与此同时,那青年訇然一声倒在自己的影子上,肩上那个袋子滴溜溜地滚到一边,他像是被勃朗科维奇的目光砍死的。”自然,这里的影子也有其独特含义,只需看看作者把合罕与“影子”当作两个地位对等的叙述主体来写就能明白这一点。
对于语言(词语、词句),作者有好些奇妙的比喻。作者说:“不过,我希望别把这些太当真,因为诗的词句不是真正的词句。真正的词句永远像树上一只苹果,树干上缠绕着一条蛇,树跟入地,树顶参天。”再如“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注意到,随着秋天的渐渐远离,词语越发成熟,像一颗果实,其果肉一天比一天饱满多汁,鲜美甘甜。到了第七天晚上,我开始烦躁不安,似乎担心我的果实熟透坠地,继而变质腐烂。”这两个比喻的共通之处在于:1、都用了果实这一喻体,形象地说明语言也会生长、成熟、腐烂。2、这两个比喻都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亦即语言是有生命的。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值得关注的是,米洛拉德。帕维奇认为,语言也是有个性的,不同的语言自有其不同的气质。显然,这使他对语言的认识更进一层,而不囿于“有生命”这一点。
作者写道:“自此发生出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勃朗科维奇一家的诸多传闻,说他们行骗时用罗马尼亚语,沉默时用希腊语,算钱时用尤太语,在教堂里唱诗时用俄语,深谋远虑时用土耳其语,仅在他们想杀人的时候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塞尔维亚语。”如前所言,语言作为一个被叙物(同时也是叙述的工具),它的个性和气质是有所变化的,随着主人公活动及心情的改变。
而在另一个例子里,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个例子是:“梅福季和他的胞弟康斯坦丁自幼便知萨洛尼卡的鸟和非洲的鸟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斯特鲁米扎的燕子和尼罗河的燕子无法用语言沟通,只有信天翁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不难看出,语言不在仅仅限于人类,它作为另一个行为和叙述主体,已经完全独立了。
之所以会这样,我想,大概与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叙事风格不无关系。据我观察,米洛拉德。帕维奇在叙述过程当中,总是力求行文新颖奇特,无论写人状物,均是如此。这样一来,他笔下的形象均现出一种荒诞、奇异的特质。
米洛拉德。帕维奇写人时常运用对比的手法,而且作为对比的另一方(不是作为叙述主体的一方),总是一些常态的人或事,米洛拉德。帕维奇就是借此来表现其笔下人物的奇特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对比的常态一方并不出现,而暗含于字里行间。
例如作者写“希腊商人”:“希腊商人一律是矮个儿,黑发,毛发浓密,胸毛甚至可以像梳头那样梳出发型,与他们一起欢宴的可汗相比之下无疑像个巨人。眼看就要变天了,鸟儿像苍蝇扑向镜子似的尽往窗玻璃上撞。可汗厚赏商人,把他们送走之后回到宴客的地方,偶尔瞥了一眼桌上吃剩的骨头。希腊人吃剩的骨头堆得像小山也似,仿佛是巨人食后遗留下来的,而可汗的却像个孩子吃剩的骨头只有一丁点儿。”这是将“可汗”作为对比的常态对象来写的。
再如作者写“苏克博士的女弟子”:“苏克博士有个女弟子,从小秃头,每夜狗来添她的脑门,从而使她头上长出了密密一层色彩班驳的首毛。她胖得没法从手指上退下宝石指环而两道眉毛则细得像两根鱼刺,头上套一只羊毛袜子以替代帽子。她睡在她的一大堆镜子和梳子上,一边打胡噜,一边在梦里找她的孩子,她的胡噜声响得使躺在她旁边的孩子没法睡着。”这里的对比比较特别,是将思想和行为对立起来了。
再比如作者笔下的斯拉夫士兵形象:“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士兵们用马和骆驼果腹,用棍子驱赶趴到他们身上的蛇,在露天依着圣树同女人****。”显然,战乱年代的士兵与和平年代的士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就语言特征来说,米洛拉德。帕维奇的状物与其写人实在是相差无几,总得来说,也无外乎求新求异一点。详细到具体的手法,则主要包括对比与拟人两类。在下文里,笔者将试着举几个小例子,借以说明米洛拉德。帕维奇是如何妙笔生花,使被叙的自然物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情绪:或哀或愁,或冷或热,不一而足。
先看作者笔下的飞鸟:“1683年塞尔维亚圣尤斯塔斯节那天,庄稼开始结冰。狗已不再出窝,靴子也被冻裂,我们笑不露齿,生怕牙齿冻住。乌鸦在绿莹莹的天上飞着飞着翅膀就被冻住,遂像石块一样坠到地上,天空只留下它们凄厉的嘶鸣。”此句重点在最末“凄厉的嘶鸣”一句,确实饱含凄伤之意,在作者眼中,乌鸦的人生、生命和意识情绪,无不体现于这种“嘶鸣”之中。
再看作者笔下的流云:“那年巴夏在他侍从的簇拥下往北而去,可是他们头顶上的云却自始至终往南飞去,仿佛要把他们的记忆带走。只此一节就非好兆。”云的情绪无疑因人而起,但又独立于人的情绪之外,二者相得益彰,都是叙述的主体。
再看作者笔下的烛火:“这时,可汗平静地打开了我卧室的铜门,室内点着一只蜡烛,芳香的烛火因他炽烈的****而不住颤悠。”只看“平静”一词,便知烛活的情绪是对“可汗”情绪的反衬和补充。
如前所叙,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语言是奇特而有生命的,但是除此之外,鉴于《哈扎尔辞典》所涉及的历史与神话传说内容,小说的叙述语言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绚丽气质和魔幻色彩。读者翻阅这本小说,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府拾皆是,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语言,则常被用来描写声音、颜色和味觉。看得出来,米洛拉德。帕维奇对此三者似乎特别敏感。
在谈及阿维尔基。斯基拉(十七世纪末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刀术师)已臻完美的刀法时,作者写道:“这一刀若刺中,会在对手身上留下一个蛇形大伤口,溅出的鲜血会发出人的喧哗声。”这当然不是写实之语,谈论它真实与否也全无意义。我们只需留心作者对声音的把握,及其所达到的传奇效果。
再来看颜色:“当时正好三面来风:从黑海刮来的风是绿油油的,从爱琴海刮来的蓝得透明,从伊奥尼亚海刮来的则干燥而苦涩。”假如不是孤陋寡闻的话,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的从颜色的角度来描绘风。风是无形无状的,也没有颜色味道,但是地域是有文化的,人是有思想情感的,这正是米洛拉德。帕维奇描写的根据之所在。他用其饱含文化情绪的眼睛去把握风,分辨其颜色气味,自然能留下如此奇丽若梦的语言。
同一道理,米洛拉德。帕维奇以同样的方式来写味道:“匈牙利人转过身子正想回他发散着红辣椒味儿的里屋......他把这话悄声译成匈牙利语。显然,他只能用他的本民族语来记数。从而一种奇怪的气息在房里弥漫开来。那是甜樱桃味儿。我明白了:这味与他的心情改变有关。......他刷一下批上大衣,店堂里立时发散出樟脑味。”这样的处理当然非常奇特,甚至怪异,但是以米洛拉德。帕维奇的思路来看,也能够言之成理,并达到其语言效果。
求新求异,也许,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