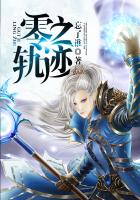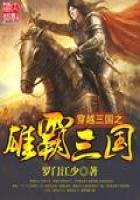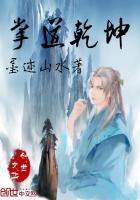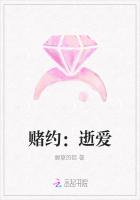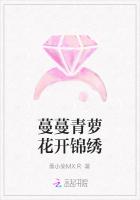今天惊喜的发现多了10个推荐,虽然不是很多,还是很鼓舞的,于是多写了千把字,虽然和那些码字大王比真的很羞愧,但是我还在准备GRE,还要做实验,还要看文献,真的是尽力了,请谅解。还请继续推荐鼓励==
==========================分割线====================================
我的大吼并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过了好半天,估计还有那个书吏四处招喊,稀稀拉拉一队队的屯兵才勉强从屋子里钻出来,参差不齐的站成数排。我沉着脸问道:你们这里谁是管事的?”
两个黑瘦的汉子站出来,依然是有气无力的应了一声:“大人,我们是。”
正要大发雷霆之际,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仔细的打量了这支队伍几眼才发现竟然人人都是面黄肌瘦,登州地方粮食亩产虽然不高,但是根据存档的资料来看,当初对本地核准上缴粮食的屯田御史还是比较公允的,每五十亩不过十石之数。当然这个不是直接的收获,由于各地种植的农作物不同,有一个统一标准折合成米,即粟谷糜黍大麦荞穄二石,蜀黍二石五斗,糁稗三石,分别等同于米一石。芝麻大豆一类经济作物则直接与米等同。但即使这样折算下来,每亩不过交大米区区两斗而已,交足那十石正粮后剩下的可都是归卫所支配,作为官军俸粮啊。固然还要经过有司登记入库再重新分发,但也不至于一个个都弄得如此羸弱不堪吧。
发现这里可能有蹊跷,虽然我还是火气很大,也不得不勉强压抑了一下,竭力平缓音调说道:“你们跟我来一下,其他人可以散了。”屯兵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又三三两两的散开了。两个军头看我拔脚就走,却又不知道我是打算去哪儿,一时愣在那不知道跟还是不跟好。还是那个书吏赶紧出来点拨:“还不快赶紧跟上大人。”
一行四人就这么沉默的走在田埂上,我听到那两个汉子在后面窃窃私语什么,也懒得去管。一直走上乡道,看到有个小茶摊,我停了下来:“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禀大人,我叫赵炳他叫李舒。”其中一个军头胆子稍微大些,局促不安的答道。
“好吧,赵炳李舒,不用太紧张。过来这边茶摊,我请你们喝茶,顺便问点事情。”走了这半天,我火气已经平复了不少,越想越觉得还是犯了毛躁,不管他们会不会说真话,会说多少真话,还是应该先问个清楚。
两个军头包括书吏显然都不是太适应和一个上司,尽管我这个上司很年青,坐在一起:赵炳和李舒都是低着头一个劲儿的搓手,姓王的那个书吏则不停的吹着茶碗里的茶,明明都已经不见茶水冒热气了还在吹。虽然心里盘旋着一堆问题,我看了还是忍不住想笑,不过也知道现在直接问他们这样紧张肯定问不出什么来。好在如何更好的和人沟通我还了解一点,当下先寒暄般的问起这两个汉子那年被征的兵,是一开始就来这边军屯还是调过来的,什么时候在这边娶妻生子的,直到两个人明显放松下来才似有意似无意的突然问了一句:“看你们的样子日子过得挺苦的吧?”
赵炳前面应得溜了,当下就答道:“是啊,日子过得苦死了……”王书吏好不容易战战兢兢把那已经彻底凉掉的茶喝下半口,一听这话立刻又喷了出来,尽管呛的咳嗽不止,还是阻止赵炳再说下去:“你对大人胡说些什么!日子怎么就不能过了?”边说边瞟了我一眼,见我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才似乎微微松了一口气。
给王书吏这一打断,赵炳也意识到说漏嘴了,赶紧没口子说道:“大人,大人,刚才我是嘴贱乱说的,日子过得不错,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天还能吃上一稀两干,比我在家穷放牛那会儿好多了。”
我听完微微一笑:“恐怕你后面这句才是胡说吧。我年纪轻,不喜欢兜圈子,实话说,在去你们营区之前我先和王书吏去看了屯田。当时我是带着一股火气过去的,看看你们把好好的秧都插成什么样子了!可是真的看到你们,我火又发不出来了。为什么?”说到这里我顿了顿,两个军头尤其是赵炳都迷惑不解的摇头。“因为我看到你们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甚至还有衣不蔽体的。照理说猫了一冬,虽然开了春农活是累人,可也不至于把正当壮年的汉子折磨成这样。我是年轻缺少阅历不错,可我不傻,几百号人都这个样子没有问题才有鬼了!”
听完这番话赵炳和李舒交换了一下目光,眼角明显溢出些泪花,嗫嚅着张了张嘴,看了王书吏一眼最后还是没敢开口。我悠悠的端起茶碗不慌不忙的喝了一口:“你们看王书办干什么?有话就直说,这里就我们四个,没纸没笔,说过算完。有什么说什么,我不会给你们穿小鞋的。”稍歇了歇,看他们还是没什么反应,“我和前任屯田郎中没什么瓜葛,这次是继承了世职才调任来的。老戚家世代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没出过一个孬种,也没出过一个奸臣。你们年纪都比我大,也不用叫我大人了,本人姓戚,叫继光。高兴可以叫我戚老弟,不高兴可以就叫我戚继光。王书吏,你也一样,不用拘谨。”赵炳李舒和王书吏一边连说不敢,但那种可以感觉到的骨子里流露出的不信任却没有了。
冷了一会场,还是赵炳开了口:“大……”看我皱了下眉,赶紧改口:“戚老弟,我们日子过得是真苦啊,还不如上战场真刀真枪和那帮子贼人干一场,哪怕死了也比现在钝刀子割肉强啊。”说着偌大一条汉子竟然扯袖口抹起了眼泪。
“慢慢说,别着急。先说说人一个个饿的皮包骨头是怎么回事?”
看我表现的极为和蔼平静,李舒也壮着胆子开口了:“戚老弟,你是不知道哇。自从我们来这里后,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开始一条光棍儿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能混着。后来在这讨了老婆,自己个儿那点口粮就不够吃了。再到后来添了娃,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基本就只能靠糠菜红苕度日了。”
我又喝了一口茶:“不对吧,我看过存档的簿子,每五十亩只交十石正粮,下剩的可就都归卫所做俸粮了,分到你们头上的也不算少。何况你们都是直接收庄稼的,哪怕打点埋伏也够混些日子了。”
赵炳一听,苦笑着问道:“戚老弟,你来之前转了一圈。你估摸屯田的地方有几百亩?我们那些人你也都看到了,你觉得有几百人?”
“就是绕了一圈,步子也不是走的很均匀,估计那一片有四分,二百亩吧。你们人么,大概百十号人,反正不到一百五。”我有一点不明所以的答道。
“唉……还是让王书办告诉你册子上登记的是多少亩,我们应该有多少人吧。”
“唔?”我把头转向了毫无准备的王书吏。他迟疑了一会采才仿佛下定决心般开口:“大人,登记在册四百亩,全员三百人!”
什么?我听完差点把手里瓷碗捏碎,田地差了整整一倍,人少了一半还多!活见鬼了,地哪里去了?人又哪里去了?我竭力镇定下来不让自己显得过于失措,头重新转向赵炳,双目炯炯的盯着他。
“是真的。”眼前的黑瘦汉子半点也没有逃避我的眼睛,涩声说道,“我来的早,有些事我也知道。那些上等田实际上都被军官或者监军的太监占了去,根本不让我们耕种。登州这地方靠海,有的地方盐碱渍上来,根本种不了庄稼了却还是算在田册里。明明两百亩不到的中田下田,硬是实算四百亩的好田,这还不算完,戚老弟你前几任管粮郎中都是不地道的,不但不管,还伙同那些军官,收粮时大斗量进发俸时小斗量出。再敲钉转角的扣个七损八耗,每月我一家三口只有一斗仓库里存的都发了霉的米啊!”
李舒补充道:“开初还能趁打粮食藏一点起来,后来不知道是哪个舔腚溜须的告了密,再收粮的时候就有兵丁看守了。年纪轻一点的实在熬不下去都偷偷的跑了,年岁大的打熬不住也累死饿死了不少,那些官也不管,倒乐得扣下他们口粮吃空饷。只有我们这样的,在当地讨了老婆,跑又跑不了,死又不得死,就这么干熬着,也不知道哪天才算到头。”
“我们磨洋工也是真的没办法了,一个个饿得脚底都发虚,哪还有力气莳秧弄稻,反正那些官老爷们也只有到收粮的时候才下来。戚老弟你是这几年头一个农忙时候下来看的,要不,光凭你说那几句话,我们也不能和你说这么多。”
我紧紧的攥着茶碗青筋微露的看着王书吏:“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些你知道吗?”
王书吏战抖抖的答道:“回……回……回禀大人,是……是真的。”看我要发作,赶紧又加了一句,“可我真的一点好处也没捞……我……我就是胆小怕事……”
“喀嚓”一声,粗瓷的茶碗终于耐不住我那能开硬弓的手施加的愈来愈大的压力,块块碎裂,“混帐!”我终于再也无法压制心中怒气大骂出声。
===============================分割线================================
本章涉及到一些换算,说明一下。当然,我说的也只是采纳了一种观点,不一定对,只是说一下而已。首先是交粮为什么以五十亩而不是亩为单位,因为明代军屯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军田一分,缴正粮十二石。我适当缩为了十石,因为登州确实不属于粮食主产区,按规定会略有缩减。
其次就是一石或者一斗到底有多重,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一石等于十斗。我取的是一斗等于现在十升,十升水是十公斤,一斗米大概十来公斤,也就是说文中一个月一家三口大概是米25斤左右,平均每人每天三两不到,而且无鱼无肉无油,可不是现在大家吃腻了山珍海味改吃野菜==
最后是粮食亩产问题,暂时我没找到资料,但是袁隆平试验杂交水稻成功前,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00公斤,而且这是有化肥有一定的机械工具情况下,生产技术总比明清时候先进许多。我看到的资料有个不准确的估计是明代浙皖苏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粮食亩产大概200公斤左右,山东登州那里还要打折扣。有兴趣的可以估算下,200亩田产的粮食,要缴400亩的粮,每亩交2斗大米(不是稻谷,稻谷两石折米一石)再发300人每人俸粮12斗大米,还能剩下什么……反正我算出来是个极大的负数--
当然,以上都是不准确估算,只是让大家可能有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另外,本章可能还有一节才会结束。下一节要解决问题了,不妨预测一下,会用哪种方式清理屯务呢?刚?还是柔?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