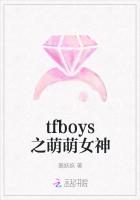承瑞将礼部呈上来的犒军单子细细阅示了一遍,抬起一双炯炯如炬的眼睛,扫向静候在一旁的礼部官员,低沉的声音冷冷的响起:“不妥,再去拟来。”
那官员已是满头汗珠,一脸惶恐,连声音也有些发抖:“殿、殿下!此次犒军钱、物之丰厚,已是我大郑天朝自开国以来罕见的了,殿下……有何不妥之处,还请殿下明示。”
承瑞将手中的单子掷在地下,冷笑一声:“自开国以来罕见?据本王所知,十年前独孤城的大军只不过平了几个南蛮小部落,其军士所得封赏皆厚于此次你们所拟的数额!别以为十年前本王只是个小孩子,就不知道这些事!还有,本次大破罗纳,受犒赏的有本王的军队、独孤城的军队,还有月惊天麾下的玉门关守军,为何月惊天的军队犒赏最少?”
“回殿下,这犒军应是论功行赏,殿下的军队立下首功,理当获赏最厚,独孤将军次之,月将军擅离职守本是死罪,功过相抵,自然犒赏无多……”
“混帐!此战首功,当属月惊天!生擒罗纳王子珂尔基、解逐鹿城之困、救本王及将士位性命,其功赫赫,所得犒赏却微不足道!独孤城的军队不过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却获赏甚丰,此等犒军之法,何以平军心?本王如何向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交待?再去拟来!否则,本王踏平你们礼部!”承瑞那张冷漠的俊脸上,已然笼罩了一层怒色,双眼中精光熠熠,直看得那官员不敢直视,拾起掉在地上的单子,用衣袖抹了抹头上的冷汗,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
待那官员离开,承瑞恨恨地咬牙用力拍在案上,直将红木几案拍得四分五裂、杯盘尽碎。
“二哥,你时常跟我说要忍,怎么这次自己倒忍不住了?不就是些钱、物的犒赏吗?何必这么认真地与独孤城那厮相争?多少大事都忍过去了,怎么区区小事倒忍不得了?”一直坐在旁边喝茶的承瑾眨着他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认真地问。
承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承瑾,家国天下的大事,什么最重要?”
“二哥很早以前就教过我,人心最重要。”
“不错,人心最重要,而军心,又是重中之重。”承瑞言尽于此,看着弟弟。
承瑾恍然大悟:“一向不与独孤族势力相冲突的定安王,为了麾下将士的利益,不惜身份去相争,确实能感动军心、誓死效忠。”
“此是不可告人的私心。另外,将士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抛却身家性命于不顾,除了多为活着的争些封赏、为死去的争些抚恤之外,还有什么能为他们做的?天下人皆知我乾承瑞年少英武、功劳等身,这些功劳,还不都是弟兄们拼死为我挣下的?所以,别的事我可以忍,唯有犒军之事,不能忍。”
“对了,我见到月来兮了。”承瑾端起茶杯来,目光没有焦点地望着前方。
“哦?”承瑞怒气尽消,表情柔和了许多,等着承瑾的下文。
承瑾盯着杯中盘旋的茶叶,说:“那天,我去送聘礼,一时兴起,悄悄从后院翻墙而入,想去她闺房吓她一跳。”
承瑞嘴角爬上一丝浅笑,微微摇了摇头。时常淘气乱来,正是承瑾一贯的风格,这一点倒与那月来兮颇为相似。
“原以为她肯定在房间里抓紧时间修习宫庭礼仪,谁想到我刚跳进去,看到她与月惊云、沐流风在花园中抚琴歌舞,自在得很。”承瑾故意把语气里加上浓浓的讥讽,掩盖住淡淡的失落。
承瑞那双冰冷傲然的双目中溢出一丝柔情:“听说,她舞跳得极好。”
“对,好极了!如天女散花,真的很美。”承瑾低了头,喝了一大口杯。片刻之后再抬起头来,脸上已经绽开了他那招牌的顽劣笑容,“待二哥把她娶进门,小弟天天去二哥府上住着,叫她跳舞给我看!二哥不要把我打出来才好哦!”
承瑞微微地笑起来:“二哥当然不会赶你走,不过,如果来兮赶你的话,二哥也绝不拦着。”
“什么——”承瑾夸张地大叫,“二哥娶了媳妇就不认兄弟了!不过……二哥,我看她性子挺辣,真个是刁蛮凶悍,二哥以后不会变成怕老婆的软汉吧?”
“再胡言乱语,打得你屁股开花!”向来严肃的承瑞也绷不住笑了起来,抬起手臂作势要打,承瑾急忙跳起来闪躲开去,军帐中绽开一串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