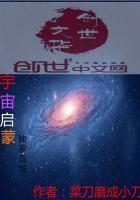原来是九月时简老太太怕知行待的无趣才买了这么一对儿八哥鸟给她解闷,不是什么名贵的鸟却机灵得很,知行断断续续地教了一个多月儿,这对鸟不但会说“你好”,而且听多了银珠的唠叨,竟然连“二小姐,放学了”都学会了。每日见了放学回来的知行,和银珠一块喊出来,长逗得知行大笑不止,因此西院里从上到下都极宠这两只鸟,知行更是当宝贝似的。
银珊叹了口气道:“平日里都仔仔细细的,也就那天鸟笼子没关好,二小姐和银珠急匆匆地出了门也忘了将那鸟提回去,等回来一看,哪还有个鸟啊。”
“那鸟飞走了?”简五爷摸了摸鹰头上黑色的翎羽,漫不经心地问。
“要真是鸟自己飞走了就好了,”银珊表情担忧,道“是叫三姨奶奶的猫给拖去了,两只都没了。如今只剩下两只空鸟笼,二小姐怎么都不肯扔,就挂在院子里的原处。”
简五爷觉得好笑,问:“她这是要干什么?”几月所见,他这个“侄媳妇”说起来最是八面玲珑,大人都做不好的“识人眉高眼低”,她却做得很好,待人处世又圆滑,谁都不肯得罪。听到她做出这般孩子气的行为倒叫简五爷想起几个月前在船上初见她的那次,让人好气又好笑,一样难缠。
“哎,”银珊叹了口气,道:“二小姐比谁都懂事,倔起来却是不管不顾,她非让三姨奶奶陪她一模一样的八哥,要不然就要将那对空鸟笼一直挂下去。”
“哈哈,她也学会欺负人了?老太太也沉得住气,眼看都到了年关了,还能由着她胡闹。不过闹归闹,凡事都得有个度,过了那个度,有理都要变无理,何况三姨奶奶又是长辈,再不收手,闹大了传到外面,她名声可不好听。”
刚谈到这里,只见棉门帘被人掀开了一条缝,有人在张望,简五爷便问:“谁?”
是门上的人,掀帘进来疾趋至简祥皓身边,低声说道:“和顺班的张班主特地来求见五爷。”
听这一说,简祥皓面上一喜,道:“快请,请到这里来就好。”
银珊、银兰知道是来了客人,不待简五爷说话,赶着就要走,“来了客人,我俩就先走了。”想想又提醒道:“五爷记得试衣服,不合适的话再交回给老太太改。”
简祥皓将那鹰往肩膀上一扛,叨念道:“罢了,还是我自己亲自去接好了。”说完就大步流星地竟先两人出了院子,留下银珊、银兰两人在房间里面面相觑,也不知他听没听见。
和顺班原来是简家养过的一个戏班子,自逊清时放了出去,班主便带着他的“水路班子”在江苏的苏、松、太,浙江的杭、嘉、湖跑码头,到一处轰动一处,着实攒了些洋钱。和顺班年年应简府的邀从初一到初七在简镇连开七日的堂会,今年因为浙奉战争的缘故到了年末生意寥落便早早来了简镇为堂会做准备。
且说简祥皓亲自将和顺班的现任班主张砚斋迎到屋里坐着,府里的佣人沏好茶,摆上了两样点心:虾仁烂面饼,核桃盒子。张砚斋三十有六,穿着件浅灰色哔叽长衫,头戴呢子礼帽,脚下是细线白袜,青礼服呢圆口布鞋,一式的新式打扮。他身材魁梧,却又文质彬彬,喝了一口茶又吃了一块点心,感慨道:“这样的手笔现如今也只有你们简府拿的出来了!”
简祥皓只微笑地摇摇头,道:“你我算起来也有四五年没见面了,莫谈这些扫了兴的话。”
“是五年没见面了,我是年年都来简镇,却是年年都看不到你,”张琴斋语带责怪,打量了简祥皓一番,想到这一路走来,简五爷的院子里除了两个老妈子,一个年轻的丫鬟都没有,问:“过了坎年,你也有二十四了,是没娶亲还是在外面自己做了主?”他自然知道简祥皓五年不曾回家的事。
“娶过。”简祥皓抿了口茶,神色平淡道。
张琴斋不由地有些失望,简五爷若是一如少年时风liu成性,这件事倒也好办了,如今他既娶了亲,看现在的样子竟像是收了心,无奈地附和,说:“娶了也好,老太太也能安心。”
“我也是经了一次才知道,孑然一身最好,何必再弄个家室之累。”
张琴斋听得奇怪,“怎么说这话?”
“婚姻就是坟墓,我死里逃生,断不能再冒着生命危险再甘愿地进去一次”
他这般一说,张琴斋也来了精神,颇有些同病相怜般地道:“你这比喻听起来倒是新奇,也对,他日有的雄心壮志都叫妻儿磨光了。”说到此,话锋一转道:“说起儿女,我可要拿个大道理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是不想成亲,屋里也该弄个人才是。你这院子里连个丫鬟都没有,显得冷清了些,我劝你还是得弄个知心着意的人。”
“知心着意,谈何容易?”简五爷起身道:“天色也晚了,不如留在这里吃饭,你在这待上一会儿,我去喊人将饭食送过来,你我多年未见,好好喝上几杯。”
张琴斋点点头,知道简祥皓的脾性。
简祥皓正要喊人过来,就见厨房里有人挑了食担来,四碟冷荤,一大盘油炸包子,居然还配了一个什锦火锅来。挑子的另一头是五斤一缸的陈年花雕。
送食物来的人从怀里掏出一本素稿,交到简祥皓手中,“二小姐让我顺带的,说让告诉张班主一声,她这几日太忙了,得了空再去班里看戏。”
“她消息挺快啊。”
厨房里的人忙回道:“这些都是二小姐备好的,她知道您和张班主关系好。”
到了年关,知行便跟着简老太太身后料理家事。府里没少人背地里说话,老太太却还坚持,也不知到底有何深意。知行是要做一件事情便要做得好,她年纪尚幼,只管理府上的小厨房,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事无巨细都处理得甚好,看得下人们啧啧称奇。
张琴斋惊咤地道:“这么快!”
简祥皓哈哈一笑,道:“小行已经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就让人送过来了。”
摆好了菜,也有几分了几丈方桌的样子,简祥皓举一举杯说:“有这个伴我,也就够了。”
张琴斋笑了,“有个人陪着你喝,不更好吗?”
“老太太托给你的事不好办,”简祥皓说:“张师哥,我是‘不要’,可不是‘不必’。”他是不要娶亲,可不是“不必”娶亲。“不必“还有几分回旋的余地,“不要”却全凭他自己的主意。
简五爷的一身功夫是跟着前任班主学的,和张琴斋也称得上同门师弟。他这声“张师哥”真叫张琴斋老脸羞红。
他面色尴尬,多年不见一见面就劝着人娶妻生子也是为了应付老太太,任任何人听了怕都是不舒服,歉意地道:“是我的错,说这些还不如我们兄弟俩说些体己的话,来,喝上一杯。”简祥皓刚才的话也让他松了口气。
如此,酒过三巡,两人喝得酣畅淋漓,天南海北地胡侃着。到了深夜,张琴斋回了班里,简祥皓才想起“侄媳妇”要自己转交的本子,便信手捏来翻了翻,这一翻却从第一页一直翻到了最后一页,素札的底面是楷体的四个字“临川四梦”,旁边又是一行小字“梦里梦,梦还醒醒还梦。”
这一出昆曲,名为“临川四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