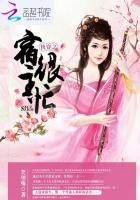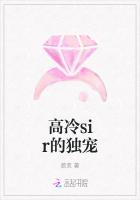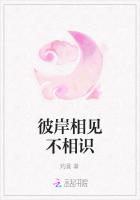世人常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样好。”
沈老夫人的离世让他不得不从任上回到祖地,居丧在家。
三年可以发生很多事,官场更是风云变化。他实在是摸不准三年后起复他还能不能捞得到一个美差。但是想到母亲这才过上没几年的好日子就离逝,不禁又伤怀起来。伤心之余那份不能为官丁忧在家失落感也便淡了许多。
在任上忙习惯了的沈父,突然间多出了好多时间,这让他一时间无所适从。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儿子沈怀远。于是便将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儿子的身上,这使得沈怀远的学问是一日千里。
三年后,沈父在吏部消了假后,上下奔走了一番,欲为自己谋得一个好的官位,但吏部却一直没有空缺。
这一年正是景泰十三年,天子突然病危京城风起云涌,诸皇子为了那把椅子拉党结派,各出奇招。各官员也是纷纷站队,安插自己的人。
这一情况使得圆滑精明的沈父,立刻停止了在吏部的打点和奔走,乐得闲置家中观望京城的风云变幻。
三个月后,原本已经是病危的景泰帝奇迹般的好了。恢复后的景泰帝以雷霆手段,压下了京都动荡的政局。
并将一干年满十五已开府的皇子,封王并勒令其十日内马上去封地,没有召见不得入京。这使得一大批提前站队的官员纷纷落马,发配的发配,贬职的贬职。
可是好似景泰帝似仍嫌这个天雷不够大。
次月景泰帝在众大臣毫无所觉的情况下。于某日的大殿早朝上,传下圣谕,并在同月由皇帝领着皇族宗老文武百官祭了宗庙。再由内阁拟昭,公告天下立年仅十五岁刚到开府年纪的皇十七子祈王为太子。
昭书的大意为:皇十七子祈,宽厚仁爱,至孝至纯……禀承天意,可承大统。
圣谕一下震得京中各方人马四仰八叉,他们做过各种设想,只是谁也没有想过先皇后所出的皇十七子会有机会继承大统。虽说他也是嫡出的皇子,但他却不是唯一的嫡子,那么一个文弱不出众的孩子在他那些哥哥的光辉下不起眼到可以让人视而不见。
景泰帝的雷霆手段使得就潘在外众王子们未及做出反应,皇十七子祈王的皇太子身份已诏告天下。
当众皇子不是忙着拉党结派,壮大自己实力,就是给互为亲兄弟的对手下套子使绊子的时候,还居在宫中的祈王子每日总会抽空去看看病重的景泰帝。即使有时候景泰帝昏迷不醒,他也是守在边上说着儿时先皇后在世时的事,几个月来风雨无阻。
也许祈王真的是至纯至孝,也许他心思深沉。但是病愈后的景帝吃他这一套,昭书一下一切都成了事实。
三个月后,景泰帝再次下诏,任内阁左相为太子太傅,并在同月册封了前任帝师的孙女,现任景朝太学院院主的嫡女为太子妃,并纳了镇国公府上的嫡出的十五姐为侧妃,内阁右相庶子的嫡长女为良娣及多位身掌要职官员家中的女眷为保林、才人。
后又请出先帝所出的永和圣长公主,代管内宫女眷。
景泰帝好像预测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他以一种燃烧生命的方式进行着他人生中最后的大动作,为他的十七子铺好帝王之路,铲平路上阻石。
景泰帝每日都将太子带在身侧,教导他为君之道,如何处理朝政,如何把握君臣之间的距离。
作为一个帝王,景泰帝虽没有太多的丰功伟绩,但他在位年间,勤勉为政,仁厚宽容。在位三十五年也算得上国泰平安,所以新帝上位后追为景圣仁泰尊帝。
然而新帝上位,根基不深的新帝忙着扶植的心腹,培养自己的手下。像沈老爹这样在从龙之时站在观望状态下的官就被闲置了。
然见过了这一年的腥风血雨,沈老爹行事越发细心谨慎。没有先前那样忙前忙后的打点,只是在吏部销了假挂了名。
虽然被闲置了,心中多有些不满。但比起那些在这次大血洗中死的死发配的发配的同僚们,他现在的境遇已经好太多了。至少他功名仍在,性命仍在,妻儿家眷安好。
回到老家的沈老爹,开始慢慢的收回父亲在时的祖宅,修善。
虽然心中仍念着他的官运,但更多的是将心事放在独子的学业上了。
在沈老爹的鞭策下沈父总算在景泰十五年得中秀才,只是名次不怎么理想未能一举拿下“禀生”的名头,只得了一个“增生”。虽说吃不了公家粮了,但却好处还是多多的。在文盲人口为主体的这个时代,民间要立文书、写信、修谱、诉讼,多依赖地方诸位秀才。秀才还可以大堂上见了朝廷官员不用下跪,只需执学生礼,不用交田赋,免除徭役,所以在地方上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算是地方的精英阶层了。
所谓知子莫若父,自己的儿子几斤几量他还是很清楚,在沈父中了秀才后,沈老爹也就没有再鞭策自己儿子一定要读书中举了。只要有了这个秀才的身份,就算自己百年后也能守得住自己挣下来家产。
对于自己这个爱读杂书不爱研究经义,策论的儿子,他也是很无奈的。儿子似乎继承了先祖的聪明才智,农耕、医、术、星象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学问也是顶好的就是不肯将精力用在科考上。数次交锋后,儿子总是上有上策下有对策,次次都以沈老爹的失败告终,久而久之他就就听知任之。毕竟再不好儿子也是自己的,况且自己的儿子为人知大义明事理,多才多艺,孝顺知礼。圣人都说“富不传三代,耕读传十世”儿子喜欢呆在这乡间农舍也不愿科举做官就随他好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嘴上虽老说“孽子不可教也!”但是为了给儿子的生活再加上一层保障,他以自己进士的身份向鲁州府学政司审请在这个离松风县有半天路程沈家村办了个私塾,一来儿子在这教书每年也能挣下个二三十两嚼头,二来能在众士子中博个好名声将来哪怕儿子想科考了也是多有助益的,三来为善乡里惠及地方真有一日自己不在了想来儿子的日子也会好过点,少一些人找麻烦,算得上是真真的用心良苦了。
沈老爹撒手不管后,沈父的小日子过可谓是风声水起潇洒得不了。松风县唯二的官方承认的学堂,在沈老爹的做镇下,沈父的经营下也是小有名气,就是邻县也有富户送来儿子就读。每年收益远超出当初的预算,因为有进士老爷做镇,又是官方承认的学塾,再加上博古通今沈父讲学时总能引古论今,使得学子们慕名而来。渐渐得使用得学堂声名远扬。
几年来,自己的几个嫡孙嫡孙女纷纷早逝带给沈老爹两夫妻的打击太大了,沈老夫人更是因为伤心过渡病重卧床,即便是三娘新生的喜悦也没能让老人家好起来,没几月便离逝了。自打贫贱不移,富贵不弃的原配离逝后他突感人世无常,在安排好家里一应事务,解下当家的重担后,便离家远游访友去了除了偶有书信回来,已经有三年未曾回过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