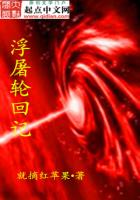回到这一幕,赵鸢儿将那小宦官带去见了訫夫人。那小宦官的名字她已经摸清楚了,叫尹应。
“姐姐。”赵鸢儿见到訫夫人便脱**到。想来距当日自己得封已经有半个月了,这几日见到訫夫人便叫姐姐;按着入宫的年份,她也该叫胡姬一声姐姐;只是胡姬的性子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她唤自己为姐姐。
訫夫人见她带了人过来,便道:“这是时下的料子?”
赵鸢儿答应了一声。訫夫人并未动作,素暖便将一干人等都打发了下去。等人都走光了,訫夫人才道:“如何?”
尹应半跪下来:“已经查到了。当日在赋桦宫内放置‘石丹落’的人是郑夫人身边的亲信,阴月。”
“阴月?”訫夫人疑惑道:“阴月是郑夫人的心腹,那这岂不是郑夫人的意思?”然后她看了看赵鸢儿,道:“难不成,你体内的‘狂罗’是她下的?”
赵鸢儿自己也感到奇怪,自从那日回来后訫夫人告诉自己体内有‘狂罗’,便已经在警惕自己的食物了。不过,訫夫人也说过,这东西不但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就像是“石丹落”那样在空气中进入人体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夫人,这恐怕不会。”素暖插嘴道。
訫夫人道:“你说。”
“那郑夫人难不成就是算准了有这么一件事,等着这样的时候来要了赵良人的命吗?不论是副掌事还是赵良人,都是韫迭宫的人;咱们韫迭宫的人可是从不会踏入她赋桦宫的,这郑夫人也知晓;狂罗就是只能到与‘石丹落’撞到一块儿了才能有反应的。”
訫夫人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不无道理。”
赵鸢儿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这‘石丹落’,是要用到一定的计量才会与‘狂罗’生效,还是如何?”
訫夫人被她这么疑问,脑中灵光一闪,道:“这‘石丹落’自是要服用到一定的计量,才能生效;服用的越多,反映便越是激烈。”
“赵良人此刻还这样好好地站在这里,而郑夫人的手段也是狠辣的,怎地可能只是让赵良人晕厥一会儿?”素暖道。
“如此说来,竟是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暗算着?只是没想到让郑夫人提前将这东西暴露了?”赵鸢儿低喃。
“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让咱们提前知晓了,也好有个应对。你保持你的日常饮食作息,不过自个儿留心着点儿,东西,都留下一些,让人为你验验。”訫夫人眼中闪过不屑:“本宫说过,本宫宫里的人儿,还轮不到别人欺负过来。”
素暖这是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赵良人,您身边可是有信得过的人在?”
显然,訫夫人也是想到了这个问题:“仆瑶可是信得过?”
说道仆瑶,赵鸢儿便想到了她见到自己手牌的情景。便开口问道:“仆瑶,可是原是夫人您身边的人?”
訫夫人奇怪她的问题,道:“自是不是。何以这么问?”
“不过问问,确定一下罢了。”赵鸢儿道。仆瑶是自己身边的人,但凭看她平日里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纰漏;何况,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地方醒来后一直都陪伴在一块儿的人,心中多少都需要自己在确定一下。
“我带着人先下去,夫人自便吧。”赵鸢儿突然没有了心情,草草便想了事。
訫夫人也随她去,毕竟她已经封为良人有半个月了,大王却没有再踏足过韫迭宫。
…………
赵鸢儿回到了自己的屋内,想到了訫夫人有交代过自己,将东西都收好,让人验验,也好让自己放心,便叫到:“仆瑶。”
仆瑶自外头进来:“参见良人。”
仆瑶作为与赵鸢儿一同从中车府令府中来的丫鬟,现在自然也是她赵鸢儿身边的贴身宫婢。
赵鸢儿道:“将我房中的香料都那一份过来。”
仆瑶有些奇怪,“良人这是要做什么?”
赵鸢儿没有多说,只是道:“你先去拿来吧。”
仆瑶知道她不愿多说,便只好“喏”了一声,下去张罗东西去了。
待到仆瑶将东西悉数拿来,她便将人都打发了出去,只留下了仆瑶。仆瑶也是感到奇怪,可在赵鸢儿面前自己总是不不敢造次;特别是在她出宫又回来后,自己便更是捉摸不透她的心思,更是不敢胡言。
赵鸢儿就那么坐在哪里,身为良人的发髻不同,但在脑后仍有青丝泻下。日光照进屋内,她的青丝显得格外黑亮。她并未坐的很端正,但今日的她总是隐隐散发出来一种威严,气场压制得仆瑶甚为不适。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仆瑶也是不敢开口说话,只是伏在地上不知该怎么才好。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许久,赵鸢儿略微沙哑的嗓音划破了空气中的凝滞:“仆瑶,你跟着我,多久了?”
仆瑶也不敢抬头回话,依旧伏在地上道:“回良人,打从小,奴婢便跟着您。”
“这么说来,竟是有十多年了。”赵鸢儿这般又像是在自说自话,仆瑶只好答道:“正是如此。”
“十多年,不说咱们主仆情分,就是十多年的陪伴,咱们这情分就当真是不浅了。”
仆瑶心中大约已经知道了赵鸢儿这到底是所谓何事,只是不到最后关头,自是不能自己将自己给暴露了,便索性什么都不说。
赵鸢儿突然走到她的身边,道:“我自从宫外回来,便时常感到身子不适,后来居然还在册封当日出了那么大的丑事,当真是愁死我了。”
她的声线并没有任何起伏,就算是叙述一件故事也是应该是有低有高,可她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平稳的声线,却更是令人胆颤。
“凭着咱们十几年的情分,你可是愿意告诉我,是谁让你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或是……是谁在后来收买了你,让你,不再对我有衷心?”
即便是说着这样让仆瑶心颤的话,赵鸢儿的声线依旧没有任何起伏。而仆瑶却是一惊,继而继续伏地道:“良人这是说的什么话?奴婢……奴婢怎的会做这样的事情?”
“或许……”赵鸢儿突然提高了音调:“看着我回话!”
仆瑶被赵鸢儿这一声厉喝吓得不轻,立即抬头,看着她道:“奴婢万万不敢做这样的事,良人明鉴!”
赵鸢儿低头看她,“你或是身不由己。你可认得此物?”赵鸢儿将訫夫人给自己的手牌拿了出来。之前的那块与这块有区别,之前那块是白色,而现在这块是红白相间,煞是好看;不过,上头的图案,或是字,还是没有变。
仆瑶一见那手牌,眼神闪烁了一下,道:“良人可知,那上头是什么?”
赵鸢儿将手牌收起,道:“不知道,才要问你。你既是这么博学,想必你身后的那位高人,也为栽培你花费了不少心血。”
仆瑶突然将头重重地叩在地上,道:“算是奴婢求求您,若是得了机会出宫,再莫回来了!”
赵鸢儿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和言语惊呆,道:“你何处此言?”
仆瑶抬起头,赵鸢儿清晰地看到她的脑门上已经有血流下来,虽是细细的一条,但也可以看出方才她叩头是有多么用力。仆瑶道:“良人您应该再清楚不过,这宫中有的是人要害您,只怕还不是一帮人;只要您离开,就可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不就是您一直向往的吗?”
赵鸢儿蹲下,看着她的眼睛道:“那么,你是哪一帮人?”
仆瑶却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将话题转到了韫迭宫上:“良人既然可以拿到红白手牌,足以见得訫夫人对良人的信任与看重;但訫夫人在宫中的日子未必就能过的长久,只怕他日訫夫人失势,会连带了您!”
赵鸢儿却没有理会她的话,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问道:“我问你,你是哪一帮人?”
仆瑶看着她,两人又进入了僵持的状态。赵鸢儿一直那么看着她,仆瑶便深吸了一口气,道:“奴婢是‘主子’的人。”
“主子?”赵鸢儿皱眉。
“不知姓甚名谁,主子是宫里暗势力的代表,但却鲜为人知,除非是内部的人。”
“你可知道还有谁?”赵鸢儿问。
“主子在每个宫里都有内应,但每个内应之间都不知道谁是自己人,这是为了让我们万一要处理内部人的时候,心中没有顾忌,不必手下留情。任何内部人之间,相互都不知晓。”仆瑶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哀戚。
“你的主子让你做的,是什么?”
“主子让奴婢做的,只是监视良人,其余并未做什么。只是因着内部的人相互并不知晓的关系,奴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什么人害了良人,所以良人,您能逃开就逃开,好吗?”
赵鸢儿替她擦了擦额头的血迹,语气软了下来:“仆瑶,我还不能走。但你……你能为我做些什么吗?”
仆瑶立即点头道:“奴婢与小姐自幼一块儿长大,为了小姐奴婢什么都能做!”
赵鸢儿道:“可不记得从前发生的事,你可是愿意一一讲述给我听?”
仆瑶点头道:“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