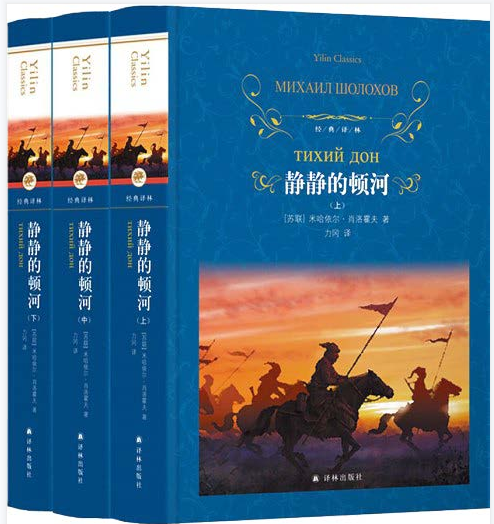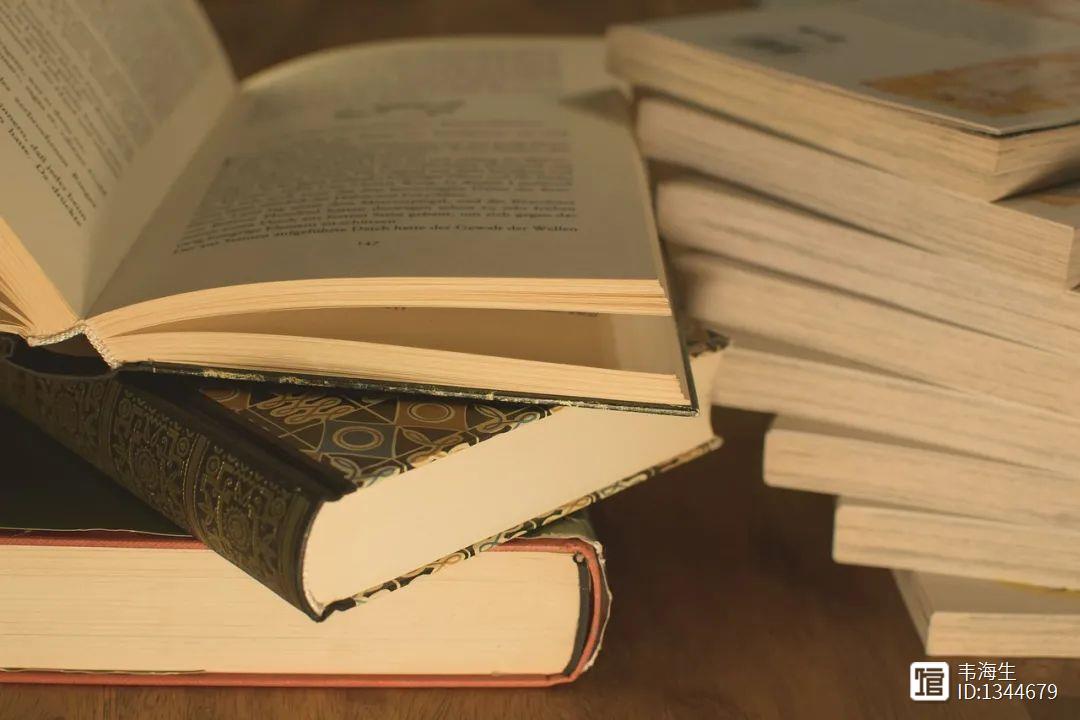晴雯和袭人到底哪个更好?脂砚斋一句批语透露答案
优秀的文学作品,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世间百态,很容易让身处红尘中的读者有代入感,不自觉地扮演其中某个或多个角色,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些其实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一切,仿佛都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经历。
《红楼梦》中,红粉无数,佳丽万千,每一位读者应该都会各有取舍,但相信性格鲜明、容貌出众、伶牙俐齿的晴雯会是众多红迷朋友十分喜爱的梦中人形象。她悲惨的夭亡,以及贾宝玉为她杜撰的催人泪下的《芙蓉诔》,更是为她赢得同情票无数。
但是,“深知拟书底里”的脂砚斋对她却不无负面的评价,如“晴卿不及袭卿远矣”(第八回)、“写晴雯之疑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轻轻抹去。正见此时都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后渐大渐生心矣。”(第二十回),与她对袭人不吝溢美之词形成鲜明的反差。
个人品读脂评本深有体会,那些事关文本立意大旨的批语往往欲言又止、点到即止,有些甚至看起来莫名其妙,但是,意会到其中的深意,就会发现石破天惊的“甄士隐”,这些批语绝对不是“不知拟书底里”的局外人所能作出来的,因此,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挑战脂批的权威性。《“行”走红楼》系列拙文关于袭人的部分,已经论证了,确实如脂批所云,花袭人当得起“花气袭人知昼暖”之诗句。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红楼梦》。每个读者的心中,也自有一个自己的晴雯和袭人。从我有限的阅读量来看,对待袭人,似乎贬远远多于褒,与对待晴雯褒远远大于贬,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认知与脂批大相径庭?“晴卿不及袭卿远矣”的原因在哪里呢?
用“大旨谈情”的“贾雨村言”敷演的“甄士隐”之文本,“表里皆有喻”,如双面风月鉴一样。之所以我们的认知与脂批大相径庭,是因为我们并不习惯阅读具有所谓正反两面的独特文本,我们只会见到满纸流情的风月宝鉴正面,而风月宝鉴背面恰恰处于我们通常习惯的阅读视觉的盲区,我们看不见,但“深知拟书底里”的脂砚斋“看见”了。
作者在家族百年繁华落尽之后,借“一番梦幻”回望百年沧桑风云,其中既艺术再现了家族的盛衰史,又暗喻了清王朝的兴亡史。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反思了其中的得与失、利与害,并提出了智慧解决之道。
作为“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脂批)的正统之象征一一秦可卿(胤礽),他的人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悲剧一一政治上高开低走,“登高跌重”,最后连人身自由都失去。即使远离了政治中心舞台,回归世俗生活,也不得善终,被迫在“一座高楼上悬梁自尽”。

胤礽的梦中化身秦可卿“语语见道,句句伤心”(脂批)的魂托,其中蕴含了古老的处常之道一一“耕读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之智慧。当然,这其实是繁华落尽之后,作者在自己和家族惨痛经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超凡智慧,给出的独到而又深刻的解决之道。
显然,作者有所取舍,对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持否定态度,而对平凡安稳的世俗生活持积极的态度。因此,正如第五回脂批所云,“是作者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撰成此书”,红楼文本在“大旨谈情”的正面之下,还是一部恢弘壮阔的社会与政治之史诗、一部“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第一回脂批)的处世智慧之圣典。当然,这一切只存在于“甄士隐”之风月宝鉴背面,我们必须探究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大旨谈情”的“贾雨村言”之隐寓,才能“心传神会”。
作为“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秦可卿只是这部浩繁巨著中的匆匆过客,但却是文本中最大的“甄士隐”之一,而宝黛钗作为通部书中最重要的三个梦中人,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就是最重要的“甄士隐”、“大旨谈情”的“贾雨村言”,没有之一。
入了“薄命司”的秦可卿所谓的“兼美”中,既有钗,又有黛,因此,“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的钗黛,也同入“薄命司”。脂批指出,秦可卿之乳名兼美“盖指薛林而言也”,而秦可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因此,在太虚幻境中“兼美”于秦可卿的钗黛,还是诸芳之冠。

从风月宝鉴正面看,作为两个鲜活的艺术形象,“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第五回脂批),“世人性分甘苦不同,目中各有所取”(第五回脂批),作者也没有褒钗贬黛之意或贬钗褒黛之意。
但是,在风月宝鉴背面,“兼美”于秦可卿的钗黛却各有隐喻一一黛玉的前世今生与“密”密切相关,“密“作为胤礽的谥号,具有政治意涵,而她的别号“潇湘妃子”,是亡国之典,与她一生的泪水相对应,同样具有政治意涵,因此,林黛玉隐喻秦可卿的家国政治部分;服用“冷香丸”的宝钗,是秦可卿魂托的耕读智慧的忠实践行者。“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她,安分从时,又不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壮志,是文本中集生活智慧之大成者,因此,宝钗隐喻秦可卿的世俗生活部分。
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是“作者自己形容”(脂批),他们的幻像一一癞僧跛道也可称是作者的化身,“通部书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第三回脂批)。作者对跌宕起伏的政冶人生持否定态度,而对平凡安稳的世俗生活持积极的态度。因此,他的化身之一一一癞僧说,黛玉之病,“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这意味着“惟宝玉是更不可见之人”(脂批)。不仅如此,癞僧跛道还让林黛玉既无“冷香丸”,又无与“通灵宝玉”相配之物,只有用一生朦胧泪眼与宝玉相对。
与此相反,癞僧送的、錾于薛宝钗所佩戴的金缨络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与癞僧镌刻于"通灵宝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是“一对儿”。宝钗服用的“冷香丸”,药方和药引子也是来自于癞僧。其实,“冷香丸”与“通灵宝玉”寓意相通,也是“一对儿”。贾宝玉在“情”里感悟,也在“情”里成长,最终将成为“情不情”的情僧,即达到“除邪祟、疗冤疾、知祸福”(癞僧镌刻于其上)的“通灵宝玉”之境界,类似于在幻境中时隐时现的癞僧跛道。所谓的“通灵宝玉”之境界,是以入世之心出世,心中有佛,有万民,悲天悯人,与“冷香丸”之境界一一以出世之心入世,不为物羁,不为媚俗,而自成高格,是相通的。

因此,从处世智慧而言,作者的本意就是宝钗才是最好的选择,而黛玉不是。在“表里皆有喻”的文本中,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从时,自云守拙”,总是稳重和平,包容大度。而黛玉“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第八回李嬷嬷语)、“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第八回宝钗语)、“小性儿,行动爱恼”(第二十二回湘云对黛玉的评价)、“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第二十七回宝钗心中的黛玉)、“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第二十七回小红之评价),因此才有.与宝玉“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第二十一回脂批)。
在文本主舞台一一荣国府的众人眼中,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红楼梦中人,“妙在全是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之笔,若看其写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第三回脂批)。第八回脂批指出:“晴有林风,袭为钗副”,因此,在以梦幻形式呈现的文本中,晴雯与黛玉、袭人与宝钗有着神奇的联结,而作者对于钗黛的不同人物设定,已经让晴雯与袭人相比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晴卿不及袭卿远矣”的原因就在于此。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晴有林风”,但晴雯还真不是黛玉。作者原本的人物设定就是钗黛“名虽二个,人却一身”(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第四十二回作者让钗黛合二为一,宝姐姐关于耕读的一席话就消除了黛玉的所有芥蒂,两人从此情同姐妹,甚至连赵姨娘都能以礼相待,合二为一之后的黛玉,当然也是晴雯所不能及的。
作者:郭进行,本文为少读红楼原创作品。
薛宝钗和王熙凤关系不咋地?其实贾探春和林黛玉也一样
紫网2023-10-16 11:06:050000社会剧变下的小人物命运
王兆善合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最后一页,心情颇不平静,社会剧变下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让我叹息不已。1965年,《静静的顿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深刻描述了从1910到1920年这前后十多年间顿河流域哥萨克人被改变的生活,涉及一战、十月革命、俄国内战等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生动反映了葛里高利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充满迷茫痛苦的悲剧命运。 王兆善2023-07-29 08:10:540000
王兆善2023-07-29 08:10:540000书单 | 我的私人书单10部
-第123篇原创文章-我有一份私人书单,里面有10部书,基本上每年都会更新一次,把其中的一两部替换掉。不过2022年我就没有更新,在《私人书单十部》这篇公众号文章里,还是停留在2021年的版本。在文章里我也说了,这十部书并非全是经典名著,只是我喜欢读而已,入选的书中外兼有。可是这两年来,除了一些技能类的书要读之外,我读老祖宗的东西更多一些。 韦海生2023-07-27 19:28:250000
韦海生2023-07-27 19:28:250000被偷脸造黄谣的女孩:AI脱衣成黑色产业链,施害者被隐藏
2017年,国外著名成人网站Reddit上出现了一段《神奇女侠》主演盖尔·加朵的小黄片,这个视频利用深度伪造(Deepfake)合成,将盖尔·加朵(右)的脸替换了色情女星的脸。至那时起,深度伪造名人色情内容一发不可收拾,斯嘉丽·约翰逊与艾玛·沃特森等明星都曾惨遭毒手。但如今,伪造色情逐渐盯上了普通人。只要你在网络上发布过自拍,人工智能都有办法帮你“一键脱衣”,规范AI色情内容刻不容缓。 译言2024-02-18 12:06:280000
译言2024-02-18 12:06:28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