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周振甫的《诗经译注》(续)
我读周振甫的《诗经译注》
我读周振甫的《诗经译注》(续)
吴营洲
读着周振甫的《诗经译注》,时不时地会感到有些纳罕:一个“文论专家,资深编辑家”,一个出版社的“编审”,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常识性错误”,或令人“匪夷所思”的翻译?如下,是我翻阅该书时信手摘抄的几则:《王风·兔爰》的末几句是:“……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该书译成了:“……我的生活到后来,碰到这样百种凶。还是睡着耳不聪。”——原诗中的“无聪”,是“不想听”,并不是“耳不聪”。“耳不聪”易被人理解为“耳聋”。“不想听”与“耳聋听不见”不是一码事!《王风·大车》的首句是“大车槛槛”,该书译成了“槛槛发声是牛车”。——窃以为,这样的翻译固然不能说错,但是,何必要译成“倒装句”呢?直言“牛车发出槛槛声”不是更口语、更通畅吗!该诗次章的首句“大车啍啍”,该书译成了“牛车开得慢又重”。实话实说,这译得就有点奇葩了!“牛车”是“开”的吗?能“开”吗?谁见过“开牛车”的?况且,“牛车开得慢”或也可以理解,但是,怎么能说“牛车开得重”呢?《郑风·羔裘》三章中均有一句“彼其之子”,该书均译作了“那个是自己的人”。为何这样“译”?该书未作任何说明。这或也是该书的缺憾之一吧。就我的目力所及,这句“彼其之子”,程俊英、王延海译作了“他是这样一个人”,徐志春译作了“穿着皮袍子的那个人”,高亨的注释是“他这个人”。就常理而言,既然作了有别于他人的解读,总该给读者一个说明;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注释也行啊。然而没有。这令人无从判定他的所“译”是对是错,尽管相信他是有所本的。另,“彼其之子”一语,在《诗经》中似乎出现过五次(指五首诗中)——《王风·扬之水》《郑风·羔裘》《魏风·汾沮洳》《唐风·椒聊》《曹风·候人》,该书分别翻译为:“那个自己乡里的人”“那个是自己的人”“他是我自己的人”“那个人的儿子”“那些他们的人”,大同小异,但均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同。《郑风·褰裳》的首二句是“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该书译成了:“你惠爱地想我,我提裤和你淌溱河。”——严格说来,第一句“你惠爱地想我”当是没有错的,但听来总感觉怪怪的:其一,“惠爱”的本义是“仁爱”;其二,感觉像是个“民国人”在舞台上说“国语”。第二句“我提裤和你淌溱河”也当是没有错的,但听来同样感觉怪怪的:其一,提着裤子“和你淌溱河”,很有画面感,但在时下的人想来,疑似欠雅,提个裤脚或许还行;其二,“褰裳涉溱”的意思,或也不该是“我提裤和你淌溱河”,当是“你就提裤淌着溱河过来”。《郑风·风雨》中共有三句“既见君子”,该书均译作了“既然看见君子人”。——窃以为,这句“既见君子”,委实无需翻译,任谁一见就懂,但是为了凑字数或为了合辙押韵等,译作“丈夫已经回家来”(程俊英)、“既见君子来相会”(于夯语)、“看到丈夫回家来”(王延海语)、“既见丈夫进家门”(王延海语)、“已见丈夫到身边”(王延海语)等,或也未尝不可,但是,该书译作“既然看见君子人”就疑似欠妥了。因为该译有了歧义。原诗中的“既见君子”,其实是“面见了君子”,并不是“看见了君子”。“看见了君子”或有可能被误认为是“远远地看见了君子”,这是与原诗的题旨不符的。《唐风·绸缪》中有一句“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该书译作了:“你呀你呀,像这样不约的人怎么办啊?”——读了该译,我不禁在想,该书怎么会如此翻译“如此邂逅”呢?众所周知,“邂逅”就是“不期而遇”啊!即便是该书对“邂逅”的注释也是如此,只是加上了“爱悦者”这个定语,称其为:“不约而来的爱悦者。”因此我思来想去,感觉是该译该是:“你呀你呀,像这样不约而来的人怎么办啊?”这或是该书出版时丢了“而来”二字,属于校对有误。《秦风·黄鸟》中有着反复咏叹的四句话:“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该书将此四句译成了:“那个苍天啊,灭亡我的好人!如果可以赎啊,人愿百死他的身。”——坦率地说,我真的被其所译的这句“人愿百死他的身”给惊着了!我的第一反应:“这不是猴吃麻花满拧吗!”怎么能是“人们愿意让他死百次”呢?我想任何人都清楚,“人百其身”的意思就是“愿用一百个人来替换他”。这意思我想该书作者肯定懂。但他又为何译出如此奇葩的句子?于是我就反反复复地读其译文,发现,是其译“有歧义”。对“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句,程俊英的翻译是:“如果可以赎他命,愿死百次来抵偿。”王延海的翻译是:“如果可以赎他命,愿用百人来抵偿。”于夯的翻译是:“如能赎他回,百人换他身。”我想,如果该书作者不想如此中规中矩地译,非要有自己的“独创”,那就将其译中的“他”,换成“自己”,即:“如果可以赎啊,人愿百死自己的身。”如此或就不会“有歧义”了。《陈风·东门之杨》一诗共二章,各章中均有“昏以为期”句,该书均将此句译成了“昏暗作为相约的时期”。——在我印象里,诸多注释皆称:“昏:黄昏。期:约定。”即,“昏”不是“昏暗”,“期”也不是“相约的时期”。说句不好听的,总觉得该书所译的这句“昏暗作为相约的时期”简直不像是人话,最最起码的,不是两个相恋的青年男女所约定的话。程俊英将此句译为“约定相会在黄昏”,王延海将此句译为“约定黄昏来幽会”,于夯将此句译为“人约黄昏时”,意思相同,都很恰切。《小雅·苕之华》的末二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该书译成了:“人可得饭吃,少有人可吃饱相求!”——请问:“少有人可吃饱相求”究竟是啥意思?再请问:这是一个正常人所说的正常话吗?《大雅·棫朴》末章的前二句“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该书译成了:“雕琢他的文章,金玉是它的质量。”——我总觉得“质量”是一个现代的物理名词,且不说该书对此二句翻译得是否恰切,但是用这样一个词,就似乎有种“违和感”。…………窃以为,我挑该书中的“毛病”,未必真的就是“不贤者识其小者”。看官明鉴!客观地说,该书的翻译,自然有许多是对的。这是无需赘言的!翻译对了才对啊!翻译错了才不对啊,才不正常啊,才有愧于或有罪于读者啊!重复一句:该书最大的“毛病”,在我看来,是对每首诗没有“题解”,即没有点明每首诗的主旨或大意。尽管有些诗的“题旨”是有争议的,但该书作者肯定能“择一而从”,或“另有卓见”的,不然就不能对原诗进行翻译或解读了。可该书作者为何不把自己的观点坦陈给读者呢?别忘了,该书是“国民阅读经典”丛书里的一种,属于通俗读物或普及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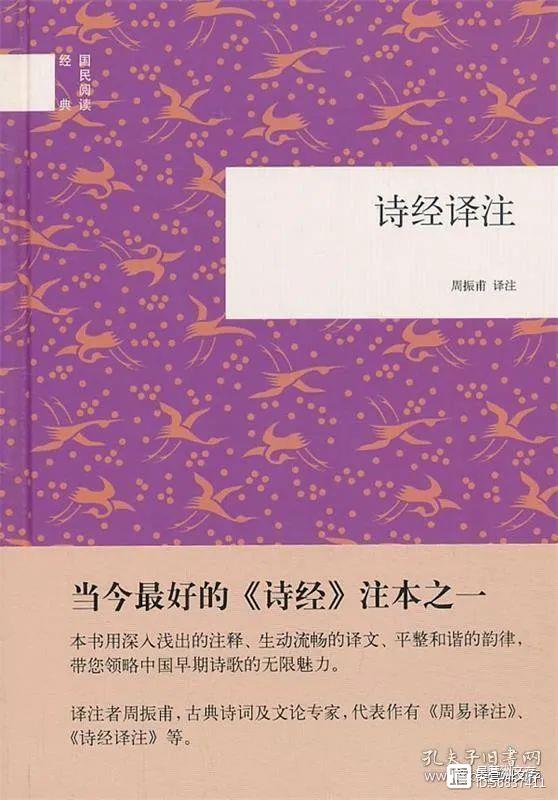
阅读7堂课:学会这10种方法,一年轻松阅读100本书
后台回复”写作“-领取写作干货▼买了一堆书回来看,想着提升自己,最后却堆在角落里落满了灰尘。工作太忙,生活琐事太多,根本没有心思看书。看了很多工具书,能力却没有任何提升,还是停留在原地。你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三种情况?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之所以会出现“没空读书”“读不进去”“读了没用”这三种情况,是因为你没有用对方法。紫网2023-10-16 15:38:160000邢夫人打了王善保家的一顿,探春认为是掩人耳目,到底是真是假?
王善保家的在抄检大观园时上蹿下跳,表演过火,被探春一巴掌糊在脸上。第二天,探春就派人打听后续,听到的消息是“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大太太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纨都认为这个处分正确合理:“这倒也是正理。”但是探春不肯相信:“这种掩饰谁不会作!且再瞧就是了。” 栖鸿看红楼2024-02-01 10:10:180000
栖鸿看红楼2024-02-01 10:10:180000友谊的衰退:我们现代人害怕孤独,又恐惧交友?
有研究表明,没有密友、感到孤独这件事,对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天吸15支香烟。我们很难仅仅从数量上得出关于一个人友谊质量的结论。有时候,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没有朋友。孤独,从某些方面来说,仍然是一种污名化的状态。最近,在欧美有一个现象,叫做“友谊的衰退”。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丹尼尔考克斯曾用这个词来描述缺乏一定数量的亲密朋友的人数的增加。 译言2023-07-28 09:14:220000
译言2023-07-28 09:14:22000016年后再看《色戒》,才发现汤唯的牺牲,远不止被删掉的那7分钟
16年前,影片《色戒》上映后,作为主演的梁朝伟携女友刘嘉玲一起走进影院,结果才看到一半,刘嘉玲就铁青着脸出来了。面对记者的围追堵截,她稍稍顿色道:“梁朝伟是一个演员,演好戏是他该做的。”众所周知,影片中让刘嘉玲脸色难看的,无疑是梁朝伟与女主演汤唯在剧中的亲密互动。 晓读夜话2024-02-06 13:05:260000
晓读夜话2024-02-06 13:05:260000从农村喂猪女,到被张艺谋劝退的“最丑谋女郎”,魏敏芝后来如何
24年前,张艺谋的新作《一个都不能少》上映,影片大热的同时也带红了作为主演的乡村姑娘魏敏芝。这个原本割草喂猪忙农活的女孩就这样一夜成名,面对扑面而来的名利以及各种签约邀请,她感到不知所措。对此,曾经坚定选择她作为女主角的张艺谋却一反常态,不仅不支持她,还直言“魏敏芝长得不好看,身材也不好,当演员没希望”。这些话如同一声声警钟,敲碎了魏敏芝的演员梦,也让她一度被网友戏谑为“最丑谋女郎”。 晓读夜话2024-02-06 14:11:100000
晓读夜话2024-02-06 14:11: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