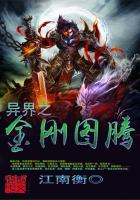转眼又是一年春。过了除夕、赏了花灯,正月已过去一大半,日子不知不觉地就又转到了三月阳春。宫中相安无事,朝野也是一片清明,除过几个月前陆隐溪于玉镜城惜败退守勒马关,对于敬赫人来说这一年几乎无遗憾可言。
蒋清寒任刑部尚书后的第二天立刻给祚承帝上了折子,奏明禾州一事,祚承帝朱笔批道:“能者代之。”而蒋清寒折子上明明白白地写了“臣愿亲往”,不知祚承帝是不是有意留他在京城,竟未作应答。于是禾州也终于有了动静,刑部尚书见自己去不得便立刻派人星夜前往。禾州一带的江湖帮派见换了不知深浅的新知府,也稍休了战事,静静观望。
三月十三这天,董慧如特地起了个大早,捧着从锦湖苑新借的前朝诗稿来到御花园。小池畔柳色青青、春光融融,坐在柳荫下还时有迎面而来的和煦微风。她就着阳光读书,海棠在她身边刺绣,不时地整理一下凌乱的彩线,两人闲下来了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海棠见她手里的诗稿换了一本,从前朝诗人所著的集子变成了这些年积下来的锦湖苑联诗。开头一首是萧怀雅的《秋夜题》,第二首是江见雨的《寒花词》。这两首诗皆为七律,所写皆为秋景。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便是前者辞工华丽雍容,洒脱大气;而后者诗骨孤冷清绝,凄凉哀婉。
按说此二人才子名声在外,所写之诗也都是值得一读的好诗。可是董慧如刚刚仔细读完了头一首,读到第二页时匆匆瞟了一眼就翻了过去,目光里满带着不屑。海棠起初以为那篇《寒花词》是她早就读过了,也没在意,后来发现她翻集子的时候总是刻意跳过一些书页,那些书页上几乎都有相同的一个名字——江见雨。
诗集是从五年前开始收录的,那时萧怀雅十四岁,江见雨十三岁,两人明明都是孩子却早已定下了诗风。这一定就是五年,想来以后也不会更改。徐继曾说过诗文见人心,是什么样的人就该写什么样的诗。纵然旁人刻意模仿,也最多做到形似,神却相去甚远。
董慧如翻完第一册,打开第二册。第二册里多了一个名字:董思微。可怜太子当时年少无知,要换在今天他绝不可能将儿时玩笑之作留在七王府里——他的处女作名叫《咏湖畔山龟二三只》,通篇大白话不说,用韵还用得极勉强,直笑得董慧如眼泪横流。
太子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十三四岁的诗作被七皇叔偷偷收录在了那本诗抄中,与自己两个好友同一时期的作品摆在一块,风格迥异、对比鲜明。倘若这些诗集让他发现了,恐怕难逃焚毁厄运吧。
好在他“一枝独秀”的日子并不算长久,第二册末尾出现了一个与他诗风极为相像、文笔酷似师徒的人。这个人的首篇甚至有个更为惊艳的名字——《苦思三夜无所得聊以无题为题却不知所咏何物》。董慧如费了半天劲,终于弄明白了这个最长诗题的意思——“我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不知道我的诗该叫个啥名,好容易取了个无题作为题目,又不知道往下该写些什么”。她喘着气翻译完又情不自禁地给诗人加了一句“作诗甚苦虽苦吾亦作之竟不知吾所想何事”,加完自己翻译道:“写诗真烦人,即便烦人我也还是要写,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往诗题下方看去,不出意料地看到豪气干云的三个大字——陆闲歌。还是亲笔。
董慧如扶额叹了口气,心道这后头的联诗可不敢看了。晦涩的晦涩、白话的白话,要联成整首诗非得把人看成疯子不可。
正想合上书,海棠忽然放下针线问道:“公主,我见您读诗时总是挑着看,要是错过了佳句岂不可惜?”
董慧如不耐烦道:“我可没挑着看,分明是一首一首读下去的。谁叫皇兄和闲歌姐的文笔过于粗犷豪放,我实在受不了才跳过一两页,这你也要管?”
海棠忙跪下辩解道:“奴婢没有别的意思,公主怎么读书奴婢自是管不着的。只是……”看出了董慧如心中烦躁,她正犹豫着要不要把无意间的发现告诉她,九公主却自己说了出来。
“有人欠我一个解释。在他亲口说清楚之前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读他的诗文。听明白了么?”
海棠小心斟酌着措辞:“奴婢虽不知道公主和江公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可您总是躲着他,他就算有心道歉也毫无机会啊。”
董慧如冷冷道:“他若是有心,就总能找到机会的。海棠,你别忘了他是什么人。”
日过正午,东风拂过,杨柳低垂。除了鸟鸣,御花园里安静得连一池清浅的碧水也不曾泛起波纹。董慧如站起来伸了伸胳膊,差海棠去锦湖苑还书,自己摇着团扇意兴阑珊地回寝宫去了。都说春困秋乏,董慧如以前从不嗜睡,这话给她听到了只会轻哼一声,说就会给偷懒散找借口,累了就睡睡够了就醒,和季节有什么关系。可现在她一人坐在空空的屋内竟也打起了哈欠,一倒头就睡熟了,还睡得格外久——直到半夜还没有醒来。
董慧如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她穿着血红的嫁衣站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听着寒风在耳边嘶吼。荒原上九月就下了雪,北风吹面如刀割,疼得她睁不开眼睛。不知道为什么她想哭,一哭泪水就被寒风拍散了,脸上留下一道道生疼的泪痕。她就这样一个人在风雪里走了很久,分不清南北东西,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远处天与沙相交的地方逆光走来一个人,那人齐肩卷发,劲装短袍,牵着一匹绛红色的高头马。与他擦肩而过时,她只觉得那人身影熟悉,却偏偏想不起他的名字来,生生错过了叫住他的机会。他好像不认识她一样越走越远。大雪骤至,她鲜艳如血的嫁衣在北风里翻飞,忽而又被大雪淹没。荒原上的风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征兆,不知走了多久,她看见雪地里躺着一个人。那是一个单薄的年轻人,青衣似水,黑发如墨。他闭着双眼,睫毛垂下一层好看的阴影。她大声呼喊却怎么也喊不醒他,无意间手指触到了他的后背,指尖沾染上一片触目的鲜红。
她猛然抬头,不知何时自己与那青衣人已被身穿黑衣的青炎教徒围在中间。他们默诵着古老的青炎卷,手中的兵器在黄昏的风雪里寒芒凛冽。她就这样死死抱着青衣人不愿松手,感受到他温热的血一层层渗透了自己鲜红的嫁衣。在长刀向她头顶举起的那一瞬,她闭上了眼睛。四周的风雪好像在那一瞬停了,荒原上静得可怕。然后她释然一笑,听见了利刃穿透血肉的声音,乍然惊醒。
清泪打湿了枕巾,冷汗浸透了中衣,她从未如此疲惫地梦中醒来。
对上她朦胧睡眼的是一个身穿黑斗篷的蒙面女人,像极了梦里的青炎教徒。她失声尖叫,那人赶忙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手缓缓摘下面纱,露出一张柔美的脸。
“三皇嫂?”
梅笑儿小心地四下张望,确信那声短促的尖叫没人听见后,冲她点了点头。董慧如斜了一眼漏壶,已经是三更了。她心里纳闷,寝宫内外都有人值夜,梅王妃来访不会不通报。难道是自己睡得太沉没听见?
“我见你门没锁就自己进来了,没想到把你吓得一头汗。”
董慧如待怦怦乱跳的心稍稍平静了,道:“我不要紧。三皇嫂深夜前来,想必是有急事?”
梅笑儿的腹部已高高隆起,此时行动颇为不便。可她刚听罢这句话,硬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流着泪颤声道:“慧如,九皇妹,救救我。”
董慧如心里咯噔一下,忙道:“三皇嫂快起来说话,当心硌到肚子。出什么事了?”
“有人要杀我……”
“咳,”董慧如只当她做了噩梦还未清醒,“皇嫂回去睡一觉就没事了。宫中处处有人值夜巡逻,谁敢造次?”
“真的有人要杀我!”梅笑儿跪着不动,瞪大了满是泪花的眼睛无助地看着她,“这个人杀我就好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我逃不掉的。你说宫中处处有人值夜,可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值夜有什么用!慧如,救救我,救救我……”
值夜有什么用?董慧如回想起自己刚醒来时看到的那一幕,背后一寒。她虽不信真的有人要害梅笑儿,但也不像刚才那样觉得轻松了。
“既知道是谁要杀你,差人去将他擒回,交给刑部处置便可。若皇嫂不方便走动,告诉我便是。”
梅笑儿头摇得像拨浪鼓,发髻都险些摇乱了。她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好像想起了什么异常可怖的人。董慧如见状,拍着她的肩安抚道:“皇嫂莫怕,这里除了你我再无他人。你要是信我,大可告诉我那人是谁。”
梅笑儿死死抓住她的衣袖,哭得梨花带雨。她努力平了平气息,抽泣间断断续续地吐出一个名字来。
董慧如听后当场愣住,久久不能言。
“董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