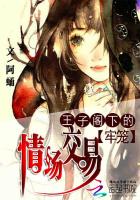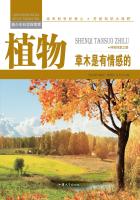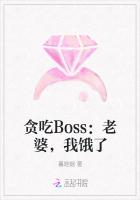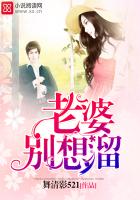在概括中国文学的形式特点时,巴赫金看到诗歌在一个长时期内是这一文学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体裁。他指出,作为中国文学之真正开端的《诗经》就是一部诗集。中国的诗具有"固定的格式和节奏"(律诗),其中"形式居于主导"地位。从"第一位诗人"屈原的"哀歌《离骚》"及全部《楚辞》起,中国诗歌艺术便不断发展,至唐代出现极大繁荣,"唐诗选"中有两千作者(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等在内)的五万首诗,"这是古老中国的民族骄傲"。唐宋以后,这种"高雅的古典诗歌"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长篇和中篇小说以及戏剧"的发展。巴赫金没有忽略这一重要现象,即:小说与戏剧在长时期内"未得到正式的认可",被称为"俗文学",因为它们是"与程式严格的儒家诗歌相对立"的,使用"较为平易的语言";但是,这些作品在数百年间上百次地刊印,最终还是被归入了中国的优秀创作之列。巴赫金还谈到了一些著名小说的特色,如他认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有心理刻画,概括的性格",运用了"拟人手法";《红楼梦》"篇幅巨大,人物达数百之多",有着"复杂曲折的情节"和对于繁复的日常生活的生动描写;《水浒传》是一部"惊险的历史小说",以历史上的人民起义为背景,可称之为"中国的英雄史诗";《金瓶梅》则是一部"性小说",写的是"一个富贾的情爱史"。清代的小说《九尾龟》,巴赫金是将其作为在中国"首次出现"的讽刺文学的代表作而提到的,并认为其主题是"鞭笞统治阶级的腐败没落"。巴赫金指出: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各阶层读者的喜爱",且由于街头流浪说书人的口头传播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小说还被改编为戏剧,由流浪艺人演出。关于中国戏剧,巴赫金认为"主要的形式是历史戏和征战戏",另外还有"传奇戏与喜剧";戏剧的繁荣是在元代,而"最早的戏"则是《西厢记》。和诗歌的长期繁荣及明清以后小说的兴起相比,元代之后中国的戏剧"较为落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巴赫金的概括,大致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可以说是为俄罗斯人初识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框架。
关于民间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巴赫金予以高度注意。他在大纲中专门列出一节谈论民间文学,认为它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从体裁上看,民间文学作品有小说、短篇故事、戏剧等,还"存在不少幻想小说和神话小说"。从思想倾向上看,民间文学是与儒学经典作品相对立的,反映出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如吴承恩的著名小说《西游记》,写的就是"佛教高僧去印度寻求经书"的故事。关于道教,巴赫金认为它主要反映了早期"村社农民的思想",其核心是"老子的辩证法",后来则"渗进了神秘、幻想、奇异的成分",《聊斋志异》就反映了"道家的幻想特点"。《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些小说,在巴赫金看来,都是"处于经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作品。此外,巴赫金指出,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大都是佚名的,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多为民间口语。巴赫金还特别提到鲁迅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也许是从中国文学进人20世纪以后的发展变化着眼,巴赫金认为,在中国,"民间文学取得了胜利"。这一提法,在中国学者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并不多见,但巴赫金的说法却道出了中国新文学与以往民间文学的更紧密的关联。
如前所述,巴赫金对中国新文学是极为重视的。他看到中国文学在进人20世纪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和改变",勾勒出这一新文学的一系列形式与内容特点。由于旧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妨碍表现新的内容,便合乎逻辑地有了白话文的倡导与使用。人道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导精神,小人物(农夫、车夫、失意的知识分子等)问题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家庭、女性、新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一些作家的作品共同显示出一种"对新人的企盼"。关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中国艺术家协会"等文艺流派和团体的倾向与影响,关于《新青年》、《创造》、《奔流》等刊物的地位,关于"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关于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历史作用,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作家的分化,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巴赫金在他的提纲或札记中都曾提及。如果对比一下巴赫金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作家作品,则更可见出他对于现代文学的重视。他所列举或提及的古代作品,除《诗经》和6部儒学典籍外,仅有《楚辞》(含《离骚》)、《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西厢记》、《九尾龟》等9部,古代诗人和作家仅屈原、李白、杜甫、王维、韩愈、苏东坡、欧阳修、罗贯中、曹雪芹、吴承恩等10人。现代作品中,巴赫金列举了《呐喊》、《野草》、《动摇》、《幻灭》、《我的童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原动力》、《赶车传》、《王贵与李香香》、《红旗曲》10部,现代作家和诗人则举出鲁迅、茅盾、郭沫若、周作人、张天翼、丁玲、赵树理、草明、田间、李季、周扬、萧三等12人。无论从文学史的时间跨度看,还是从文学成就看,这都是不平衡的。这也许显示出巴赫金以及当时苏联文学界的一种普遍的"厚今薄古"的意识。
特别显示出巴赫金见解的独特性的是,他将1942年视为"新中国文学"的起始年份,并提到这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他所列举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所提到的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形式,"民族的形式与人民民主的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内容",等等,其实是我们国内研究者所说的"解放区文学";而他最后所提到的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才是新中国文学开始的标志。巴赫金的这一提法虽然独特,却准确地把握到了新中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血肉联系,富有洞察力地发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新中国文学的直接指导作用,显示出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的一种敏感与目力。
巴赫金还注意到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外来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早在19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刚刚兴起、开始进行"更新文学的尝试"时,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文学的现象,但这时的翻译文学尚未对中国文学产生大的影响。1911年革命之后,西方各种文化与文学思潮涌入中国,"印象主义、颓废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均得到传播"。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崇洋"和不恰当地"效仿西方","颓废派"曾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出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普及",从契诃夫到马雅可夫斯基等俄国作家和诗人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马列经典作家的翻译"则无疑是外来先进思潮直接作用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巴赫金甚至还提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道主义者甘地在中国的影响。作为生活在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谈及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时,特别把"苏联文学的意义"当做一个专门问题提了出来,这既为他本人的身份和视角所决定,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外来文学的接受史的。
《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虽然只是粗略地勾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历史面貌的一份提纲,可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巴赫金的思想和见解的某些独特性。尽管由于语言的阻隔,巴赫金不能通过直接阅读汉语资料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但他对于这一文化与文学的价值、对于认识、研究它的意义却是充分肯定的。作为一位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的学者,巴赫金看到了具有某种神奇色彩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从事一般文化与文学研究、探索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规律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把握。这其实是创立了"对话理论"的巴赫金在观照东西方文化关系、思考世界文化发展问题时所必然形成的见解。他本人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总是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总是将文学放在文化发展规律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总是十分重视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特有价值,这些特点在他对于"汉语与汉语文字"的构成和特色的简要勾勒中,在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不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对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现代文学的诞生伴随着整个文化的现代转换等现象的关注中,在他关于中国民间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的观点中,都清晰地显示出来。巴赫金认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后来是"民间文学取得了胜利";他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1942年作为"新中国文学"的起点--这些见解颇为独特而又自有其道理,使人感到新鲜而又令人叹服。
毋庸讳言,巴赫金也偶有错失之处,例如他不知《诗经》、《书》、《春秋》、《论语》、《大学》等其实都包含在所谓"五经"、"四书"之中,而把这五种典籍与"五经"、"四书"一起当做七部书。这一差错显然出自他所参考的某位俄国汉学家的著述。在考察巴赫金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描述时,人们注意的当然不是这种偶尔的差错,而是这一描述所显示的他的明晰的思路、独特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和高度的概括能力。这一切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巴赫金理论体系与治学方法,而且对于我们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4."写意"与"假定":梅耶荷德对中国戏剧艺术的接受
1866年(我国清朝同治年间)的某一天,俄国《圣彼得堡新闻报》的一位记者有机会在恰克图地方观赏了一场中国戏,不久便在当时的俄国杂志《剧场休息》上发表了一篇剧评,题为《中国戏剧》。这位记者把中国戏剧和俄国戏剧作了一番对比。他认为,中国演员在表演骑马打仗时,拿着棍棒当马骑,还觉得自己是骑在真马上,这说明他们愚昧无知;而在亚历山大剧院表演的战斗场面中,作战的不是瘦弱的演员,而是勇猛的士兵,他们骑的也不是棍棒,而是欢快嘶叫、膘肥体壮的枣红马!透过这位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原则毫无所知的俄国记者的武断而自负的言辞,可以想见那个时代俄罗斯戏剧演出的一般状况,以及普通俄国观众对于中国戏剧艺术的隔膜。
历史让这种状况在《中国戏剧》这篇小文章发表之后至少还延续了30年,直到年轻的戏剧艺术革新家梅耶荷德以不可阻挡的锐气出现于俄罗斯剧坛。
弗·艾·梅耶荷德(1874~1940)是20世纪俄罗斯最著名的戏剧导演和演员之一。他是在他的老师、著名戏剧艺术家、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一丹钦科的有力影响之下开始自己的戏剧艺术活动的,但是他又开辟了一条和他的师长不同的演剧艺术路线,创立了所谓"假定性戏剧"的演剧理论,并在戏剧艺术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世纪前30年间,整个俄罗斯一苏联戏剧的繁荣、革新和进展,都是与梅耶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进人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梅耶荷德的戏剧艺术理论在他的祖国经受了时代浪涛的无情冲刷,艺术家本人也因其"标新立异"而招来一连串厄运,最终导致为自己心目中最神圣的艺术而殉身。然而,时间毕竟是严格而又公正的评判者,在历史的暴风雨过去之后,梅耶荷德的戏剧理论现已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一样,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戏剧艺术史上最珍贵、最重要的一部分遗产。
谈到梅耶荷德及其演剧艺术,人们往往把他和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实验和创新联系起来,这自有其道理。梅耶荷德无疑是俄罗斯现代主义戏剧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可是是否有人会想到,这位戏剧艺术革新者的探索中,伴随着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巨大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梅耶荷德热爱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惊叹于中国戏剧的特殊艺术表现力。他的"假定性"戏剧理论与中国戏曲的"写意"原理之间,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可以说,梅耶荷德的戏剧理论的形成,离不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文化的关注、研究和接纳。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俄罗斯艺术家对于中国文化接受的深度,而且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