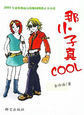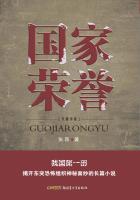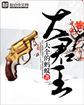梅子涵是十年动乱后开始文学创作的。当时,人们把那段时间称为“新时期”。虽然人们说不清“新时期”的内涵是什么,但从总体上意识到和以前的不同。反应在文学上,人们不需再固守为政治服务等概念,可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将文学当作文学去看待,将美、艺术形式当作艺术本体、艺术目的去追求。和一些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不同,梅子涵没有太多的传统留下来的包袱,所以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倾向。如果说《马老师喜欢的》还主要是一种题材禁区上的突破,《小路》《走在路上》《嘀嗒、嘀嗒,下小雨了》《写封信试试》等则将探索主要放在形式,尤其是叙述方式的变革上。这几篇小说都属于在当时颇为新颖的意识流结构,作者有意识地打乱故事时序,不是按故事时序安排文本时序,而是在故事临近结束的地方开始叙述,将此前的经过选择的片断以人物回忆的方式穿插在人物现在的活动中,用一个较小的时间段封闭起一个较大的时间段,这样就增大了叙述的密度、厚度。但由于这种增加是以回忆的方式呈现的,不仅使经历中的事件变得柔化,也使现在的叙述变得灵动,从而使整个作品变得空灵;这使梅子涵的小说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蓝鸟》用的也是意识流结构,但和《小路》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其一,它用的是第一人称,让少年主人公周明明叙述自己从那个封闭、压抑的小山村出来去寻找县里的重点中学植树王的心绪,这种心绪成了读者主要的观照对象。其二,人物此时正处在一种冲动的不甚理智的状态中。由于受了老师窝囊的升学动员的反向刺激,他决心去找植树王,精神处在一种骚动的、亢奋的状态。即是说,此时的人物多少被潜意识控制着。作品以此时的人物意识为主要表现对象,不仅使这一人物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潜意识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西方意识流文学的本意。其三,第一人称,人物充当叙述者,而《蓝鸟》中的叙述者又有明显地在时间、心绪上离人物很近的特点,读者感到周明明是在边走向植树王的过程中边向我们叙述的,这使他的叙述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他此时此刻具有潜意识特征的心绪的制约。《小路》等也写回忆,也将人物此时此刻的心理作为作品的结构因素,但其心理基本上是意识层的,是偏向理性的,所以呈现在此时人物心理中的回忆、回忆中的事件与现在人物行为间的穿插总体上是清晰的、有条理的。而《蓝鸟》是处在亢奋、不甚理智状态的人物叙述自己亢奋的、不甚理智的心理,所以显得飘忽、闪烁,甚至有些不合逻辑。这样,作品内容上的特点便传递、体现到作品的形式上,形式本身便成为内容了。作品对人物恍惚状态中的感觉的把握也很准确。
以人物充当叙述者(即第一人称),是梅子涵小说用得最多的一种叙述方式。除《蓝鸟》外,还有《打枪的事》《我们没有表》《老丹行动》《黑色的秋天》《双人茶座》《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林冬的故事》《女儿的故事》《我的故事讲给你听》《青蛙的声音和癞蛤蟆的声音》等。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兼叙述者,不管是作为成人的“梅子涵”还是其他少年、儿童,多是可靠的叙述者。并不是说叙述者叙述的每一件事情都绝对正确,没有错误,而是说人物兼叙述者的价值取向接近作家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在作品中的声音。这种叙述距离带来双重的效果。一是人物的叙述较为坦诚,努力和读者建立一种“我—你”的对话关系。如《女儿的故事》,叙述者虽是一位父亲,一个成人,但将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无奈,自己的矛盾都呈现在小读者面前,语调也显得诚恳;《咖啡馆纪事》是少女毛兰自己的叙述,浑身散发着都市少年的先锋气息,以此使作品形成一种极有魅力的氛围。二是叙述者作为作品中的人物,他们也有缺点,也有无奈,也会犯错误,这就使叙述者常常被逼到一种挺矛盾、挺狼狈的地位。这时,隐含作者就和人物兼叙述者悄悄地拉开了距离,站在一定距离外带着一点嘲弄、揶揄看人物兼叙述者,使叙述者的叙述带上某种戏剧效果。如《青蛙的声音和癞蛤蟆的声音》,叙述者在故事中一再陷入困境,又一再用“我没有脑子急转弯”来开脱,左支右绌,颇为狼狈。但这种嘲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作者信任、肯定的人物。在这类叙述中,作者极有信心地控制着叙事距离,舒展自如,张弛有度。
更具先锋特色的是作者的第二人称小说。如作者所说,这在整个“文革”后的文学中都是一种较新的叙述方式(作者说主要是年轻作家喜欢运用第二人称,这倒未必。中国作家中运用第二人称最早也最成功者,应是刘心武)。在《儿童小说叙事式论》中,作者说这种叙述方式有一种“尾随”和“高空俯视”的效果,是颇为精到的体会和论述。但何以产生这种效果,作者没有深论。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可以引申。其一,第二人称小说中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你”,这个“你”是谁?在小说中,“你”都是听故事的人,是叙述接受着,但在一般小说中,这个“你”都是不具象的。第二人称小说将其具象化,但其实仍不在故事中出现。出现在故事中的是作为人物的“你”。就像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原是小说中的人物后来充当叙述者成为“我”一样,第二人称小说是人物兼叙述接受者,是给“你”讲“你”的故事,就像教练在一场比赛结束后给参加比赛的队员放录像、讲录像一样。但如果不强调现在的这个点,只让人们面对故事,就给人一种现场直播的效果。其二,从叙述者和人物所处的位置关系说,在第三人称小说中,人物处在“他”“他们”的位置上,叙述者和人物不处在同一世界,可以任意地出入故事,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将视点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可以从甲的视点看乙,也可以用乙的视点看甲,也可以采取一个超越的视点看故事中的所有人物,所以一般不会产生尾随的效果。第一人称小说是人物兼叙述者,用人物聚焦,属于定点透视。但叙述者和人物同一,人物的视点视角也就是叙述者的视点视角,自然也不会有尾随的效果。只有第二人称小说,给“你”讲“你的”故事,“你”是故事的主要叙述对象同时又是故事的聚焦者,采取的是定点透视,但叙述者又不是“你”,叙述者的镜头安放在“你”身后的某个地方,跟着“你”前进,尾随、高空俯视的效果便产生了。梅子涵将这种叙述方式运用得很成功。比如《你和自己干杯》,尾随“你”劳改回来初到上海的一段经历:如何出车站,如何决定坐出租车回家,如何在车上和司机聊天,如何看到邻居异样的目光,如何听到奶奶无声的叹息,如何去买酒准备和自己干杯,整个画面里几乎只有“你”一个人。叙述者在叙述作为人物的“你”的故事,也在向并未露面的作为接收者的“你”指点迷津般的作着解说:“你”所以要奢侈得坐出租车回家,所以在出租车上听到司机说他“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后心里一亮,所以买酒和自己干杯,其实都是为了使自己显得不窝囊。而这原来在“你”那儿都是不很清楚的。这就体现出第二人称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某种解说性。这也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现场直播。
1990年前后,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曾有一场有关童话和幻想小说的讨论。有人在童话和幻想小说间划出各种各样的界限,有人为童话和幻想小说给出各种各样的定义,虽大多语焉不详,但反映着一种探索的热情。后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幻想文学”丛书,创造出许多颇有新意的叙述方法和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梅子涵也进行过这方面的试验,如《星期六童话》。《星期六童话》并不是童话,“这是一篇小说,但写得像童话一样”。说它不是童话,因为它“没有动物,没有飞翔,精灵和巫女也无影无踪”;说它像童话,因为它有变化,有变形。爸爸在星期六变成了“大头”,妈妈在星期六变成了“小妹”,儿时相片上的小率率从相片上走了下来,和现在已长大的率率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熟悉《聊斋志异》的中国读者不难发现,类似的创造艺术形象的方法在蒲松龄笔下大都出现过。作者继承了《聊斋志异》的创作精神,尤其是与童话,与儿童的带有互渗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童话小说化,小说童话化,在儿童与成人,幼年的孩子和长大的孩子的转变中进行一种换位思考,激发人们对现实的教育儿童的方式进行反思。复兴古老的幻想小说的叙事艺术,接通儿童小说的志怪小说源头,使现代儿童小说找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文革”后各种各样的先锋小说中,一种最为极端的小说形式就是“反小说”。反小说就是在小说虚构的故事系统外另设一个系统,这一系统构成了对小说虚构的叙事系统的解构。梅子涵在自己的小说中也进行过这样的实验。只不过这两个系统间的距离及后一系统对前一系统的解构都不十分明显。如《林冬的故事》,虚构故事是“我”与中学生林冬之间的交往,虽然写得“随随便便”,但他们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但作者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又常常站出来,以“作者”的身份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说,并对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探讨,于是在作品的虚构之外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比如作品一开头,叙述者还没有开始叙述故事,就以“作者”的身份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你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写法。读得耐心点。小说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一直采取各种各样的写法。
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也多次打断叙述者的叙述,直接站出来和读者说话。如在叙述自己初中毕业后去乡下当农民,“文革”后才重读大学,因为没有读上一个好大学因此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考上第一流的大学时,就插入了这么一段:
你们不是都去当工人农民了吗?后来又怎么会考上大学呢?关于这一点,你们最好也去问一下。我写我考试,小便要小出来这一段,是为了举例说明什么叫“情结”,对比,我觉得似乎要说明一下,我怕挑剔的批评家会说成有点离题。
在故事临近结束的时候,又引了英国作家弗斯特的一段话:
有些人除故事外一概不要……故事……它只有一个优点:使读者想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反过来说,它也只能有一个缺点:无法使读者想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第一个系统讲“我”(叙述者)和人物的故事,第二个系统讲“我”(作者)对小说写法的思考。前一故事将读者尽量带入虚构的情景中去,后一系统则一再将读者从故事中拉出来,告诉读者那是小说,是故事,是虚构,并引导读者对作者这种虚构的讲故事的策略进行了解,这就要读者拉开与故事的距离,对作者的叙述本身进行观照和反思。虽然说儿童小说大多以“入”、以将读者吸引到故事中为主,但作为一种实验,作者也提供一种新的儿童小说的叙述方式,对探讨儿童小说的可能性也有益处。
三
梅子涵实验过多种叙述故事的方式,更实验过多种讲故事的语言。比较而言,他在语言方面形成的特点似乎更明显一些。读梅子涵的小说,我们很容易感到一种只属于梅子涵个人的语体方面的东西。
梅子涵的语言前后也有不小的变化。如他刚开始写作,主要只写作面向成人的小说的时期,语言是颇为清晰的。在《小路》《嘀嗒、嘀嗒,下小雨了》《雨飘着,头上脸上……》《写封信试试》等作品中,甚至是委婉、抒情的:“在下雪,下雪比下雨好看,它使人想起某一个童话,里面的圣诞老人,银的树,银的屋顶……”“太静了。大概只有这种老式华贵的花园洋房中才会如此安静的。她们住的那幢楼里几乎永远响声不断,一层到五层的楼梯,通宵都有人在走。上夜班地去了,下中班地回来了,有人下楼梯排队买菜去了。家家都用小火表,走道里的灯头搞得一只也不剩。谁也不愿意在公用面积装盏灯去照亮别人。走道里永远是黑的。谁喜欢黑暗呢,有的大概怕黑暗里走出个鬼来,就故意把楼梯踩得像击鼓一样响……”这种非常书面化的语言和作者当时描写的偏重内心细腻情感的内容相适应,也是青年作家开始写作时一般都会采取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梅子涵这儿很延续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以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如《马老师喜欢的》《课堂》《走在路上》《感谢太阳》,一直到《你的高地》《打枪的事》等,都保持着这种清晰、明净的语言形式。就是在《女儿的故事》《很好玩的故事》等作品中,它们也在深层成为作者语言的基础。
但在将“叙述面向”主要转向少年儿童后,作者的语体还是渐渐地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或许是面对儿童读者,作者自觉不自觉有一种叙事上的优越感觉;或许是经过一段时间创作,作者对自己的叙述变成更有信心,至《双人茶座》《咖啡馆纪事》《女儿的故事》等,作者渐渐锤炼出一种“写”和“说”相融合的语言形式。一方面,作者的儿童小说主要是“说”的。《女儿的故事》《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固然是说的,《双人茶座》《老丹行动》《打枪的事》《咖啡馆纪事》等也是说的。因为在这些作品中,读者能很分明地感觉到一个正在讲述的叙述者的存在。读者主要不是面对故事,不是面对人物、场景,而是面对这个讲述者,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事件等都是这个叙述者带给他的,虽然这个叙述者原来可能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但另一方面,这和传统的讲故事的“讲”又有很大的不同。如作者在《儿童小说叙事式论》中所说的,传统故事的讲法是一种“长者语调”,他讲述的是读者不知道的东西,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叙述者,而且他讲的内容是读者毋庸置辩的。而梅子涵小说中的讲述者往往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他们向读者讲述现实中的事情,且这些事情没有很强的故事性。讲自己的遭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绪,并不是读者不能接触的世界,也不是读者不能置疑的事情。作品吸引人不仅在它们讲的内容也在它们讲的方式、讲的语调,是一种介于以描绘为主的写的小说和以讲述为主的故事之间的一种语体。
先看两段具体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