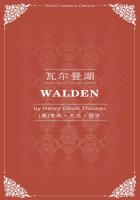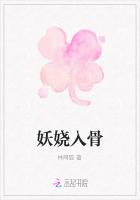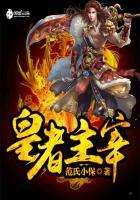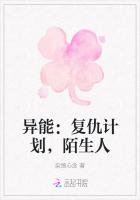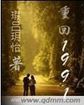生活中有清溪潺潺,也有浊流滚滚,但是我们都在乘流而下。我们走过早晨的上游,渡过中午的中游,来到黄昏的下游,回首前尘,曾经发生的一切显得那样不真实似的,如同一个远逝的梦。
菊
她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中等个头,身材略显瘦削,但亭亭玉立。头发黑而密,扎两只短辫,调皮得晃在脑后。眼睛很大很黑,而且闪烁有光。她听人说话都是平视,有时眨两下眼睛,表示“哦,是这样!”或“是吗,是这样吗?!”她眉宇间有一股英气,甚至流露出一点野性,但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她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文静,很秀雅的。
她在班上学习属于中等水平,也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女孩。那时农村的寄宿学校,一般每两周放假一次。她好像也不常回家。星期天下午,班上的同学都陆续从家里回来了,看见她宿舍门口的晾衣绳上,总是花花绿绿挂满了衣衫,她正忙着往屋里收呢。或者常常看见,她带着罗老师三岁的女儿燕燕,在篮球场上扔篮球玩。她好像显得有些孤傲,打饭也是独来独往。不像别的女生,三五成群,叽叽嘎嘎,结伴而行。
那时候,国家办教育,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学工学农学军。一有劳动任务下来,我们就扛上铁锹或者拿上镰刀,到附近的生产队,帮助收割或者平田整地。大家排好队,显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出发了。队伍在行进中,照例要唱歌。所有歌曲都由她起头。“日落西山红霞飞,一二!……”“地道战嗨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一二!……”她清脆甜美的歌声回荡在原野,回荡在麦田。正在田间挥汗如雨的农人们也听到了,停下镰刀,抹一把汗,在心里赞叹说,这女娃,这条嗓子还了得。
她有唱歌的天赋。学校里每学期都要进行文艺汇演,每个班都要出三到五个文艺节目,并且评奖。这关系到集体的荣誉,也关系到班主任的工作能力。我们班常常在汇演中夺魁,这与菊有直接关系。她擅长秦腔,尤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她往台上一站,台下立刻鸦雀无声。化了装,穿了戏装的她,越发显得楚楚动人,一招一式竟有些专业演员的风范。“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八年前,风雪夜,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我爹娘……”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她也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么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轻柔的旋律飘荡在公社的礼堂,也飘荡在同学们枯寂的心田。如果哪场晚会没有她的演出,大家便意兴索然,观众也就稀稀拉拉。许多年以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回忆起母校,母校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或许就是菊的歌声,这歌声让这所学校美好起来。
她是学校的校花。对于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有人仰慕,有人嫉妒。仰慕者,上课的时候弄一块小镜子,先是把小镜子贴放在书本上,再一点点移动,直到菊的形象出现在镜子里,枯燥的课堂就变得生动起来;嫉妒者,看见她在台上唱歌,台下欢声雷动,就在暗处拉开弹弓,将一块石头弹出去,重重地打在她的胸脯,全场顿时哗然,听歌的氛围也随之消散。
秋天的一天,我们班全体出动,到生产队割糜子。累了,大家都坐在田埂上喝水、吃干粮,有的在磨镰刀,有的在谈笑。罗老师说:“大家静静吧,让菊给我们唱支歌,大家轻松轻松。”菊正坐在田埂上,低着头抚弄她的两只短辫。听到老师的召唤,忙站了起来。她说就唱支《浏阳河》吧!“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歌声曼妙动人,与秋天田野里成熟粮食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撩拨着我们青春的心,让人感到熨帖、感到舒展、感到活着真好。这时,突然有人惊叫了一声,菊刚才坐过的土丘上有淡红的血迹。歌唱完了,她也许是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屁股,发现湿漉漉的,手指也沾上了鲜红的血迹。她立刻变得难堪,脸膛上笼罩了火红的霞晕,有些烫人。就像一尊雕塑,她愣在了那里。有人睁圆眼睛在注视,有人打起了尖利的口哨。还是罗老师反应快,他说:“菊同学累了,就由巧陪伴着,回去休息吧!”尴尬局面被打破了。她眼里流淌着羞愧和不安,满脸是悲伤的泪水,几乎是被巧搀扶着走出了那片田野。红头巾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像一团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菊一周没有来上课。
这件事之后,班里就有了关于她的一些闲言碎语。说她星期天不回家,常有一个操环县口音的男人来找她,在她宿舍里过夜;还说,他同公社放电影的小刘好上了,有人亲眼看见她和小刘在操作间亲嘴。一次青春的流血竟招致了铺天盖地的议论,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她依然独往独来,上课、写作业、买饭,有时唱歌给我们听。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似乎横着一堵高墙,无法逾越,也不能逾越。虽然天天见面但很少来往,很少交流。高中两年,我和她只有过一次正面接触。十一国庆节的时候,罗老师安排我们出一期黑板报。我写了一首颂国庆的小诗准备发表在板报上。星期六下午,公社的小礼堂演电影《南征北战》,这部电影在我们这里至少放映了二十遍。我没有去看,站在凳子上抄板报。
菊也没有去看电影,她来教室里写作业。她看见我在黑板前忙乎,就凑了过来。她看了我写的诗,称赞了两句。她说:“你的作文写得好,有啥秘诀,给我们传授传授!”我说:“哪里有什么秘诀,只是多读多写呗!”“是吗?是这样吗?你有什么好书借我看看。”我说:“宿舍里有一本《战斗的青春》,一本《林海雪原》,就借给你吧!”“是吗?那太好了!”她用目光平视着我,脸上浮现着甜甜的笑容。写完黑板报,我两只手上沾满了墨汁和粉笔灰。她笑着说:“我去给你打点水。”说着拿了一只洗脸盆,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端了半盆水进来,放在我眼前的凳子上。她自己先把两只手放到了水盆里,嘴里念叨着:“有点冰,凑合着洗吧!”隔着清水,我看见她的一双手十分美丽,手指红润而修长。她撩拨了一下清水,就站在我面前,刘海儿弯弄着娇柔,目光里满含着温情。盆水溅出星星碎玉,也荡起细细波纹。我嗅到了她身上的香味,不禁有些脸红心跳。她却笑了,笑得那个平淡的午后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同学林,长我三岁。这家伙成熟得早。在我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已为爱情而心事重重了。他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红楼梦》。有一天晚上,我扯开了他的被子,想看看是什么情节使他如此迷醉。他指给我看贾琏和多姑娘发生性关系那一段:“进门一见其态,早已魄飞魂散,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锦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贾琏此时恨不得连身子化在她身上……”林还“厚颜无耻”地悄声告诉我,昨夜他遗了精。
林早已暗恋着菊了,只是无缘一诉衷肠。
终于有了一个接近她的契机。
那时候,班里每个同学有一项硬性的劳动任务,就是每人每学期积肥十背篓。女生还是受到了优待,她们只需积够八背篓就行了。学校在西山洼有点试验田,积了肥种小麦、种土豆、种蔬菜,好补助老师学生食堂的伙食。
下午放学,就有三三两两的同学,背上芨芨草编织的小背篓,手里拿把铁制的粪叉,转悠在山峁上、背洼里。但这事很困难。草原上很难找到成堆的牛粪、马粪、驴粪,一般都是星星点点的,有时转悠了整个下午,直至夜幕降临,仍是收效甚微。班上的劳动委员还把这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定期公布在黑板上,每个人都感受着压力。
林似乎对这件事从不挂在心上,照旧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他的《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诗情画意、儿女情长,远比背着背篓在大山里寻找牲畜们的粪便要有趣得多、美妙得多。但有天晚上,他诡秘地笑着,关上宿舍门对我说:“快,借辆手推车,跟我来!”
原来公社里有家生猪收购站,农民每年都要向收购站交商品猪。收购的季节里,毛驴车拉来了养肥的猪,排着长长的队,等待收购。天长日久,院子里就沉积了许多驴们猪们的粪便。但院子的铁门锁着,看门的老头阴沉着脸,他会允许我们拉走吗?
林从怀里掏出一包早已准备好的“海河”牌香烟,一口一个“大爷”招呼着那老头,他终于允许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拉走几车。
第二天,我陪林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挡住了菊,告诉她,她的任务已经完成。她听了先是有点惊异,后来就笑得前仰后合,不断重复着:“是吗?有这样的好事吗?太感谢你们了。”她还送给我们两袋香喷喷的葵花子,作为回报。
但据我观察,林和菊的关系,直到高中毕业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她依然高傲地仰着头,每天重复着她的“三点一线”,对异性投来的含义丰富的目光,似乎显得不屑一顾。
1979年,我考上了宁夏大学中文系,林也于同年参军去了甘肃张掖。菊参加高考落榜,第二年复读一年,仍然榜上无名。她怀着对生活的无奈和怅惘回到了家乡的小村。几年后,嫁给了一位长她九岁的中学老师。不久随夫来到了甘肃环县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后改作美容院,做起了老板。虽然远隔时空,但她的一些情况还是断断续续地得到了证实。说是她傍了大款,那大款是一位很有钱的石油鬼子。那石油鬼子出钱装修了她的美容院,替她购置了先进的器械、设备,把她的雇员送到兰州进行了专业培训。菊生意红火,赚了大钱,和丈夫离了婚又复了婚。还有一些关于她的故事,听起来有点惊悚玄乎,就不说了吧!作家孙犁说:“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身体一步步向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这可能是对她的生活的一种诠释。二十多年前那个扎着短辫、歌声甜美的小姑娘哪里去了?茫茫人还挂着淡淡的笑容。我听了,一夜无眠,心里充满了感叹与唏嘘。
1997年,我当时还在县委宣传部当通讯干事。早春的一天,我陪同《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去长庆油田采访。下午的时候,汽车路过环县县城。我想起了菊,我想去看看这位老同学。在县城里稍一打听,就找到了那家著名的“思美”美容院。这家装修豪华、气派非凡的美容院坐落在县城的东南角,它与周围低矮寒碜的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显得有些扎眼,有些鹤立鸡群。一位漂亮的红衣小姐,听说我在找她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说:“不巧得很,老板今天早上去银川了。”我心怅怅。在店里转一转,看到菊的一张巨幅彩照。她胖了,很丰满,身着看上去很高档的时装,浑身珠光宝气。眉宇间了无少女时的清纯,更多地透出甜媚和俗气。烫卷了的头发,像一只别致的鸟窝,她含情脉脉地平视着来人。“还是不见的好!”我在心里告诉自己,随即辞别了红衣小姐,走出了美容院。那时,暮霭已经笼罩了这个大山丛中的小县城。身后的美容院,霓虹已然开始闪烁,节奏激烈、震耳欲聋的音乐敲击着耳鼓。街上行人稀少,在早春的寒风中瑟缩着,我感到一阵阵孤独和荒凉……
斜阳外,寒鸦数点,“油路”绕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