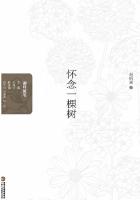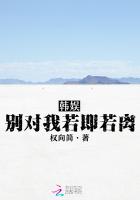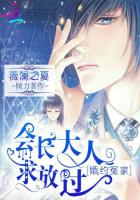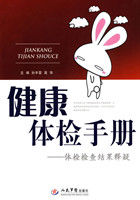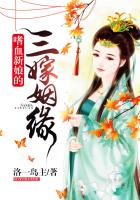大约是半年前,在外和几位文友聚会时,他们问我:“盐池有个施原钰你认识吗?”我说:“听人说过,但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几位文友谈起他的时候,都显得很激动,纷纷给我推荐发表在1989年《朔方》第八期的《走向黑夜》,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回到盐池,我就找到了刊登《走向黑夜》的那一期《朔方》,一个晚上诵读再三,我像是一块久旱的土地,突然在一夜之间饱受了一场甘霖,每个毛孔都感到熨帖、舒坦。我承认我从他的小说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同时,我也认定,这篇小说充分显示了作者在文学上的不凡功底。
后来,我常听一些文友谈起他。谈他如何勤奋,如何对文学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如何在吃饭睡觉时苦苦构思,如何一蹲在厕所里就忘记了早该离开那个空气不怎么新鲜的地方,等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了他。第一印象:他的风度远没有他写的小说潇洒,长相也不会让一个妙龄女郎一见倾心并发誓嫁给他。他的言谈举止倒是让我联想到“像秋天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那样朴实、可爱”之类的句子。从他身上你可以清晰地感到质朴、真率、憨厚、勤谨,山里人的铮铮如铁,作家的丰富、敏感等独特的个性气质。
他向我诉说着当初是怎样投出第一篇小说的,怎样从焦躁和失望中开始第二篇的写作,写每一篇小说时的心境、当时的情状,《朔方》编辑的热情扶植、严格要求……他说得很动情。我们大约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谈了很多。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较全面地了解了他的生活、创作经历。他说:“1958年3月,我出生于盐池县南部山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当时,全国大炼钢铁,家里没粮吃。直到1979年底,我从宁夏交通学校毕业,那落地时勒紧的裤带,还未松开过。工作后,由于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发生了巨变,常常回顾过去,胸中总是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酸楚。于是产生了一种欲望——向人们介绍属于我独有的那块土地和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他作出了这个沉重的选择后,经历了很长一段“在摸索中孤独地爬行”,他终于完成了从一个汽车司机向作家的过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
我陆续读了他已发表的一些作品,诸如《我的父亲、我的家》、《冠心病》、《分水岭》、《今夜,月亮好圆》等,掩卷之后,余味咂舌。
今年《朔方》第四期发表了他的小说专辑,这就确切地表明,他已带着他独具的光彩登上了宁夏文坛,以至走向全国。
对于他的作品,自有评论家会作出精辟深刻的评述。但作为他的读者,我的感觉是:人们尽可以用“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深情的叙述语言”、“深刻的真实性与社会容量”等语言去概括。但我要说的或许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笔下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辛酸和苦难的世界,他把自己的人物置于西部传统文化意识和现代精神撞击、裂变的大背景下,用一种饱含感情的细腻的笔触,写他们的聪明、愚昧、狭隘、狡黠,写他们的迷惘、躁动、挣扎……可贵的是,他不仅仅要再现这种生活,而且期望更新和推进它,有心的读者会从那字里行间听到作者这炽热而焦灼的心音。
对于原钰的创作,我有一种暗暗的期待,凭他丰富的生活积累、深湛的文学素养以及对文学执著的追求,是完全可以给西部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增添几部力作,给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几个西部人的典型形象的。
但他在今后的创作中,会不会被名利之类的一些什么东西所困扰?
他当然还需要在生活中进一步修炼、强大。鲁迅的话:“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是值得玩味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在更大的人群中取得某种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与优势——以你的博大精深,你写的小说才可能达乎上乘。
好在他能够耐住寂寞,头脑也是极其冷静的。我想,每一个向前冲刺的作者,除了必备的优势而外,并不排除冷静的头脑。冷静不同于冷漠。在这种清醒与冷静中,实际上正蓄蕴着向更高程度攀越的潜力。
原钰,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