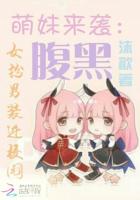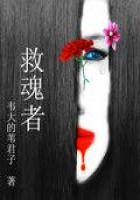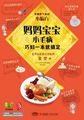台北荣总精神医学部社会工作师
江怡雯
当愈来愈多的忧郁症患者进入医疗系统接受完整的治疗,似乎就代表着“忧郁症”不再是有损名誉的疾病,这对忧郁症患者及家人而言,无疑是一大解放,解放许多患者与家人于无形的文化禁锢中。
转介来社会工作处的病患及家人,都是在医师评估下认为有家庭问题需处理的个案,忧郁症患者本身,除了经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之外,还得为因疾病带给他人的折腾而感到内疚。家人也因为家中有生病的人,而时时处在备战状态,患者的一言一行都成了全家注视的焦点,担心做了什么让患者不高兴而加重病情,害怕让患者一人在家会想不开,或是将疾病全怪到患者个性不好,指责是某一个人的冷漠与过度保护而造成的结果。这样往往让家庭成员陷入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里,每个成员皆无法正常地过生活,冲突声淹没了正向沟通、合作的可能性,以致家庭成员精疲力竭,最后只有放弃。
社会工作师面对精疲力竭的家人,总不免担心照顾患者的压力会让家人也成了另一位忧郁症患者。时常有家人对我说:
“为了照顾他,我每天都睡不好,吃也没胃口,动不动就紧张兮兮,看到他一点进步也没有,我都快忧郁了……”其实,有诸多实例也一再提醒家人,在照顾患者的同时,也该学习照顾自己,或许你我都容易忽略,其实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同时影响患者而不自知。
第一次见到病人是在急性病房住院的时候,三十五岁已婚女性,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没有特别整理,但也还算整洁、清爽,带着圆形细框眼镜,眼神有点朦胧,看人总是眯缝着眼、无目的地在病房的长廊来回走着。没见着她与其他的病友互动,周遭发生了什么事,对她似乎一点也不重要。
她的诊断是忧郁症,就病人的说法,她在三年多前发病,发病的原因是工作地方的老板觉得她不胜任,用尽各种理由开除她。她在几次的坚持、抗议之后,终于被其他同事联合迫害而被迫辞职。至此之后,陆续换了几个工作,但都被类似情节所逼退,最后一次被逼迫的当时,就发病了。她形容的崩溃,就是口不择言骂了公司里的几个同事,包含上司在内。砸掉看得到、拿得到的东西,整个人像是被附了身似的疯狂,她说,其实她很后悔,她并不想这样做的。
当然,她还是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可以偶尔听她诉诉苦,发发牢骚,但总是觉得这世上没人了解她,她开始变得足不出户,成天躲在房间里,饭也不吃,想到以前受同事欺负的事,忍不住哭泣了起来,哭累了,躺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睡也睡不着。她是个要求完美的人,曾经几度她都无法接受这个失去灵魂的躯体,而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亲近的家人劝的劝、骂的骂。几次惊恐地送病人至医院急诊室,焦急、无助、痛苦的情绪写在脸上不言而喻。
父母七十多岁了,每天忙于自助餐的生意,生意不算太好,但赚来的收入勉强可以糊口,多年来也存了一点钱,买了基隆县的一间中古屋,“就也够了!”母亲说道,“可能是我从她小时候就没时间好好照顾她,家里孩子多,生意不能不做,这孩子从以前就内向,话不多,成绩普通,也没带过同学来家里,她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年纪都大了,其他兄弟姊妹各自成家,谁会照顾她!她四肢健全,也不去找个工作,成天想东想西。”
家人担心之余仍不免责怪病人,试着了解之余也不免质疑,想要全力支持又怕病人无法独立。母亲说,她结婚之后就应该会好了,女人嘛!结婚就没事了。
病人这三年来,陆续住了几次医院,不稳定的情绪大同小异,只是这一次,多了夫妻相处与婆媳不和的问题。她,结婚了……家人能对忧郁症有正确的观念是重要的,唯有了解疾病对一个人的影响,才能理性地面对及给予支持,除了治疗之外,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家人持续的谅解与关怀!
雅琪是一位二十二岁未婚女性,此次进入精神科病房治疗的主要问题是有强烈自杀念头,并用美工刀割手腕,也尝试跳楼,但被邻居发现后请救护车送来急诊。入院后,病人情绪仍起伏不定,四处搜寻病房内可以用来自杀的工具,不时会以头撞墙,或企图咬舌自尽,需医护人员密切的观察,以防止病人自伤,一直陪伴在旁的妈妈眼神显得相当的焦急、沮丧,疲惫的身躯,道尽了这一路来的风风雨雨。
“这个孩子,从小就被她爸爸抛弃,她五岁的时候,她爸爸就跟外面的女人跑了,丢下我们母女两人,外面的女人已经得到我先生了,她还不放过我们,叫黑道的人三天两头就来骚扰我们,要我们搬离这个地方,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她很恨她爸爸,恨他为何如此狠心地对待我们母女,甚至天真地想要我们一家人破镜重圆,一家和乐。我常常不自主地哭泣,什么事都做不好,工作也因要照顾她而常常请假。上个礼拜被老板解雇,现在有一餐、没一餐,她住院的钱我还在担心付不出来……没有人肯帮我……”
经过三周的药物治疗,病人已不像住院初期的狂乱,极度想寻死,只是在病房中,漫无目的走动着,与其他病友的互动很少,多由妈妈陪在身旁,病人常会与妈妈发生口角,口角争执的内容多半是妈妈要求病人振作,赶快好起来、去找工作等。病人在疾病的影响之下,能力也较以往退步,找个稳定的工作,是病人一直想要做,但却屡屡挫败的一件事。病人在几次工作不顺后,开始逃避会有压力的工作,只要上司一多要求,病人就不干了,“不是我做不来,而是我不想做。”这是每次病人失去工作的说词。妈妈会替病人解释;她高中的第一志愿是念商科,记账一定难不了她,只是她公司的同事都嫉妒她太有能力,而被排挤……她下次一定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妈妈眼中的期待,病人都清楚地知道也努力试着达成,但在一次次失败后,病人害怕与妈妈有眼神的接触,对于妈妈的要求,也以自杀的方式响应,“我死一死,我妈妈就不会逼我了……”
这样一对关系紧密、相依为命的母女,有着共同被抛弃的经验,也有着相同的梦想,她们的世界中只有彼此,都有着照顾对方的使命,妈妈因为病人疾病的牵绊而无法过自己的生活,没有社交、娱乐,整天想的也都是该如何帮助病人重新站起来,仿佛只要病人好起来,她就会跟着快乐,却忘了先照顾好自己。失婚的痛苦经验让她一蹶不振,生活中充斥着对前夫的怨怼,离婚至今十多年,她从未为自己买过一件好看的衣服,吃一顿好吃的,更遑论让自己去外面走走,与朋友散心、诉诉苦,除了病人,她一无所有。病人自童年时期对父亲就又爱又恨,渴望有父爱的她,一直至今都不放弃让一家人团圆的梦想,“我只有住院,爸爸才会来看我,爸爸和妈妈如果可以因为我的住院而复合,那我吃再多药也甘愿。”只是一再让她希望破灭的爸爸,选择离她越来越远,这又应验了妈妈每天挂在嘴巴的“负心汉”的诅咒,她除了死亡,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罚爸爸所带给她的痛苦。
破碎的婚姻令人遗憾,先生、父亲的缺席,留给这对母女生命中巨大的缺口,缺口中充斥着变幻莫测的痛苦,但我们仍期盼这样的影响不是永久的。即使父母的一方不再与孩子接触,孩子仍可以清楚地了解父母无法继续生活的难处,不再责怪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可以拯救父母的婚姻。让孩子有机会做自己,去交朋友、谈恋爱,做她这年纪应该做的事,而非守在妈妈的身边,跟着一起怨天尤人。
我要妈妈减少来医院陪伴病人的时间,妈妈初期显得犹豫,担心病人会趁她不在时伤害自己。经过几次的尝试之后,妈妈可以放心每天来陪病人两小时,晚上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休假时去找朋友聊聊天、看场电影,不用担心为了照顾病人而遭解雇,经济收入可以渐趋稳定……慢慢适应找回自我的生活,她开始思考她要不要找一个伴,在未来的日子和她一起携手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