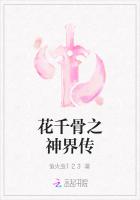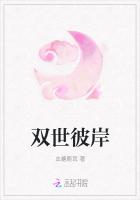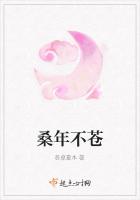从世界文化史上看,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在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萧条之后,往往可以由衰而盛。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的滞缓和萧条中,也潜伏着未来的井喷式发展的可能。有一些学者在暗暗地积蓄着学术的能量,在适宜的时代和环境中,会做出一鸣惊人的奉献。沉潜是时代压抑的结果,但从正面来看,压抑使他们寂寞,也使他们沉下身来,潜下心去,如此,沉潜就成为一种历练,一种蓄势待发。钱钟书、季羡林、杨周翰诸先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出的一系列成果,是沉潜后的必然的喷发,对中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繁荣,给予了莫大的刺激和推动。
((第二节))沉潜期的主要收获
一、季羡林等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
在中印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如果说1920—30年代的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的研究属于首开风气的第一代的话,那么,194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的季羡林的研究则承前启后,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季羡林曾在德国专攻梵语、吐火罗语等印度、中亚古代语言及印度历史文化,并获得博士学位,是20世纪前半期我国极少数受到系统、正规教育的印度研究专家之一。
1946年,季羡林回国并在北京大学任教。此后,他在中印文学研究方面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语言与童话》(1947年)、《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1947年)、《“猫名”寓言的演变》(1948年)、《列子与佛典》(1948年)等,都从实证的角度大体梳理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950—70年代,季羡林又陆续发表或写作了《中印文化交流》(1954年)、《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55年)、《印度文学在中国》(1958年)、《泰戈尔与中国》(1961年)、《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1959年)等论文,还出版了包含十篇论文的题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的论文集。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季羡林在1950—70年代有关论文,都属于中印文学关系的实证的传播研究,并初步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众所周知,中印古代文学文化交流自宋代后基本停止,后来的近千年时间两国基本上处于疏离状态。加上印度的梵语在12世纪后消亡,作为中印交流媒介的包括吐火罗文在内的中亚古代文字,也早已湮灭不传,因而造成了时间上的阻隔和文字上的障碍,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使得这方面的研究颇具挑战性,甚至被视为“绝学”。
同时,由于这一研究是远离现实的纯学术的研究,因而属于冷僻的学科无疑。季羡林献身于这一学术领域,与他对其价值与意义的充分认识密切相关。他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来观照中印两国文学交流史,把两国的文学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他在《中印文化史论丛·序》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国和印度都是文化极古老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三千多公里的边界把两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中印两国有着几千年的和平的文化交流,而没有发生战争,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研究两国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巩固和发展两国的友谊,会有重要作用。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使得他能够在中印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倾尽全力。
在具体的研究中,季羡林基本沿袭了胡适、陈寅恪的思路,也受到德国的印度研究的影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强调来自印度的佛经文学,即佛典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而德国学术界则一直普遍认为印度是全世界寓言故事的老家。季羡林先生有关的文章都侧重于印度文化对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中的题材、主题、文体、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现象,首先大胆地“假设”是受了印度的影响,然后加以细致的求证,在这方面,他在此时期的代表性的文章是《印度文学在中国》。
在该文中,他将1940年代的有关文章的观点和材料做了进一步提炼和归纳,又补充了新的材料,以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为线索,以重要的个案史料为例证,从先秦时代的屈原《天问》,一直写到近现代文学,初步呈现了中印文学在几千年中的因缘关系。他首先讲到《天问》中的“顾菟”,认为月亮中有兔子的传说来自印度,从《梨俱吠陀》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中有兔子。《战国策》中狐假虎威的故事,《三国志·魏志》中曹冲称象的故事等,也来自印度。季羡林不仅指出了印度故事在中国的传入,还进一步分析了印度故事在中国的译介和流传过程中的“中国化”现象。例如《宣验记》中的“鹦鹉灭火”的故事,在中国古籍中即有好几种变体,他指出:“印度故事中国化可能有多种方式,但是大体说起来,不外两大类:一是口头流传,一是文字抄袭。前者可以拿月兔故事做一个例子,而后者的代表就是一个鹦鹉灭火的故事。”接着他总结了印度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一般过程与规律。指出:“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的:印度人民首先创造,然后宗教家,其中包括佛教和尚,就来借用,借到佛经里面去。随着佛经的传入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文人学士感到有趣,就来加以剽窃,写到自己的书中,有的也用来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劝人信佛,个别故事甚至流行于中国民间。”
在谈到唐代文学与印度文学的关系时,季羡林认为唐代文学两种崭新的东西,传奇和变文,都与印度文学的影响分不开。而在内容方面,印度的影响更是普遍而深刻。他指出中国“龙”和“龙王”都来自印度的梵文,目连救母的故事作为一种题材,对中国的民间文学和戏剧影响甚大,唐代柳宗元的《黔之驴》与印度《五卷书》第四卷中的第七个故事很相似。明代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则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有渊源关系。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记载的“猫名”寓言,也是从印度搬来的。季羡林还列举了近现代文学家苏曼殊、鲁迅、沈从文等与印度文学及佛经翻译文学的关系,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总之,《印度文学在中国》这篇长文,是季羡林关于印度文学在中国传播历史的一个提要式的文章,包含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学术信息和学术见解。
在许多问题上,他接受了胡适当年在《白话文学史》中的一些观点,又为胡适的论点做了更充分的证明。季羡林的研究基本是实证的、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十分注意佛经翻译在中印文学交流中的重要媒介作用,对文本,特别是文本细节进行细致分析,争取找到更多的细节暗合之处,同时也注意到了印度文学流传到中国后,经中国的改造而发生的变异。从这些方面来看,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这篇文章中已有全面的体现,确立了季羡林学术研究中的那种重材料、重实证、不发空论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和学风。到了70年代后期,他又将这篇文章中的若干问题进一步展开,写成了《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多篇文章,将研究具体化、深入化。
季羡林的研究在比较文学方法上无疑是学术正轨,堪称楷模。当然,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由于有时过于强调印度影响中国,而对双向的交流似乎揭示不够,有的结论出现了争鸣和商榷的意见。例如,关于月兔的故事是否就来自印度?季羡林的研究由于实证材料不多,未能展开。后来,台湾的著名印度问题专家糜文开的长文《中印文学关系举例》(台湾《中外文学》1981年10卷1期)以大量的资料考证,说明印度佛教故事吸收了中国的月中白兔的传说,其材料与结论都较充分,可与季羡林先生的看法并存,聊备一说。
再如,著名印度学学者吴晓铃(1914—)在此时期发表了《西游记〉和〈罗摩延书〉》(《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一文,他认为:“西游故事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想象从释典翻译文学的夹缝里挤进来的一点点的、删改得全非本来面目的《罗摩延书》(即《罗摩衍那》——引者注)的故事的片段竟会影响到《西游记》故事的成长,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吴晓铃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季羡林先生不同,而与鲁迅先生相近。80年代后,也有新一代学者撰文认为《西游记》中没有多少印度影响,孙悟空是中国的“特产”。又如,中国的“龙”是否就是从印度传来的?1980年代后有年轻学者做了更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这些观点和看法孰是孰非不必过早下结论,但作为学术上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可喜的。
谈到吴晓铃关于印度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有一篇论文很值得重视,那就是《印度戏剧的起源分类和角色》(《戏剧论丛》2辑,1957年5月)。该文在今天看来也是研究印度古代戏剧起源问题最翔实、最有说服力的文章。吴晓铃提出关于印度古代戏剧起源的四种不同说法,即“神启仙造”、“吠陀祭仪”、“史诗轨范”、“希腊影响”。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关于印度戏剧与希腊戏剧的关系,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他认为,侵略过印度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是最喜爱戏剧的,他在战争的时候都带着随军的剧团。而亚历山大入侵印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印度古典戏剧在公元后1世纪左右便兴盛起来,这是耐人寻味的。他指出,希腊悲剧的最后一个伟大作家优里僻特拉死在公元前406年,比第一部印度古典戏剧的出现差不多要早五百年。
印度虽然有人传诵他的作品中的名句,但这只能说是大众欣赏文学名著的一般现象,不足以作为证明希腊戏剧与印度戏剧相互关联的主要材料。因此,许多梵学者主张希腊悲剧是促成印度戏剧兴起的原因,希腊新戏剧才是直接影响印度戏剧成长的真正根源。接着,吴晓铃从序幕、分幕、布景、结构、穿插几个方面,说明了印度与希腊戏剧的相似性:它们戏剧在开头都有一个序幕,作用是交代作者的姓名、剧本的名称和内容梗概,演出的目的和对观众的祝贺;希腊戏剧一般都分五幕,印度戏剧有时略有增减;两者都不采用背景,只用一方帐幔将前台与后台隔开;希腊戏剧和印度的“英雄戏剧”(“那叱伽”)的剧情结构很相似,印度“英雄戏剧”差不多总是一个王公与一个民间女子相爱,中间出现挫折,后来证明那个民间女子是一位公主或高种姓出身,于是结为姻缘;希腊新戏剧的剧情大体相同。
此外,吴先生还指出,初期的印度戏剧是很严格地遵守“三一律”的,印度和希腊戏剧中的丑角的身份也相似,都是寄食型的帮闲之流;希腊喜剧和印度戏剧都使用雅俗两种语言。吴晓铃的这篇文章,充分吸收了国外梵学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这对于揭示东西方戏剧之间的久远联系是很有帮助的。此前,许地山曾撰文认为中国戏剧与印度古代梵剧存在渊源关系,而吴晓铃所论证的梵剧与希腊戏剧的关系,对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自然也有参考价值。
在中印及东方各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还需提到的是艺术史专家常任侠(1904—)的《中印艺术因缘》,该书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收论文十一篇。虽然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文学,但与文学问题密切相关,所以也值得一提。该书在“内容提要”写道:“本书对于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在古代和现代的文化艺术交流上,做了细致而深入的介绍,以增进人民与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保卫和平的力量。内容涉及中、印古代艺术史的伟大成就,如麦积山石窟与阿旃陀石窟艺术,我国的杂技、傀儡戏和皮影戏艺术,古代中印间象棋与骰子的交流关系,以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团和印度文化代表团演奏的舞蹈与音乐等。”
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以中印艺术的交流为主题,也有一些文章涉及除中印以外的日本、朝鲜乃至西方诸国,例如在谈到傀儡戏的时候,指出中国的傀儡戏起源于原始社会,汉末以后高度繁荣,便向外传播。“自唐以来,日本也叫‘傀儡师’,直到现代,在翻译上才改称木偶戏。日语中的‘窟傀子’和俄语中的‘顾傀儡’,大概都是傀儡的译音。我国历史上的名词,很久的已成为国际的通用语了”。显示了作者纵横捭阖、贯通古今中外的广阔的文化视野,这正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精髓。
在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此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研究中缺乏大家手笔,像上述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中的季羡林那样的大家学者,在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中还没有出现。1930—40年代中日文学研究的大家,如周作人、钱稻孙等,许多都像钱钟书曾经说过的,由“日本通”变成了“通日本”。抗战胜利后他们受到了制裁,也疏离了日本及日本文学方面的研究。
加上1930—40年代日本的侵华,1950—60年代中日关系的非正常化等因素,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领域在这时期显得更为萧条,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篇小文,如张葆华的《鲁迅的作品在日本》(《天津日报》1956年10月19日)、小战的《鲁迅与小林多喜二》(《天津日报》1962年11月7日)、陈北鸥的《中国戏剧在日本》(《光明日报》1962年2月18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在数年中没有储备人才,未能及时适应新的形势,仍然处在沉寂中。直到1978年,才有刘德有《白居易在日本》(《光明日报》1978年8月13日),吴泰昌的《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战地增刊1978年第2期)等两三篇文章出现,但这却预示着1980年代后中日比较文学的崛起和全面繁荣。至于中国与朝鲜、越南等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文学研究,比中日文学研究领域更为薄弱,严重缺乏专门的研究人员。
在中朝文学关系方面此时期只有林辰的《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文艺报》1950年第3期)一篇文章和从朝鲜文翻译过来的一两篇文章。我国与中东地区各国文学比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季羡林、刘振瀛合写的《五四运动后四十年中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一文,是仅有的一篇介绍东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用文献统计学的方法,对蒙古、朝鲜、越南、日本、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阿富汗、伊朗、古代阿拉伯、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约旦、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南非等亚非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做了统计。例如,作者统计出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的蒙古文学作品单行本二十二种,朝鲜文学作品六十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