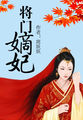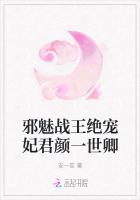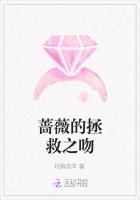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与文学关系,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怀有乌托邦式的憧憬之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欧洲有所传播。18世纪以后,随着中西文化实力的消长变化,欧洲人及欧洲文学中的中国观及中国形象也有所改变。到了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文学开始大规模输入并影响中国。中国与欧洲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有关研究,从不同侧面发掘并系统呈现了中国与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文学关系的面貌,并在比较中得出了许多有有价值的见解、观点和结论。
(第一节)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一、中俄文学关系的总体研究
自从1900年中国开始接受俄罗斯文学起,到2000年的整整一百年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数量在全部外国文学中占第一位,我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与评介文章,在我国全部的有关外国文学的文章中也占第一位。俄罗斯文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运动、文学观念和作家的创作、评论家的批评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也主要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研究。
对中俄文学关系进行系统的总体研究,开始于戈宝权。他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他在各种学术期刊或书籍中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中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文章。1992年,这些文章连同中外文学关系的其他研究文章,收在《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中,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中的第一部分——“中俄文字之交”部分又分三组,第一组是“俄国作家与中国”,其中谈到了普希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摩维支等九位作家与中国的关联。
第二组是“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分别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系统而有重点、以点代面地清理了20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轨迹。第三组“中国的俄国和苏联文学翻译家及研究家”,介绍了瞿秋白、鲁迅、耿济之等对俄苏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做出的历史贡献。其中大部分文章发表于1950—60年代,一部分文章发表于1980年代。戈宝权作为一个有突出成绩的俄苏文学翻译家,非常熟悉俄罗斯作家作品,许多珍贵的材料是他在翻译某作家作品时发现的。
例如,在《托尔斯泰和中国》一文中,戈宝权谈了自己在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之关系、中国译介托尔斯泰的历史方面的新发现。他指出了托尔斯泰如何钻研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孔子、孟子的著作。他还考证出了与托尔斯泰通信的两个中国人中除了辜鸿铭为人所熟知之外,另一个究竟是何许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俄文译音,有的判断为“钱玄同”,有的判断为“张之洞”,而戈宝权根据自己深入托尔斯泰博物馆中所发现的原信复印件以及有关的史料,考证出这个人是“张庆桐”,并介绍了张庆桐的生平。戈宝权还第一次描述了中国译介托尔斯泰的历史,指出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从英文译出的《俄国政俗通考》中的一段文字是最早介绍托尔斯泰的中文文字,指出我国出版的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的单行本是1907年香港礼贤会出版的《托氏宗教小说》。戈宝权作为一位中俄文学交流的实施者和见证者,他在谈论和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的时候,能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体验融入研究中,将个人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文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统一在一起。
这是他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他研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对中俄文学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文学史”的概念,但他的研究已经包含了翻译文学史研究所应包含的基本要素——原作家、原作品、译作、翻译家、读者等,为今天我们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戈宝权的文章采用的是严格的传播研究方法,注重史料的挖掘、考证和梳理,注重以事实说话,文风朴实严谨,决无空论。当代中国学界,许多人把“理论”理解为抽象的宏论、形而上的思辨,甚至是超越史料与事实的玄言空言。而实际上,戈宝权这样的研究才是得“理论”之真义——把研究对象讲清楚,展示历史的真面目,这本身就是“理论”。
1990年代初我国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倪蕊琴主编、陈建华副主编的《论中苏文学的发展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跟上述戈宝权的研究一样,这部著作也采用了将系列论文编辑成书的方式。
但戈宝权在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是从事实与文献出发的传播研究的实证方法,而《论中苏文学的发展进程》则是以传播研究为主、平行研究为辅。其中,倪蕊琴写的《中苏文学发展进程比较(1917—1986)》一文作为全书的“绪论”冠于卷首。也是全书中提纲挈领的一篇重要文章。她分析研究的重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文学关系。她勾勒出了“中苏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及其颇有戏剧性的文学关系”,即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对应的关系。从中国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对应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即50年代的接受时期、60—70年代时期,80年代的选择时期。其中,50年代中苏文学是同期对应关系,60—70年代大体是逆向对应关系,80年代基本是错位对应关系。这样的勾勒和概括相当洗练地呈现了中苏当代文学的发展的基本对应规律。
全书正文十八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这些文章试图对中苏文学的发展进程进行历时的、纵向的比较研究,这在选题上是很有意义的;在一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苏当代文学发展的对应性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但同时,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显然只是初步的,有的还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上,理论上的更深入的分析仍有较大的余地。书中只有六篇文章是属于比较研究的文章,第四、五部分的全部文章和第二、三部分的有些文章是单纯论述前苏联文学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固然有助于读者对前苏联文学的深入了解,但却与中苏文学的“比较研究”的大论题相对游离。
与《论中苏文学的发展进程》几乎同时出版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再次体现出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俄苏文学研究方面的实力。这部书是由王智量教授主编的系列论文集。执笔者除王智量外,还有夏中义、王圣思、汪介之和王智量的研究生王璞、王志耕、刘文荣、戴耘和李定。
研究的范围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与中国文学的接受的研究,重点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及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有对中国翻译俄国文学的历史的总结。对于俄罗斯这些经典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此前已有许多论文发表,在此基础上使研究有些新意,有所深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俄国文学与中国》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在切入的角度、论述的方式乃至结论的概括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出新意识,并在不少方面有所突破。
例如,王志耕在《果戈理与中国》一章中认为,“果戈理在写黑暗方面给了中国作家三方面的启示:写人物身上的黑暗,写人物眼中的黑暗,写人物心中的黑暗”;戴耘在《屠格涅夫与中国》一章引用了国外批评家对屠格涅夫创作特点的评价,即认为屠格涅夫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独特性就是他的“诗意的现实主义”,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王圣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一章中分析了中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接受上的特点,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描写,而对陀氏的另外的方面,如二重人格、地下人、偶合家庭、宗教关怀等主题,则不甚关注。王璞在《契诃夫与中国》一章中谈到契诃夫的戏剧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时认为,契诃夫戏剧的特点是情节的淡化和抒情的氛围,即“非戏剧化倾向”。这种倾向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创作。
曹禺、夏衍和老舍的作品中都有这种影响的印记。夏中义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与中国》一章中,将俄罗斯三大批评家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做了综合的研究考察,认为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上,能在政治与艺术两方面皆投中国文坛所好者,非别、车、杜莫属。这是别、车、杜能够长期成为在中国“享受美学豁免权的唯一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派”的原因。但是,这种对别、车、杜文艺思想的膜拜,却带有强烈的政治实用色彩,从而将他们的完整统一的文艺思想割裂了。
李定的《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一章,对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情况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并列出了《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出版数量变化表》等多种表格,用严格的科学统计学的方法,展示并分析了1903—1987年的85年间,中国翻译出版俄国文学的数量、文体种类、版本、选题变化等多方面的情况。搞清和掌握这些情况是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流行着一波一波的“理论”热潮,习惯于空泛的议论,而对文献资料、学科史实的研究却比较冷漠,对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基本情况缺乏认真系统的清理与研究。因此,李定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今后更为翔实的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汪介之(1952—)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透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从文化视角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的专著,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由个人著述的系统的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俄文学关系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全书最富有新意的是第四章从“忏悔意识”、“思辨色彩”的角度对中俄文学所做的比较。作者指出,由于东正教的影响,忏悔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积淀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俄罗斯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作家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分析。但俄罗斯文学的忏悔意识并未被中国作家所理解、所接受,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乏基于个人与环境冲突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从政治角度展开的“知识者自我批判”,却难以见到从宗教信仰出发的具有深刻忏悔精神的作家。
这是十分正确的见解。作者同时认为在这方面“也许只有鲁迅、巴金等人是少有的例外”。但严格说来,鲁迅、巴金恐怕也不是“例外”。他们的“忏悔”和俄罗斯作家的“忏悔”根本上是不同的。作者还指出:“浓烈的思辨色彩”是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色,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达到一定哲理深度的作品却颇为有限”;“除了鲁迅等少数杰出作家之外,现代作家一般尚未达到对历史生活、社会图像、人性表现、社会价值做出带哲理性的分析与把握的高度。这既为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所决定,又为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势所制约”。这显然也是十分有价值的见解。实际上,在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哲理”,有时也相当“深刻”,但那常常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刻,而不是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那种宗教的、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抽象层面的深刻。作者还指出,中国文学在认识和接受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有不少片面性,出现了一些有意无意的忽略和失落。
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作家看重的是俄罗斯作家的社会批判,却忽略了俄罗斯作家对俄罗斯国民性、民族心态所做的描写、反思与批判;同样的,我们对别林斯基等俄罗斯批评家,看重的是他们的“社会—历史批评”,却忽略了他们的美学批评。第五章《一位文学巨人在中国的命运》,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作者在此前曾出版了《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漓江出版社1993年)一书,对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这一章里,汪介之指出:“中国人心目中的高尔基,却多少是中国人自己描画的。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曾被各种‘理论’所左右,包括被庸俗社会学控制过一个长时期。正是这种‘社会学’使高尔基受到损害并发生‘形变’,使作家的完整面貌不为一般读者所知,这就为一些人曲解甚至贬低高尔基提供了‘证据’。”作者回顾和分析了中国翻译、介绍、评论和研究高尔基的历史,指出了“左”的政治化、功利化倾向和庸俗社会学理论对高尔基的曲解和贬损。
汪剑钊的专著《中俄文字之交》(漓江出版社1999年)和上述汪介之的著作一样,也是一部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专题著作。作者选取了中俄文学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为论述对象。其中,关于五四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及“拉普”与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问题、“新写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问题等,作为中俄文学关系中的重点问题,此前不少文章和著作多有论及,在这些问题上,汪著似无多大突破。
但也有部分章节是有新意的,如《中国的“青春型写作”与肖洛霍夫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章,对50年代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对王蒙的《青春万岁》与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杨沫的《青春之歌》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之间的关联,做了比较论述。此外,作者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对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影响也做了令人感兴趣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