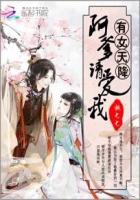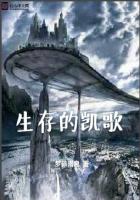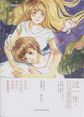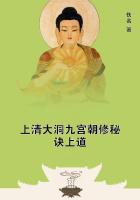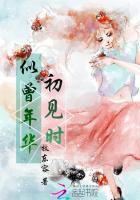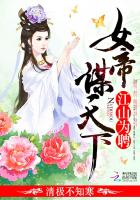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也是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和外国——主要是欧洲和东方的日本——的翻译文学理论的比较,有助于突显我国翻译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由于翻译文学存在共通的规律,面临大致相似的困难和问题,故中外翻译文学理论在探讨的路径、思考的问题、思维的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有许多不期而然的地方,对此可以进行类同的比较,如由翻译经验谈向翻译理论形态的演进,由宗教经典的翻译孕育文学的翻译,由探讨翻译的一般规律到探讨文学翻译的特殊规律等等。
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可以进行平行的对比,如中国翻译理论以文艺学为主导的传统,西方翻译理论文艺学与语言学(科学)的二元对立与互补,中国翻译理论多为短小的文章和片段的议论,西方翻译理论则较早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有关重要的概念术语,也是比较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如中西翻译文学理论中的“直译”、“意译”,中国的翻译文学中的“神似”论和西方翻译文学中的“风格”论,晚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论和现代西方的“等效”、“等值”论等等,都有比较研究、相互阐发的必要。同时,中外翻译理论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也是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内容。如清末民初中国翻译理论与日本译坛的关系,就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重要的研究领域。
鲁迅、周作人以及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的翻译活动均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他们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理论主张与日本文坛、译坛有什么关系?搞清这一问题显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这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注意,迄今为止这样的文章很少。笔者见到的印象较深的只有钱剑锋的严复的“雅”与二叶亭四迷的“言文一致”》(载论文集《翻译与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但研究的还不是中日译论的传播与交流问题,而是平行的比较研究。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翻译理论受到前苏联的影响,80—90年代,中国译学理论(包括翻译文学理论)受到了欧美译论的很大影响,也受到了西方相关学科——如哲学阐述学、美学、语言学——理论的很大的启发,对此也有必要从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加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既可以清理中外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中外译论的相互对话和会通。
在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方面,谭载喜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的第九章《中西译论的比较》做了可贵的尝试,可惜尚不深入。傅勇林的论文集《文化范式:译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有些文章有意识地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问题。论及中国译学的历史与现状,他认为:中国译学研究的现实是“局部精确,整体零碎”;探讨翻译技巧,即“术”的文章多,而“‘论’的层面亦与严几道‘信达雅’之说形影不离,却鲜见‘体制别创’、异调新谈,始终徘徊在‘学术四合院’的方井里,尺幅不纳寰宇,境界不深,思想苍白,学术乏力,既不能塑造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建立自己应有的学术范式,亦不能以深具原创性的研究实绩汇入国际学术主流”。根据以上我们对中国译学80—90年代研究现状的大体分析,可知傅勇林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对于严复“信达雅”的“形影不离”不断讨论和阐发,倒是逐渐形成了唯一具备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范式”,对此不应低估。
从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理论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在译学理论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首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8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翻译问题、翻译文学问题的文章。1994年,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了“译介学”这一概念,对“译介学”研究的性质、内容及对象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并在《中西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教材中以专章专节表达了这些见解。1999年,他的专著《译介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他近20年间关于比较文学、翻译文学、译介学研究的集大成,标志着他的译介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系统。《译介学》在学术上的特色和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作者评述了西方、俄国和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艺学派”,并指出从文学角度出发的翻译研究是20世纪翻译研究的一种趋向。一直以来,各国翻译史上都存在着“科学学派”和“文艺学派”两种不同的翻译思潮,比较文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全部的翻译现象,而是翻译中的文学翻译,而文学翻译一般归属为“文艺学派”。
谢天振没有以“文艺学派”这个西方翻译史上的流派称谓来称呼中国翻译史,在谈到中国翻译史上的类似现象的时候,他审慎地表述为“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学传统”,指出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去研究中国翻译史,不仅有可能,也有必要,从而为比较文学的译介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找到了历史依据。第二,他深入地论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现象,并把翻译家的“创造性叛逆”看作是文学翻译的一种规律性特征,认为文学作品的有关词语中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象”,翻译不应该失落和歪曲这些意象,并认为当初赵景深将“milkyway”译成“牛奶路”而不是译成“银河”,曾被鲁迅嘲讽,现在看来是无可厚非的。第三,鉴于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各种文学史书上不写翻译文学,不给翻译家和翻译文学以一定的位置,谢天振提出应该承认翻译文学。他认为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观点的提出给中国比较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共鸣。他认为对翻译文学的承认最终应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别(中国)文学史上让翻译文学占有一席之地,一是编写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史,并就如何撰写“翻译文学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学翻译史”不等于“翻译文学史”。前者侧重于文学的事件和翻译家的评述,后者是以文学为主体,也是理想的翻译文学史的写法。这些理论和观点对90年代后期的比较文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特别是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对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与写作开始于1920年代后。有梁启超的长文《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年)、阿英的《翻译史话》(1938年)。1980年代初,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后扩充为《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翻译史的著作;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祖毅、任荣珍合著的《汉籍外译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书籍在外国翻译出版历史的专著。199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对中国和日本翻译史做了大体的描述;1998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的《西域翻译史》,系统论述了古代我国西域地区翻译的历史。这些书并不专论文学翻译,但含有不少翻译文学的内容。
对中国的翻译文学史进行独立的研究,是以《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问世为标志的。
80年代中期,陈玉刚教授组织了李载道、刘献彪等五位撰稿人合作撰写《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到1989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陈玉刚主编的这部《史稿》。《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并不是从古到今的中国翻译文学通史,而是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起鸦片战争,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书按不同的历史阶段分为五编。每编的第一章均是“概述”,以下各章为分述。第一编论述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从1840年至1919年,分别以专章评述了梁启超、严复、林纾的翻译活动与贡献。第二编的时间从1915年到1930年,作者将这一时期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初期,分章评述了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四个团体和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四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第三编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中期,从1930年到1937年,分别评述了“左联”、瞿秋白的翻译,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与研究,《译文》杂志、《世界文库》丛书对翻译文学的贡献。第四编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后期,时段是1937年至1949年,分别论述了上海“孤岛”时期、国统区、解放区三个不同政治区域的翻译文学,其中重点介绍了朱生豪、梅益、傅雷、戈宝权、方重、肖三、姜椿芳等人的翻译文学。第五编是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分章介绍我国对亚非拉、对俄苏、对欧美各国文学的翻译。作者在“编后记”中谈到了本书编写的原则,即“以文学翻译活动的事实为基础,以脉络为主,阐明翻译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并力图对翻译文学和新文学发展的关系,各个时期翻译文学的特点,重要文学翻译家的翻译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翻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和它同其他形式的文学基本的不同点等问题进行探讨”。
可以说,作者在本书中基本实现了这些设想和目标。现在看来,这部书对翻译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它的填补空白的开拓性。作为我国第一部翻译文学史,在选题上有着相当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为此后的翻译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借鉴。它基本确立了以翻译家和翻译史实为中心的翻译文学史的写法,并且将文学翻译理论作为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加以评述。当然,作为第一部翻译文学史,它难免存在一些不足。该书以评述文学翻译的史实为主,评介的中心是“翻译活动”,实际上是“文学翻译史”而不是“翻译文学”史。“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应该以文本为依托,但本书对文本的分析却是薄弱的。
1996年出版的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是与《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同类的著作。但它是一部中国翻译文学的断代史和专题史,专谈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前17年间我国的英美文学的翻译,在写法上与《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基本相同,那就是以翻译文学的史实、翻译活动的记述为中心。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统计出了十七年间出版的英美文学译作四百六十种,并做成表格附录于后;提到和评介了三百多位翻译家,在全书的中心部分第二编中,分章重点评述了二十六位重要的翻译家,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卞之琳、曹未风、方平,诗歌翻译方面评述了方重译乔叟、朱维之译《复乐园》、王佐良译《彭斯诗选》、查良铮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袁可嘉译英美诗歌、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小说翻译方面评述了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小说、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韩侍桁译《红字》、曹庸译《白鲸》、杨必译《名利场》、吴劳译《马丁·伊登》、王仲年译欧·亨利小说等,此外还评述了综合型翻译家傅东华、张谷若、黄雨石、王科一。
在评述翻译家的翻译成就时,作者将基本史料的陈述与作品文本的分析结合起立,采取了将英文原作与译文抽样加以比照的方法,来说明翻译家译笔的特色。这样一来,“翻译文学”的本体色彩就突出了,这是本书较《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一个显著的进步。
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继上书之后出版的又一部中国翻译文学的断代史。郭延礼是中国近代文学的著名专家,其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我国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近代文学史。他以近代文学史家的身份研究作为近代文学之组成部分的中国近代翻译史,是有着明显的学术优势的。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比较而言,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尤其是书刊出版杂多,资料大都处于缺乏整理的散乱状态。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中,近代翻译文学这一段的研究在资料的收集、辨析、考证上最为困难。除了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资料整理外,郭延礼在资料的积累方面是得天独厚的,这是他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成功的基础。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不是翻译家,也没有翻译经验,却能够写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原因。
该书1998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一种推出,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赞赏。现在看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是上述丛书中质量最高的一部专著。在材料的丰富翔实、资料使用的准确可靠、论说的条贯、持论的平正方面,堪称翻译文学史写作的范例。全书分上下两篇。在绪论中,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到五四运动止,统计出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二百五十人左右,共翻译小说两千二百六十九种,诗歌近百篇、戏剧二十余部。该书上篇以翻译文学的文体形式分类,在总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特点之后,分专章论述了近代翻译文学理论、诗歌翻译、小说翻译、政治小说翻译、侦探小说翻译、科学小说翻译、戏剧翻译、伊索寓言翻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