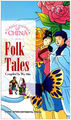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文学研究是受时代和政治干扰相对较小的部门,1980年代之前,翻译理论的探讨和建构已有丰厚的积累。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的翻译文学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大有推进,主要表现为译学理论及翻译文学的史料整理开始规模化和系统化,翻译文学专题研究(包括翻译家的个案研究、理论命题的专门研究等)进一步深化,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开始展开,并成方兴未艾之势。
(第一节)对中国译学理论和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一、对翻译理论资料的整理
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译学理论研究中,资料建设作为研究的基础工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国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许多翻译家对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翻译观都做了总结,并形诸文字。有的翻译家和理论家还提出了极有理论价值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见解主张。对此,近年来翻译界已有人下大力气做了收集和整理,出版了若干重要的资料集。较早的有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的刘靖之编《翻译论集》。内地出版的有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翻译论集》,收集自汉末至1980年代初期一千七百年间有关翻译的文章一百八十余篇。
按照时代,分为汉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五四以来、解放以后共五辑。本书所收译论,尤其是古代的译论,多与佛经翻译有关,并非纯粹的文学翻译理论,但由于中国传统翻译是宗教经典翻译中包含着文学翻译的因素,所以,《翻译论集》在现在看来仍是研究中国译论的最集中、最丰富、最权威的资料集。早在1940年,翻译家黄嘉德就编选出版过《翻译论集》(西风社),我国港台地区也出版过翻译理论的资料集,但其系统性、规模均无法与之相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的出版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也包括翻译文学理论研究乃至翻译文学研究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冠于卷首的罗新璋的题为《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刊物介绍进来不少国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真可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相形之下,我们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就那么贫乏、那么落后?编者于浏览历代翻译文论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
同年,中国译协和《翻译通讯》编辑部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翻译研究论文集》,分两册分别辑录了1894—1948年和1949—1983年间散见于各种书刊上的有关论文一百一十篇,其中多数文章为文学翻译家所写的涉及文学翻译的文章。199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自俭、刘学云编选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新论(1983—1992)》,该书在编选的时间范围上显然是承续外研社的《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83—1992共十年间在《翻译通讯》(后改名《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和《现代外语》等刊物上发表的48篇文章和专著节选6篇。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各类文体的翻译研究;第二编为译学本体论研究,包括总论、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美学与风格、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史与译论史研究;第三编是跨学科研究,涉及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化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与翻译之关系的研究。
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南京大学许钧主编的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录》,在时间上基本承续《翻译新论》,编选了1998年之前约十年间的有代表性的翻译研究文章80多篇,分“翻译纵横谈”、“翻译艺术探”、“翻译理论辩”三部分。本书在选文方面很见眼力,所选大都是翻译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界的名家或新秀之作,文章大都言之有物,观点新颖鲜明,是近20年间最精当的一个译学理论选本。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选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1985年);张柏然、许钧主编,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学论集》(1997年);谢天振主编的《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收1998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三十多篇。
对当代健在的或仍然活跃于译坛的翻译家的译学观点、译学理论进行采集和整理,是比较文学研究及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迫切任务。在这个方面,山东聊城师范学院的王寿兰和南京大学的许钧做出了贡献。80年代初,王寿兰用了数年时间向全国各地的老一辈著名翻译家发函并亲自到各地走访,约请了一百四十多位翻译家撰写有关文学翻译的心得、体会、经验、观点、主张和看法的文章,并将这些材料编成了一部书——《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七十万字,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当代文学翻译家的词典,以翻译家为单元,先是某一位翻译家的翻译生涯自传或简介,然后是他所撰写的谈文学翻译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是首次在本书中发表,翻译家们对各自的翻译经验做了总结和自我评价,有许多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不可替代的有关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从1998年开始,许钧在《译林》杂志的专栏中,就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当代一些著名翻译家,如季羡林、罗新璋、袁筱一、李芒、许渊冲、萧乾、文洁若、吕同六、郭宏安、赵瑞蕻、叶君健、方平、杨武能、草婴、李文俊等对谈,并于2001年编辑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对谈这种灵活的形式里,翻译家们将自己的翻译经验和理论主张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为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及译学理论提供和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除此之外,1990年代出版的类似的文集还有香港地区的教授金圣华、黄国彬主编的《困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该书的特色是以收香港、台湾地区的著名翻译家的文章为主,在所收十三位翻译家中,就有台港地区的翻译家余光中、林文月、思果、高克毅、刘绍铭、金圣华、黄国彬等七人。其中,日本文学翻译家、《源氏物语》的译者林文月女士的《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一文,谈了她翻译三种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的心得体会。这些资料在大陆地区难以见到,因此该书在大陆的出版很有价值。
除了上述的各种译学理论的论文集外,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还出版了多种文学翻译家个人的翻译理论方面的著作或文集。重要的有许渊冲的《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王佐良的《论诗的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于雷的《日本文学翻译例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刘重德编著的《文学翻译十讲》(英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许钧的《文学翻译与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金隄的《等效翻译探索》(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8年)等等。
二、对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构建
对中国译学理论做纵向的梳理和研究,是译学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基础。在这方面,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系统地发掘、整理、描述和阐发了从汉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及重要的理论家的理论建树及其历史地位。全书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章,重点评述了从古到今70位翻译家、学者的翻译理论主张。作者擅长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在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学、考据学方面很有造诣。
这种文献学的功底也体现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全书资料丰富,也较为全面。有些资料——例如有关清末民初的翻译理论家康有为、张元济、高凤谦、罗振玉、胡怀琛、蒋百里等——此前无人注意或注意不够,没有现成的文献可以利用,作者在这方面探幽发微,在原始资料上做了发掘。有些翻译家的资料以前虽被收进有关资料集子中,但有重大遗漏,如章士钊早年的译论和周作人晚年的译论,都因在发表时用了化名而不为人知,作者对此做了补充并首次论及。作者对道安、鸠摩罗什、彦琮、玄奘、赞宁、梁启超、严复、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傅雷等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都做了细致的评析。该书出版后受到翻译界的好评,后又再版,成为近二十年间仅有的一部中国译学理论通史类的著作,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陈福康的著作是史的纵向的研究,那么,沈苏儒(1919—)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则是对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史的专题研究。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对中国翻译影响最大、最持久,也最有特色的译学理论,当推严复的“信达雅”。信达雅在中国译学史上的影响、对它的不同看法和理解,构成了现代中国译学理论发展演变的主线。在严复的信达雅提出一百周年之际,资深翻译家沈苏儒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专论信达雅的著作。作者以严复的“信达雅”说为坐标,在纵向上将近百年来不同的翻译家、学者对信达雅的内涵、价值等的不同看法,做了梳理。表明大部分人对信达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一百年来作为翻译工作者所遵循的翻译的总原则,信达雅说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还没有其他的译论可以取代。同时,在横向上,沈先生考察了在我国流传较广的几种外国译学学说,其中包括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论”、奈达的“动态对等论”、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等,并与严复的信达雅说作对照,进而从翻译的本质论上,从翻译的实践论上,分析了信达雅说在理论上的巨大的概括价值。
沈苏儒认为,照搬外来翻译理论并取代在我国翻译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信达雅这样的译论是行不通的。他提出,翻译的实践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理解原作,第二阶段为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原作的内容,第三阶段是使译作完善。信达雅分别是对这三个阶段的翻译要求的最精炼的概括。他同意傅国强等先生的看法,认为不能局限于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对信达雅的有限的解释,后人应该对这一理论不断加以阐发、修正、补充和完善。沈苏儒综合一百年来各家对信达雅的阐释,提出了自己对信达雅的阐释和理解,认为:“信”就是忠于原作,“达”就是使原作的内涵充分而又明白晓畅地在译作中得到表达,“雅”是要使译作的语言规范化并达到尽可能完善的文字水平,使译文为受众乐于接受。经过沈苏儒这样的上下纵横的梳理、廓清、辩正、阐发,严复的“信达雅”在现代译学理论中的意义就更加突显了出来。
在对译学理论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有不少翻译家和学者倡导在我国建立“翻译学”这一学科,尝试对“翻译学”进行新的理论构建,并出现了张泽乾的《翻译经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谭载喜的《翻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体系性的著作。特别是《翻译学》一书很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学,有两章内容分别论述“比较译学”和“中西译论比较”。在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周仪、罗平合著的《翻译与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王金玲的《文学翻译新论》(作家出版社1999)、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年)等。
其中,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具有鲜明的文学翻译理论构建意识,书中涉及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审美标准、结构系统、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及创造心理,文学翻译的主体与“自我”表现,风格的翻译,翻译的方法原则,翻译批评等方面,并把“和谐”作为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初步形成了文学翻译的理论框架。许钧的《文学翻译与批评研究》和周仪、罗平的《翻译与批评》两本书,则初步形成了我国“翻译文学批评”的理论架构,都是高质量的著作。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些译学理论著作尚处在草创的水平,理论上不够成熟。这突出表现在一些研究翻译文学理论乃至翻译美学的书,只不过是把文学理论的某些概念、术语、框架、思路,机械地套用在翻译文学现象上面。
例如,在谈到文学翻译原理的时候,就把“思想性”、“真实性”、“风格”、“内容与形式”、“民族性”、“时代性”等文学理论教科书上的流行概念拿来,作为全书立论的基础;在谈到“翻译美学”的时候,就把“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经验”等传统美学的概念拿来,再用翻译方面的材料加以填充。这里只以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为例来看其中的问题。该书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一种,作者试图用比较文学乃至比较美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翻译,把收集到的大量译例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中,立意很好。但是,作者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的学科精髓没有吃透,只是停留在有关概念的套用上,甚至有时套用得很是牵强、很不自然。例如,本书的书名“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就令人费解:是“文学翻译与比较美学”呢,还是“文学翻译比较的美学”,或者是“文学翻译中的比较美学”呢?翻遍全书,作者对此并无一字解释,令读者颇费猜测,不免歧义横生。再看正文,第一章标题是“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思辨”,其中的各节内容并没有什么“美学思辨”。
例如(第一节)“文学翻译理论比较美学观”,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各家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与主张的简要评述;(第二节)“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范型观”,以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几个人物为例,分析了翻译家、理论家或翻译家兼理论家、或翻译家兼多种“家”于一身等不同的情形,这实际上是对翻译家知识结构的分析,大可不必冠以“比较美学范型”这一大而洋化的美学哲学术语。综观全书内容,约百分之九十的文字是中国现代翻译作品的相同片段的比较及与原文的比较,是一部以实例分析为主的实践性的翻译研究著作,但作者极力以“比较美学”之类的学科术语做理论上的提升,反而显得勉为其难,捉襟见肘。这个例子说明,将文学翻译的研究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提高到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高度,必须基于作者内在的理论修养,而不能乞灵于外在的美学哲学术语和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