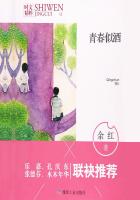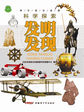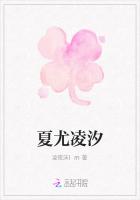(三)读者的诞生与作者的死亡
1968年,巴特在《占卜术》杂志上发表了《作者的死亡》这一著名文章。在世人的惊愕中,巴特喊出:“作者死了。”巴特认为在文学方面,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的逻辑。他对以往文学批评的做法表现出质疑,对传统文学中作者之于文本好比上帝之于人类的神学意义表示出不满。他愤愤地说:“作者至今在文学史教材中、在作家的传记中、在各种文学杂志的采访录之中,以及在有意以写私人日记而把其个人与其作品连在一起的文学家们的意识本身之中,到处可见;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学的意象,即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其‘秘闻’。”这是以往实证主义影响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的投影,这种做法使文学作品成为作家的附庸。巴特反对实证主义赋予作者的极大关注,他的目的在于颠覆作家的神学位置。
巴特从文学和语言学两方面来消解作者权威。在文学方面,他列举了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和超现实主义。他认为法国是马拉美最先充分认识和预见到有必要用言语活动本身取代直到当时一直被认为是言语活动主人的人,是言语活动自己在说话,而不是作者。瓦莱里则从未停止过对作家的怀疑和嘲笑,在他的全部散文作品中考虑的主要是语词的条件,语言本质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耗费心智之处,对作家内心的任何援引都将是一种纯粹的迷信。抛却浓厚的心理意识流动,在普鲁斯特的作品里,叙述者的声音与作家本人的生活脱离,作品不再是以往曾经感知过的人对自己生活经验的一种再现,而是一种即时铭刻。作品不再是现在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和一般将来时。超现实主义则强调期待的落空,让手写连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的事情,接受一种多人写字的经验,使作者失去了神圣性。
因而,巴特说,在现代写作中没有作者,只有抄写者,作者的死亡意味着一种本源意义的消失,一种原创性的消失。罗兰·巴特在《就职讲演》里断言:“伟大的法国作家的神话,一切较高价值的神圣守护者,已经瓦解了”,而且一种新型的人物出现了,“我们不再知道(或还不知道)怎样去为他们命名:作家?知识分子?书写家?无论如何,文学统治消失了。作家不再是中心舞台”。在《形象、音乐、文本》中,他说:“写作便不再表明一种记录、一种确认过程、一种再现过程和一种‘描绘’的过程……现代的抄写者在他的先辈哀婉的目光中,埋葬了作者,因为他不再相信他的手会慢得赶不上他的思想或他的激情。因此,他也就不再相信他在建立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写作规则时,还要再去强化传统作者的那种延缓的和无限加工的写作形式过程。相反,在他看来,他的手由于摆脱了任何声音,而只受一种誊抄的写作动作(而非表情动作)所引导,因此,他开拓了写作的一种无源头领域——或者,至少,这种领域只有语言本身是源头,也就是说,这种源头对其他一切源头表示怀疑。”作者源头的消失意味着文本意义的无处安家,文本便处于一种文本与文本的交汇之中,处于间性之中,文本永远在指向其他文本,这样,所有的文本便处于一种互文性的海洋之中。文本的意义叛离了作者,处于互文之中:“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文本不是从神学角度上讲可以抽出单一意思(它是上帝之间的“讯息”)的一行字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布瓦尔和佩居榭都是既高尚又滑稽的不朽的抄袭者,而且其最深刻的可笑之处恰恰表明了写作的真实。像他们一样,作家只能模仿一种总是在前的但又从不是初始的动作;他唯一的能力是混合各种写作,是使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对立,以便永远不依靠于其中一种;他也许想表明——但至少他应该明白,他打算‘表达’的内在‘东西’本身只不过是包罗万象的一种字典,其所有的字都只能借助于其他字来解释,而且如此下去永无止境;这种经历典型地出现在年轻的托马斯·德·昆西身上,他古希腊语很好,甚至能使用这种已死的语言来表达完全近代的观念和意象,波德莱尔告诉我们:‘他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套随时可以取用的词汇,这套词汇比繁琐的纯粹文学性主题词汇还复杂和广泛。’《人造天堂》;继作者之后,抄写者身上便不再有激情、性格、情感、印象,而只有他赖以获得一种永不停歇的写作的一大套词汇: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因此,在巴特看来,任何文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上的一个结点,它与四周的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克里斯蒂娃将自己的目光聚集于文本之中,巴特的互文性思想关注的焦点则是读者,这一在古典主义批评中长期缺席的人。为此,巴特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去换取。巴特眼中的写作状况应该是一种广义互文性的结果,这种多重性只有在读者的阅读中才得以体现:“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但是,这种多重性却汇聚在一处,这一处不是至今人们所说的作者,而是读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无一例外;一个文本的整体性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存在于其目的性之中,但这种目的性却又不再是个人的;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在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古典主义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文学中没有别人,而只有写作的那个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了,善心的社会正是借助于种种颠倒来巧妙地非难它所明确地排斥、无视、扼杀或破坏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为此,必须颠倒写作的神话,将作者的神学位置还给读者。巴特的惊世之语无疑是偏激的,此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斯潘诺斯对罗兰·巴特进行修正,在他那里,作者并没有死,只是去掉了神学意义,从上帝的使者变为普通的凡人,有着凡人的焦虑、无奈、空虚与无所适从。
二、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所有
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德里达一样驾轻就熟、见解深邃。他不满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文字的贬斥,通过对语言学中逻各斯中心论即语音中心论的批判来建构自己的文字学,并将文本置换到中心地位,“文本之外,无物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是他著名的文学观点之一。
德里达的文本性概念是一个大于互文性的概念,他由文字特有的间距、含混、重复、模仿与转义等,引申出文字符号总是指涉着不在场的其他符号,文字的意义不是单一的,总是指涉着其他文字。意义没有中心,意义永远处于无限滑落之中。在与克里斯蒂娃进行的名为符号学与文字学的访谈中,他说:“实际上,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
德里达的文本观与他强调的差异踪迹是糅合在一起的。在回答克里斯蒂娃关于非表达性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表征时(以往的语言观将语言看做是表达的,在德里达看来,语言应该超越这种表达性而追求一种非表达性),他说:“在所谓的(所表达的)‘意义’已经完全由差异组织构成的程度上,在已经存在着文本之间相互参照的文本网络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一‘单个术语’都是由另一术语的踪迹来标识的,所假定的意义内在性也已经受到它的外在性的影响。它总是被带到自身之外。”这段话看似回答语言的非表达性,实际上谈的是符号的非指涉性,符号不能表达本身,只有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异中才能取得自身的表达,意义正是由其他符号的踪迹构成的,对于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本来说,亦是如此,单一文本只有与不在场的其他文本相参照才能取得自身的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说只存在综合、延异和文本。
那么什么是延异呢?这里有必要对德里达的核心术语“延异”作一简要说明。196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探讨结构主义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德里达来谈谈结构主义。结果,这位年仅35岁的青年学者却在结构主义还大放异彩的时候宣读了一篇名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结构主义。这篇论文影响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世界近40年,德里达的名声也与解构联系在一起,人们只要一谈到解构就不得不想起德里达,德里达几乎成了解构的代名词,以至于和他访谈的人如果没有谈及“延异”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德里达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解构批评大师,是因为他不同意结构主义将一种普遍模式凌驾于文本之上的形而上学的做法,而提出“延异”这一核心概念。
其一,从词源学上来看,“延异”(Différrance)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汇。它与法语中的“差异”(Différrence)仅一字之差。字母“a”的嵌入构成了不同于原来的含义,把Différrence一词带向了时间性。在Différrence里只有差别的含义,只是在空间上显示出一词与一词、一物对一物的区别来,无法表现语言符号在时间上的差别。两个词在发音上完全一样,意义却不尽相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德里达旨在挑战口语优先、颠覆语言学上的“语音中心主义”。
其二,“延异”(Différance)具有双重性。德里达在这个生造的词里,汇聚了空间性(差异)与时间性(延迟)双重意义特征;从词性上看,在“延异”身上兼有动词和形容词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属于空间,是共时态的(Synchronically);另一方面,它属于时间,是历时态的(Diachronically)。德里达声称这个词不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策略,任何企图给“延异”下一个明确定义的想法都是思想领域的乌托邦幻想。他说:“Différance主题,当它带有一个无声的字母a时,它实际上既不起一个概念的作用,也不起一个词的作用。我试图证实这点。但这并不妨碍它产生概念的结果和动词性、名词性的具体事物。而且虽然这一点不能直接被注意到,但是它为这一‘字母’以及该字母的奇特的‘逻辑’的不断作用所表现,同时也被它们撕裂。”
在这个不是概念而产生了概念效果的“延异”身上,可显出拒绝定义的解构思想,解构同样也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与纷争的概念。在某些时候与某些场合,它一贯被人们理解为否定、颠覆、拆毁和破坏,这种思想至今仍表现出它的顽固性,被人们习焉不察地当作“否定”的代名词使用着。德里达对此表示十分恼火,以至于他多次以文字、著作、访谈等形式为解构而辩白。在与迪迪埃·卡昂(Didier Cahen)的访谈中,德里达强调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而是一种肯定性的运动,将解构简单地理解为破坏与否定是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学过程。”他似乎对人们把结构理解为否定性非常不满。他颇为不耐烦地说:“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Being)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认为解构就是否定,其实是在一个内在的形而上学过程(intrametaphysical process)中简单地重新铭写。”他还说解构不仅仅是对于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还必须向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最顽固的传统挑战。
延异的无法定义性、非概念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延异是无法定义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把根源、中心和在场等含义重新引入延异之中。另一方面,因为延异在语言中的作用,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真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的地位和功能,但事实上延异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名称,它可以被其他如‘痕迹’、‘游戏’、‘播撒’、‘文本’或‘源初文字’等策略性的名称替代。”
其三,任何事件总是发生在某一特定时刻,思想与文字不可能对其作“实况直播”,事物在头脑中产生印迹总是延迟的。文字符号总是指涉着不在场的符号,这样就具有了指涉他者的性质。符号一开始就以偏移的方式运动,它总是偏离本身、漂浮的能指。这样文本就表现为歧义、派生、转义和互文,文本就通向解构,通向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