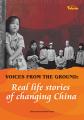遗嘱一般是在年迈或临终前才立,但也有人为了稳妥起见而早立,以防最后措手不及。宋人袁采就主张“遗嘱之文宜预为”,不然的话,“风烛不常,因循不决,至于疾病危笃,虽中心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动,饮恨而死者多矣。况有神识昏乱者乎?”可见早立遗嘱也是一种习俗,并且大有人在。由袁采说的“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以及有关案例的判词所说的“其所谓遗言者,口中之言邪,纸上之言邪”来看,唐宋时期立遗嘱主要有口头和自书(书面)两种方式。
口头(含代书)遗嘱,是在立遗嘱的人不识字或者因病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采用的方式,也有的是觉得发生争执的可能性不大,口头嘱咐一下身后家产的处理,令当事人(主要是晚辈)遵守即可。但由于遗嘱“若曰口中之言,恐汗漫无足据,岂足以塞公议之口”,所以多数人为了防止日后发生争执时口说无凭,口述时还常请人代书。《文选》载南朝刘宋时候颜延年《陶征士诔》中有“式尊遗占”之语,唐人吕延济注曰:“遗占,遗书也;占者,口隐度其事,令人书之也。”由颜延年所说、吕延济所注可以知道,南北朝隋唐时期这已经是一种常用方式。唐宪宗时裴晋公“临薨,令弟子执笔,口占状”;《全唐文》卷302载王元宗“临终口授铭”一则,均属此种方式。宋代这种方式更为常用,如一个姓黄的寡妇在急病临死前曾经“面授遗嘱”,请娘家兄弟负责用自己的遗产充女儿的嫁妆;许文进为王氏的接脚夫,义子许万三显露出逐王氏独吞产业的苗头,“许文进病重,口令许万三写下遗嘱,分咐家事,正欲杜许万三背母之心”,等等。事实上,口头遗嘱尤其是涉及财产数量较大的时候,大都要请人代书,纯粹口头嘱咐很容易发生争执,一旦发生争执,官府又难以理断。所以,涉及大宗财产的遗嘱一般都尽量付诸文字,以为凭据。
自书遗嘱,是遗嘱的主要方式,也是沿用已久的方式。西汉颍川太守何并“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葬,为小椁,檀(但)容下棺”即可,告诫儿子不要接受皇帝追赠的钱物及薄葬诸事,即是用亲作“先令书”的方式为之的。《新唐书》列传所记姚崇、袁滋、刘弘基等人分家产的时候都有“遗令”,都是自书的遗嘱。敦煌发现的公元10世纪即唐末五代时期的文书中,有几件当时的“遗嘱格式”,其中比较简要完备的一件内容为:
遗书一道。某尊(专)甲
身染患疾,已经累旬。种种医疗,未蒙抽咸(减)。今醒素(苏)之时,对兄弟子侄诸亲等遗嘱:房资产业、庄园舍宅,一一条支分数。例(列)名如下:右厶乙生居杯幻,处在凡流。今复苦疾缠身,晨昏不觉,准能报答。因缘房资贫薄,遗嘱轻微;用表单心,情(函)纳受,准前支给。恐有诤论,盟(冥)路之间,故勒斯契,用为后凭。厶年月日遗书。同时同地的另一件文书是僧尼在传继私有财物的时候使用的遗嘱文书原件,与世俗民间通用的格式和内容应该相同:
尼灵惠唯书。
咸通六年十月廿三日,尼灵惠忽染疾病,日日渐加,恐身无常,遂告诸亲,一一分折(析)。不是昏沉之语,并是醒苏之言。灵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与侄女潘娘。更无房资。灵惠迁变之日,一仰潘娘葬送营办。已后更不许诸亲恡护。恐后无凭,并对诸亲,遂作唯书,押署为验。
外甥十二娘十二娘指印外甥索计计侄男康毛(押)侄男福晟(押)侄男胜贤(押)索郎水官左都督成真。
在作为见证人的9个人中,除外甥(女)十二娘不会写名字,按了指印外,其余8个人都是亲笔签名。这份遗嘱最完整,大致分为立遗嘱的原因、被遗嘱人、所嘱财产和义务、誓语和见证人,最后呈官府盖印。请到了“诸亲”和当地官员,但不知为何立遗嘱人灵惠和被遗嘱人潘娘没有签名。
宋代的遗嘱也大都是自书方式,如案例所载,曾千钧有两个女儿,过继了一个养子,病重“垂没,亲书遗嘱,摽拨税钱八百文与二女”;徐二的后妻带来其前夫的儿子陈百四,母子专其家产,“徐二虑之熟矣,恐身死之后,家业为异姓所攘,乃于淳祐二年手写遗嘱,将屋宇、园地给付亲妹与女,且约将来供应阿冯(按:指其后妻)及了办后事”;还有一个叫柳璟的人,为了让四个侄儿照料其孀妻幼子,临终时遗嘱每人每年给钱十千,“书之于纸,岁以为常”,几年后发生争执的时候,四个侄儿的理由也是说此遗嘱“系璟亲手”写成的。刘夔“前死数日,自作遗表,以颁赐所余分亲族”;涪州有个赘婿执其岳父的“遗嘱与手疏”和养子争家产,也是指的自书遗嘱。官府审理遗嘱纠纷案的时候,鉴别亲书笔迹是最可靠、最常用的方法(详后)。
北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陕西扶风法门寺的《重真寺真身塔主兼都修主赐紫衣大德志遗留记》碑文说,塔主志谦俗姓杨,在寺中数十年,“余与师兄志永、师弟志元辍郍衣钵,去寺北隅置买土田四顷有余,又于西南五里已来有水磨一座,及渠田地”。晚年的时候志谦嘱咐说:“羔羊尚立尊卑,鸿雁犹分次第”,这些共置的田产应该“一则用供僧佛,一则永滋法义所述诫勖”,按佛寺的习惯留作寺中公用,并且详细开列了田亩地段、房舍、牛车以及碌碡等物,总计折合款数,最后刻上了寺中所有僧人的名号。这是刻在塔身上的遗嘱,由于是以志谦的口气叙述的碑刻文字,也可以归入自书遗嘱的范围。
除了上述两种方式之外,唐宋时期的遗嘱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家训。古代士人常在晚年把自己一生的治家处世的经验整理成文字,传给后代,称之为家训或遗训、遗令、遗诫、世范,后来也有直接称为遗嘱的。家训的内容很广泛,所谈的不全是分家的问题,但大部分家训都包括分家的内容。因此,家训中的身后家产处理等内容也可以看作是分家遗嘱的方式之一种。事实上,家训也经常与遗嘱合在一起,如著名的唐代姚崇的家训全称就是《遗令诫子孙文》,其中的一段关于身后财产处置的内容为:
比见诸达官身亡之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惟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主张该分就分,不要贪图同居共财的虚名,导致亲兄弟为争家产而反目。姚崇不仅要求自己的儿子照此嘱咐去做,还要求历代子孙遵守,“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有明显的遗嘱特征。
家训的明显增多是宋代以后。仅宋人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所记,宋代名士的家训就有30余种。影响比较大的有司马光的《温公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赵鼎的《家训笔录》、朱熹的《朱子训子帖》和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这些家训有的仍然是嘱咐子孙不得分家析产,如赵匡胤的孝章宋皇后临终嘱咐娘家人不要分居,到真宗年间其弟弟宋偓闹分家,真宗仍然劝他要“务遵先后遗戒焉”;还有南宋绍兴年间赵鼎在《家训笔录》中约束其家人“田产不许分割”,而且要求“子孙守之,不得有违”;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的家训已经比较实际,多数家训都是告诫子孙要和睦相处,该分就分,不要因财产利害冲淡了骨肉亲情,如前引姚崇和袁采所讲的那样。不论哪方面的家训,不论子孙能否遵守,家训的作者们都是当作对子孙的身后嘱咐来写的。
口头(含代书)遗嘱、自书遗嘱以及家训,是唐宋时期分家析产遗嘱的主要方式。这些遗嘱的具体方式虽然不同,但是所体现的原则是相同的,即在诸子平均析分家产、分别传承门户的制度之下,有亲生儿子之家的家产门户可以自然地析分和传继,不必通过遗嘱方式;只有在没有亲生儿子或特殊需要的场合,才立遗嘱给女儿、赘婿或养子等人。此外,有子嗣之家超出常规安排家产的时候也可以采用遗嘱的方式,如刘弘基临终前留下“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良田五顷。谓之亲曰:若贤,固不藉多财;不贤,守此可免冻馁。余悉以散失”。这是把部分财物施散与他人、未完全按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分家的情况下才立遗嘱,有的家训也属于这一类。在正常的按习俗进行的分家过程中就不需要了。
订立遗嘱的手续,也有约定俗成的具体规定。由前面所引述的唐代遗嘱文书格式和宋代案例判词所说的“遗嘱经官给据,班班可考;质之房长,并无异词”来看,除了遗嘱人、被遗嘱人和见证人签押之外,一般还要经过两道手续。
一是要经过族中近亲的同意。征得族人同意认可的原因在于,在古人的观念中财产不是个人的,而是家庭的;既然是家庭的,也便是家族的;在无子嗣的家庭中,如果把财产遗嘱给女儿往往被带到婆家,遗嘱给赘婿、外甥外孙或异姓养子,都等于是把本家族的财产给了外姓人,剥夺了本族近亲子弟的潜在的继承权。所以族人的态度非常重要,族中长辈或近支兄弟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表示同意,遗嘱才可以顺利履行。这也是很早就形成的传统做法,前面引述过的汉代沛郡富人临终“呼族人为遗书”,即有征得族人同意的目的在内。唐代尼姑灵惠的遗嘱中有“遂告诸亲”之语,签押处有侄儿、外甥;在《敦煌资料》第一辑中收录的另外两份遗嘱,也说曾经“与汝儿女孙侄家眷等宿缘之会”,趁此病中“醒来之时,对兄弟子侄诸亲等遗嘱房资、产业、庄园、舍宅”等物。发生争讼的时候,官府也认为家产继承方面的遗嘱“必须宗族无间言而后可”,必须在遗嘱的“文字内诸子皆有知押”方为有效。在前面引述的《清明集》的案例中,曾千钧把家产遗嘱给女儿的时候,“千钧之妻、弟千乘、子秀郎并已签知”,表示同意,其弟弟就是代表的家族近亲。遗嘱文书一般由被遗嘱人保存,作为继承家产、继立门户的凭证,但前引柳璟案例说其遗嘱是“就其族长(处)索到”,这份由族长保存的遗嘱无疑也是经过了族长签字的。
尽管立继产遗嘱的时候要受族人制约,但不能违背立遗嘱人的意愿,更不能为他人所强迫。通常的操作过程与分家过程相似,先由户绝之家的家长决定了要立遗嘱,并且决定了遗嘱的内容之后,才征求族中近亲的意见;只要不违背习俗和律令,没有出格的地方,族人的同意只是一道手续,不能过多地干预。为了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即使不是为人所迫,临终病重、神志不清时所立的遗嘱也无法律效力,前面引述过的唐代的遗嘱都有今“醒素之时”立下遗嘱“、不是昏沉之语,并是醒苏之言”,就表明这一点。宋代有个案例说,卢公达先过继卢应申为养子,又收养了续弦夫人带来的陈日宣为养子,死后“卢应申、陈日宣各执出公达生前遗嘱”争家产。官府见所出示的两份遗嘱的内容互相矛盾“,皆是公达临终乱命,不可凭信”,不能代表其本意,判令遗嘱作废。同时又“以大义裁之”,废除了卢应申的继立关系,勒令陈日宣归宗,请卢氏的长辈“从公择本宗昭穆相当人,立为公达之后”。等于是由族中长辈代为“命继”,继承家产继立门户了。
第二道手续,是经官府盖印。灵惠遗嘱的见证人押字处有索郎水官和左都督两个官员,这两个人应该是兼有见证人和官方代表的双重身份。在另一份残断的遗嘱原件上,清楚地写着“将此凭呈官”的字样,以及习惯讲的当事人必须遵守,否则罚钱“没官”,都是遗嘱需要呈报官府的反映。宋代明确规定,“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官给公凭”。官府盖印意味着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有“经官投印,可谓合法”之说。由宋代的案例可以知道,必须符合习俗和律令的规定,官府才能批准盖印。在无合法继承人的户绝之家,遗嘱给内外缌麻以上亲(本家侄儿或外甥外孙)的时候,官府盖印之前是要严格审核的。
习惯上也认为,遗嘱“若曰纸上之言,则必呈之官府,以直其事矣”,这样才有得以履行的法律保障。前述曾千钧的遗嘱在亲属签押之后又“经县印押”,后来族人指控该遗嘱是伪造的时候,也说是所盖“县印为私(刻)”。另一个案例说,汪如旦的遗嘱也曾“经官府除附给据,付(被遗嘱人)庆安收执”保存;寡妇余氏的继产遗嘱发生纠纷的时候,官府认定其不合法的主要依据也是“设果有遗嘱,便合经官印押,执出为照”,而余氏的遗嘱却没有经过这样手续;何烈的遗嘱被判为无效的原因,也是其“不曾经官印押,岂可用私家之故纸而乱公朝之明法乎”?并且,官府鉴别遗嘱真伪的时候不仅要求“印同”,还必须“印之年月并同”,方可凭信。
官府审核盖印,是为了防止日后争讼,同时也是想通过监督订立遗嘱的过程和限制遗嘱财产的数量,来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