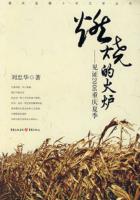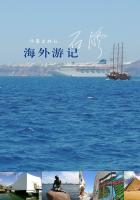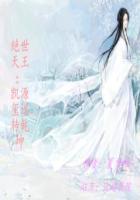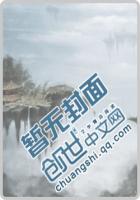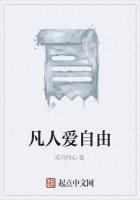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做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做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曾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做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梭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