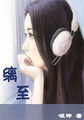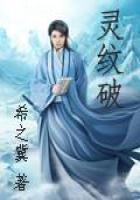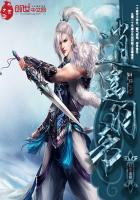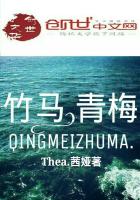《新建设》一九五七年二月号,发表了高尔太的《论美》
一文,我读过以后,觉得有一些疑问,特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作者说:“有没有客观的美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客观的美并不存在。”我说,当我们欣赏一个美的对象的时候,譬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美的,”这话的涵义,是肯定了这朵花具有美的特性,价值,和它具有红的颜色一样。这是对于一个客观事物的判断,并不是对于我的主观感觉或主观感情的判断。这判断,表白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我听说,某一歌舞场面(艺术美)很美时,我会不惜辛苦地去排几小时队,花钱买票,目的是要去亲眼看见那客观存在的美的对象。这个客观存在的美的对象,丰富了我的心灵,充实了我的生活。我把这个新获得的、原来我没有的东西——这次的美的认识——带回家来,可以夸耀于那些没有看到这歌舞的朋友,这美的对象对于我这鉴赏美的主观心灵,是百分之百的客观事实,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要忘了自己,才能充分占有它,否则,我也不会费力费钱,去获得它了。这种美,可以许无数的人同时占有,不像一块面包,只能极少数的人占有,这是它的普遍性特点。
歌德在他中年的时候,摆脱了他的一切事务,悄悄地“逃往”意大利,去认识和研究古典的美。对于歌德,古典的美的型范,是在意大利客观地存在着,他不去是无法亲自接受、占有它的。他占有了之后,写出他的名剧《伊菲吉利》,是德国文学中最具有古典美的杰作。你若对歌德说,古典美只是你的心理过程,歌德一定瞠目不解。他一定对我们把手指向罗马。
米开朗吉罗和贝多芬,一生吃的苦,费的力是大极了,是惊人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美!为的是那对他们自己和对我们都客观地存在着的美,永恒不朽的美。
科学家(心理学家),先肯定了美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后研究这美的对象被人们接受吸收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分析这“美的对象”的内容和结构(如和谐等等),然后,美学才建立了起来。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着美,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研究美学,国家也不能提倡美育,设立美术馆。提倡美育,就是培养人民对客观存在着的美的对象,能够接受和正确认识,像科学那样培养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真理有正确的认识一样。
至于人们欣赏美的事物时必须具备着主观方面的心理条件,如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想象力的活动和情绪活动,甚至于在看戏时还要带望远镜,这就同人们对物理现象做科学研究时也要具备的心理条件(如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想象力、情绪活动须收敛些,而求知意志须坚强些)一样,有时也用显微镜、望远镜等器械,但人们不能因此就说“物理现象”就是“感觉的复合”、“心理的过程”(马赫曾有此谬论,已被列宁据理驳斥掉了)。
作者否定了美的客观存在,但他在下面几句话,似乎又肯定了美的客观存在。
作者说:“我们爱大自然,就因为大自然的美。我们爱某人,如果不是因为那人的外貌是美的,便是因为那人的灵魂是美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某人的外貌,或者灵魂是美的时候,我们便会爱某人。”这几句话,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它是和作者前面开宗明义的话,自相矛盾了。这里,作者显然承认大自然自身是美的,或具有美的性质的,客观地存在着美。否认这个,可贵的“爱”岂不落空了吗?
作者这篇文章里,逻辑性是不够强的。
但是,作者忽然又把爱“美”转化为爱“善”,并且,坚决地主张爱“善”正是“美”。他说:“美如果离开了善与爱,便无法获得自己的意义”。又说:“善与爱的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因为只有它适用于一切场合。”
美的“自己的意义”就是爱“善”。那么,美学应该划归到伦理学的范围了?
如果说,爱“善”就美,就是“美的基本法则”,那么,伦理学就该划归到美学范围里去了?
怎么办?
关于艺术和美的关系,作者有下面几句话:“事实上,艺术在创造着美;这美不是在艺术家的劳动过程中,而是在读者受到感动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旁点是我加的)。上半句话说:“艺术在创造着美”;下半句话说:“美是在读者受到感动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创造”和“劳动过程”、“产生”的分别在哪里!?
原载《新建设》195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