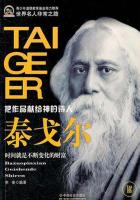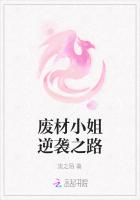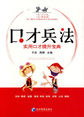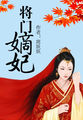待得最后一轮战罢,李义庭与何顺安同积26分并列第一。按照当时的规则,先看双方对赛成绩,再看用时多寡——第四轮两人弈成平手不过李义庭用时更少,冠军属于李义庭!何顺安虽然是本届比赛惟一一位保持不败的棋手,但他只能屈居亚军;杨官璘则位列第三。
这也是何顺安距离棋王宝座最近的一次,此后他再也无力染指桂冠。一局戏剧性的“捉放曹”,李何二人从此棋坛之上地位悬殊,令人唏嘘。
20岁即加冕棋王,李义庭如同慧星般闪耀中国棋坛。1959年他又获得亚军,1962年再夺季军。李义庭可以在残局争斗中战胜内功高深的杨官璘,也可以在激烈的对攻中战胜棋风刚猛的王嘉良。在文革前,“李氏快刀”堪称弈林之中头号利器。
一代棋杰伤离别
1958年夺得全国冠军之后,李义庭成为湖北省体委的一名干部。苦出身的他,对于这份工作倍加珍惜,感情深厚。
1959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举办,象棋也是正式比赛项目之一。作为新科冠军,李义庭憋足了劲,要在全运会上争取好成绩。
9月全运会象棋比赛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官开战。预赛李义庭下得磕磕绊绊,先是被甘肃老将武延福逼和,而后又败给河北棋手王家元。不过杀入决赛后李义庭抖擞精神,积分与杨官璘、王嘉良等人一直咬得很紧。
倒数第二轮他与王嘉良激战成和,赛后两人的对局被推选为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最好一局棋”。作为评委的谢侠逊、陈松顺等5位棋坛名宿评论:这局棋布局新颖、不落常套,双方在互求复杂的变化中,寻找胜利的可能;中局着法紧凑,拼杀猛烈,一方弃子夺先,棋局上几度出现惊骇险恶、扣人心弦、变化极其繁复的场面;双方在残局阶段,经过深谋远虑,反复推敲,终于化险为夷,杀罢成和。总的说来,双方在这局棋中走出了不少妙着,基本上未出错漏。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解放10年来中国象棋技术水平的发展成果。
最后一轮较量,李义庭与杨官璘正面厮杀也战成平手。杨官璘最终以5胜2和的战绩成为首届全运会象棋冠军,李义庭与王嘉良同样是3胜4和并列亚军。
虽然只是一个全运会亚军,但其含金量明显比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更高。回汉之后,李义庭的月工资调到了66.5元,与当时中南地区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一样高。后来,又涨到了令人艳羡的80多元。1960年全国评高级知识分子,湖北省体育系统只有两人入围,李义庭名列其中。同年他还被推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象棋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各项活动都停顿下来。1969年李义庭被下放到位于荆州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才回到武汉。这期间他再也没有摸过棋。
1974年,中断8年之久的全国象棋锦标赛在成都恢复举行,杨官璘等众多名家共襄盛举,然而36岁的李义庭却令人意外地选择了“封棋”,从此告别赛场。
差不多30年之后,已年过花甲的李义庭一次去广东顺德参加象棋联谊活动,讲述了当年决意退出棋坛的真实原因。他表示退出与政治因素无关:“当年我的确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我不下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身体原因。当时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比赛后常常睡不着觉,难以适应时间长达半个月的全国个人赛。这种身体状况使我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受感情因素的影响。当年我从干校返回武汉,湖北省体委不肯接收我,后来是武汉市体委安排了我的工作。当时参加全国比赛,只能以省的名义,所以我一气之下,也不愿再为他们‘卖命’了。”
不再与天下英雄一争长短,挂印封金的李义庭从台前退至幕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提携青少年棋手以及组织操办棋艺活动之上。
1974年的全国棋类锦标赛李义庭虽然没有参加,但却主持了湖北省参赛棋手的选拔工作。后来名震棋坛的“东方电脑”柳大华,当时还是一位24岁的下放知青,是李义庭力排众议,让其代表湖北参赛。虽然初出茅庐的柳大华最终连决赛都未能打进,但经过这次全国大赛的洗礼,他的收获很大,很快便成长起来。1980年更是夺得全国象棋锦标赛冠军,打破了胡荣华的“十连霸”。
谈起这段往事,柳大华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李义庭虽与自己没有师徒之谊但却有提携之恩。如果不是当年李力排众议让自己出战全国赛,“今天的柳大华还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湖北武汉,如柳大华这般因着李义庭的教诲、提携而成长起来的著名棋手还有很多。“封刀”之后,他仍然为棋类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棋坛慧星”,从未陨落。(作者:邹谨)
△柳大华——“东方电脑”
“除非身体状况不允许,抑或棋盘之上已力不从心,否则我绝不会离开赛场。”60岁生日当天,被誉为“东方电脑”的象棋特级大师柳大华直抒胸臆,掷地有声。原来在“东方电脑”的字典里,还没有“关机”这个字眼儿。
一件棉袄,永远的温暖
1950年3月3日,伴随着元宵节的爆竹声,柳大华呱呱落地。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大中和大昌。
解放前做过湖北省田粮处处长的父亲柳文生,此时并没有固定工作,靠打散工维持生计,一家人租住在汉正街徽州巷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好在柳文生高大魁梧,有一把子力气,1952年他在汉口流通巷码头(现集稼嘴码头附近)助勤大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当上了搬运工,家里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然而好景不长,有着所谓“历史问题”的柳文生,不断地受到冲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之后,情况尤甚。1958年9月,不堪受辱的柳文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妻儿,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这个时候,柳大华的小妹已经出生。没有了父亲,一家5口的生活陷入绝境。一直做家庭妇女的柳母段守贤,想尽办法在一家街办小厂找到了工作,全家艰难度日。
为了给母亲分忧,大哥大中领着两个弟弟课余在家里糊火柴盒,贴补家用。糊1000个可得4角8分钱,一月所赚不过10元,但是对柳家三兄弟而言,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按照当时的政策,像柳家这种困难家庭,孩子就读可以减免学费,但是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他们一直被打入另册,补助之事也根本无从提起。
初中二年级,柳大华遇上了班主任周芸老师。周老师当时年近5旬,对待学生就像慈爱的母亲。在她的力争之下,柳大华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补助——一件新棉袄。
“接过棉袄的时候,我只想哭。”50年之后,谈起那份特殊的礼物,柳大华仍刻骨铭心,“面料很滑、很软,特别暖和,我穿了很多年。我永远忘不了老师。”
棋书作伴,自学成大器
柳大华学象棋,大哥柳大中是引路人。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中学的大中迷上了象棋。从柳家到学校,必经江汉桥。桥下有一位高老爹,十几副棋盘摆着一个棋摊,大中便是这里的常客。一天放学回家,他偶然间在棋摊上发现了广州出版的《象棋》月刊,一角钱一本,翻看之下如获至宝,遂咬牙买了下来。正是这本杂志,让大华和二哥大昌领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回家之后,大哥手捧棋书比比划划,那副如痴如醉的样子让两位弟弟很是好奇——有这么好玩?!我们也要学。从此,三兄弟都迷上了象棋。放学回家先做功课再糊纸盒,任务完成就直奔高老爹的棋摊,杀个天昏地暗。
与热衷于实战的其他少年不同,柳大华从一开始就对打谱情有独钟。看棋书学理论,用棋谱指导实战,独树一帜的习弈之道,帮助其技艺飞涨。
虽然没有名师指导,但是三兄弟很快就闯出了名头,成为棋摊上的霸主,人送绰号“柳氏三雄”。当时在棋摊上下一盘棋要交两分钱,一般由负者掏腰包。高老爹见三兄弟棋力出众且忠厚老实,便免了他们的对局费,从此小哥仨下棋就更来劲了。
9岁、10岁大小的孩子,连环画是他们的最爱。不过对于柳大华来说,棋书的地位至高无上。他读谱的劲头越来越大,不仅上学、放学的路上看,晚上躺在床上也是手不释卷。由于用眼过度,他的视力急速下降,左眼一度只有0.3。
棋摊征战无敌手,柳大华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当时汉阳工人文化宫是武汉棋界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在一位叶姓棋友的带领下,他开始转移阵地。汉阳工人文化宫每晚都有名手挂大棋盘应众表演,最初大华的任务是帮名手大盘摆棋,这也是一件很露脸的事情,同时还可以学上几招,他很是高兴。渐渐地,大华也有机会做应众表演,一来二去,名声不胫而走。
总结自己的成长之路,柳大华曾言:棋书是我最好的老师。他讲过这样一段往事:1966年6月,文革大搜家浪潮初起,为了避免自己的宝贝们被抄走,他将一大旅行袋的棋书藏到了好友余昌晋的家中。“我们家成分不好,而且我的目标太大,别人都知道我家棋书多。余昌晋跟我关系很好,更重要的是他家家庭成分好。”柳大华回忆。
母子情深,灯芯绒兄弟
声誉鹊起的“柳氏三雄”,足迹开始遍踏武汉棋界各大活动场所。从汉阳工人文化宫到硚口工人文化宫再到民众乐园,三兄弟所到之处,别具一格的“组团”表演备受瞩目。
1963年6月初,硚口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象棋晚会,内容包括闭目棋、双打、一对五、老对少、名手表演等,其中“柳氏三雄”的应众打擂表演赛“过三关”,最受欢迎。年仅13岁的柳大华把守第一关,第二关柳大昌,第三关柳大中。事先规定,连闯三关者即可获奖。然而连续8人上场,都败在大华的手下。众人哗然:“柳老三好厉害!第一关都攻不下来,奖品太难拿了!”
事后,《武汉晚报》载文称:“本周末晚上,在硚口工人文化宫里举办了一次别致的象棋赛,吸引观众达五六百人之多……逗人兴趣的是‘闯三关’,由柳大中、柳大昌、柳大华三兄弟把关。年仅13岁的柳老三把守第一关,未让对手越雷池一步全胜而归。”
对于三兄弟下象棋,柳母最初并不赞成。然而她渐渐发现,学棋之后儿子们懂事多了。有一件事,尤其让她感动。
一天晚上,三兄弟去文化宫参加象棋表演赛。结束后主办单位每人发了一包点心,哥仨谁也没舍得吃,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妈,你吃吧,这是我们下棋挣的点心。”妈妈从每个包里拣出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吃得格外香甜。
柳家素来贫寒,那个时候三兄弟身上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很不体面。儿子们穿成这样,怎么能在大家面前表演呢?柳妈妈下定决心,要给孩子们置一套像样的衣服。省吃俭用,她攒下30多元买了几米蓝色灯芯绒布料,一人做了套衣服。
这之后,每当外出表演,哥仨就格外地引人注目。大家都说:“蓝灯芯绒兄弟,棋下得好厉害!”
学习国象,大华险改行
1963年5月,柳大华代表硚口参加了武汉市少年比赛。不过象棋生涯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他打得并不理想,只获得第三名,赛后很失落。好在有大哥大中开解,他很快走出阴影,对自己在市赛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反省、总结。
同年7月,柳大华代表武汉参加湖北省少年象棋赛,以3胜3和的不败战绩拿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半月之后,他又代表湖北出征中南地区少年象棋赛,2胜2和屈居亚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广东棋手李广流的争冠之战,对局质量备受称赞,事后经李义庭、陈培芳等名家评注,棋谱登上了1963年第10期的《象棋》月刊。这让年仅13岁的大华很是自豪,也进一步坚定其学棋的信心——我就是下棋这块料。
中南地区少年赛之后,野路子出身的柳大华终于有了正规学棋的机会,他与二哥柳大昌一起,成为武汉体育馆青少年业余体校的正式学员,师从刘成万,每星期有3个晚上训练。不过兄弟俩学的不是象棋,而是国际象棋。
对于这次“改行”,柳大华后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是兄弟几个一直渴望有正规的场所和老师可以去学棋;二来刘教练对自己和二哥青睐有加;更重要的是,国际象棋当时在中国刚刚起步,“容易学出名堂”。如今看来,这最后一条颇有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意思。
国际象棋在兵种、走法、战术手段、战略思想等诸多方面,都与象棋有着共通之处。凭借多年练就的象棋功底,大华兄弟很快就展现了过人的天赋与悟性,他俩突飞猛进的棋艺也令教练刘成万大呼意外。
学习国际象棋的日子里,柳大华也没有放下象棋,一有闲暇便四处找高手切磋,不时还进行公开表演。“两条腿走路”的相互印证之中,他的棋艺境界又有提高。
可惜幸福的时光太过短暂,两年之后刘成万因故离开武汉体育馆,他所执教的国际象棋训练班也随之成为历史。
贵人相助,走上专业路
在柳大华眼里,一代棋王李义庭是自己走上象棋专业之路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初遇李义庭是在1962年的某个周六晚上。当是时,李义庭虽然只有24岁,但已经拿过全国冠军,贵为棋王;而柳大华尚是一个怀有追星情结的12岁少年。那晚在民众乐园看名手表演赛,棋刚开始下,有人一捅柳大华:“李义庭也来观战了。”大华很是激动:“在哪里?在哪里?”那人说:“最后一排。”
就这样,柳大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崇拜的大国手,一位文静而又神秘的年轻人。
4年之后,1966年的正月初一,在硚口区文化馆,柳大华终于有机会与自己的偶像对坐手谈。一向乐于提携后进的李义庭,面对少年郎弈来仍兢兢业业,最终双方战成平手。半月之后的正月十五,柳大华16岁生日这一天,两人于同一地点再次进行公开表演赛,仍旧平分秋色。此番交手,也为日后李力荐柳参加全国比赛埋下了伏笔。
柳大华中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1968年12月底,他去安陆农村插队。沉重的随身背包中,没有多少日用品,几十本棋书和一副象棋唱了主角。插队的日子里,白天干活就在脑子里自己跟自己下棋,如同放电影;晚上油灯下,则是不停地读棋书、拆棋,从不懈怠。反反复复地研究,到后来那几十本棋书几乎全都可以背下来。
由于高超棋艺传遍四里八乡,柳大华得到了特别的礼遇。隔上一段时间,他就要请假回武汉找高手交流,而生产队里总是网开一面,不加干涉。
经过数年的停顿,象棋活动逐渐在国内解冻。1974年,有关方面决定恢复举办全国棋类比赛。由于当时还属于下放知识青年,武汉市的选拔赛柳大华没有资格参加,只能作壁上观。不过在确定湖北省参赛人选时,主持选拔工作的李义庭相中了他。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柳大华连市赛都没有资格参加,全国赛就更是师出无名。不过李义庭坚持认为,柳大华是省内公认的强手,人又年轻,有发展前途,应该让他去锻炼。
就这样,李义庭力排众议,把柳大华从湖北推向了全国。而柳大华也借此机会,一步一步走上专业之路。
另类加油,棋王终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