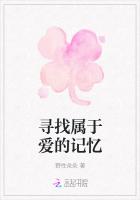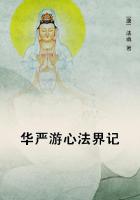汉正街和汉水边的码头是鹿宁坤和柳翻译经常逛的地方。他们俩为什么喜欢逛汉正街?因为英租界刚开一年多,租界里除了几栋小洋楼就是江边的洋行和仓库,几乎没什么娱乐设施,即便有,也不对华人开放。汉正街就不一样,汉正街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明朝的时候,整个汉口镇就是汉正街,以及与汉正街平行的汉水码头这一带。当时,汉口镇与河南的朱仙镇、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被称为‘中国四大名镇’。鹿宁坤和柳翻译逛汉正街,不是因为它古老,而是因为它繁华,这里吃的、喝的、玩的、逛的应有尽有。
鹿宁坤在扬州长大,扬州也算是个有名的大城市,来汉口的路上,鹿宁坤也到过上海,上海在他眼里,可以说相当繁华。但是到了汉正街,鹿宁坤还是被汉正街密集的街巷、繁华的码头惊呆了。汉正街里商铺、会馆、庙宇、茶馆、酒楼星罗棋布,热闹非凡。叶开泰、汪玉霞、谦祥益、谈炎记等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宝庆会馆、江西会馆、山陕(山西陕西)会馆、新安书院(徽州会馆),各个地方的会馆好几百家,数都数不清楚。还有许多寺庙,什么大王庙、西来庵、龙王庙、四官殿、药王庙、西关帝庙等,有些庙宇是庙宇与会馆合二为一。庙宇中西关帝庙最为宏大,它也是山陕会馆,前些年太平军占领汉口时还做过天王府,可惜太平军走时一把火烧毁。至于茶馆酒楼就多得根本没法数。
汉正街两边有许多巷子,什么永宁巷、流通巷、万安巷、竹牌巷,五彩巷,小新巷、大火巷、小水巷、淮盐巷等等,靠汉水那边的巷子,每一条巷子都直通码头,每一条巷子都是一种乃至多种货物的集散地。流通巷直通流通巷码头,主要装卸食用油与皮油;萧家巷直通萧家巷码头,主要装卸江西的瓷器;药帮巷直通沈家庙码头,主要装卸中药材;小新巷直通小新码头,主要装卸各种水果。至于汉水边的码头,起码有上百个,什么杨家河码头、石码头、老水巷码头、三圣码头、新茂巷码头、五彩巷码头、彭家巷码头、大硚口码头、小硚口码头、利济码头、大王庙码头、五显庙码头、沈家庙码头、大新码头、关圣祠码头、鸡窝巷码头、接驾嘴(集家嘴)码头、宝庆码头、龙王庙码头,延绵好几里地。
当然,最吸引鹿宁坤和柳翻译的还是这里众多的小吃和茶馆。汉正街里有许多走街串巷的提篮小贩和挑担子的挑贩,有卖饼子和油条的,那一尺多长的油条别提多爱人;有卖麻花的,那一根根铅笔大小的麻花,香脆酥松;有卖凉粉凉面的,那晶莹洁白的凉粉,油光锃黄的银丝凉面,光看一看挑子里的佐料就令人口水欲滴,什么酱油呀,麻油呀,辣椒油呀,芝麻酱呀,姜汁呀,蒜水呀,虾米呀,蜇皮呀什么的;特别是卖“清炖冰糖莲子汤”的,和卖“桂花赤豆汤”的,鹿宁坤看到后非喝上一碗才走,这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下江人,对甜食特别感兴趣。
除了这些挑担小贩,汉正街还有固定的小吃铺子,有狗肉巷的豆丝、大通巷的馓子、还有祖师殿的汤圆等等。祖师殿的汤圆也是鹿宁坤最爱吃的,每次到这里他总要来上一碗猪油黑芝麻馅的,他总是边吃边说,这里的汤圆一点也不比宁波汤圆差。再就是谈炎记的水饺,那是柳翻译最爱吃的,柳翻译总是用汤匙舀起一个水饺对鹿宁坤说:哎!你看这皮,薄得跟纸似的;再看这馅,鼓得跟核桃似的;还有这汤,是纯正的的牛骨头熬出来的,汤色奶白奶白的,汤里还有紫菜、虾皮,哎,这才是纯正的水饺哇!两人口味一致的,就属“杨豆皮”了,挑开那面上一层金黄焦脆的蛋皮,里面露出鲜嫩的竹笋、酱红的牛肉和油亮的糯米,吃上一口,别提有多美。
吃够了小吃,两人再找个茶馆,往里面一坐,沏壶好茶,就闭上眼睛听一段正宗的黄陂花鼓戏,那滋味,别提了。黄陂花鼓戏虽然不是鹿宁坤的家乡戏,不过没关系,只要是戏,他都爱听。要是不想听戏,他们就找个说书的茶馆听上一段,什么“关公温酒斩华雄”呀,“秦琼背运卖宝马”呀。到了下午,再在茶馆里泡个澡,往大水池子里一跳,泡上半个钟头,两人边泡边聊,把浑身泡得通红,再叫个搓澡的来搓背,真是太过瘾了。
鹿宁坤和柳翻译来到集家嘴。站在江边,看着汉水从眼前流过,在不远处的龙王庙与长江相会,清澈的汉水涌入浑黄的长江,就像一条青龙和一条黄龙翻滚着绞缠在一起,然后再一起奔向浩瀚的大海。汉水江面上,烟波浩淼、万帆林立,江对岸的龟山尤如一只万年的镇江老龟,忠心耿耿地镇守在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
“哎,你说!为什么有人把这里叫集家嘴,有的人又叫接驾嘴?”柳翻译看着眼前的江滩问。
“你这半个洋人,当然不知道!”鹿宁坤笑着说。然后他告诉柳翻译,明朝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为没有儿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兴王朱厚熜(cōng)继位,为世宗皇帝,年号嘉靖。兴王的封地位于湖北的承天府,是明朝三大府之一,兴王朱厚熜当上皇帝后,就把他原先的封地赐名为钟祥。当年兴王朱厚熜从钟祥出发,到北京去继承皇位,中途就经过这个渡口。因此,当地的百姓就称这个渡口为“接驾嘴”。大清国开国后,当地的官员觉得这个名字不妥当,在大清国接明朝皇帝的驾,有“反清复明”之嫌。于是把“接驾嘴”改成“集家嘴”——集天下万家之船。这样一来,有的人管这里叫“集家嘴”,有的还是叫“接驾嘴”。
“鹿帮办,你还懂得真多。”柳翻译称赞道。
“那当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嘛!”
正说着,不远处的宝庆码头突然骚乱起来,鹿宁坤顺着吵闹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的江面上停着几只大帆船,帆船上围着一大群人。
“哎,打码头了!”柳翻译朝宝庆码头一指。
汉水沿岸的码头,每个码头都有一个大头佬带着一帮码头夫,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个大头佬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别人涉足。码头上经常有越界行为,从而引起两帮码头夫械斗,通常是几十人上百人拿着扁担撬杠打斗在一起,有时还会出人命。打码头最利害的就是宝庆帮和徽帮,两帮为宝庆码头争夺了差不多一百年,最后一场械斗是在1856年,那一场械斗整整打了一天,码头上血流成河,双方死伤许多人,最后宝庆帮在曾国藩的弟弟、湘军将领曾国荃的撑腰下,才把徽帮赶出宝庆码头。
“快过去看看。”鹿宁坤说着,就和柳翻译快步朝那边走去。
今天,宝庆码头不是打码头,而是江汉关关差和一伙茶商发生了冲突。宝庆码头前面的帆船上围了不少人,中间有三个江汉关关差准备捉拿一个年轻人,被那个年轻人三拳二脚打翻在地。三个关差一看不是年轻人的对手,就留下两个关差看住年轻人,派一个关差上岸去喊人。没过一会儿,陶大勇带着七八个关差赶到帆船上,这时候船上的和岸上的码头夫们看到有人闹事,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围拢过来看热闹,一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人呢?”陶大勇问留在船上的差役。
“就是他!”差役一指年轻人。
陶大勇左手一叉腰右手猛一挥,大喝一声:“拿下!”
接到命令,四个关差朝年轻人扑去。一个关差上去就扭年轻人的胳膊,年轻人后撤半步,左手拨开关差的手,右手一掌击在关差的胸前,把那个关差打飞出去。另一个关差从另一边扑了过来,一拳直朝年轻人的太阳穴打去,年轻人侧身让过,右手往打来的手腕上一扣,一个顺手牵羊,将这个关差带飞出去。另外两个关差一看,同时拔出刀来,一个直奔年轻人的脖子砍去,一个直朝年轻人的小腿削去。只见年轻人一跃而起,让过脚下的刀,飞起一脚,踢飞了上面砍来的刀,然后在空中连踹两脚,踹在两个关差的脸上。只听两声惨叫,那两个关差像两个木桩,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好!”
“太精彩了!”
码头夫们一片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