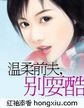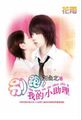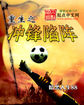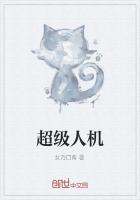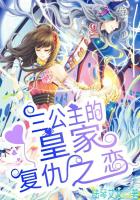1966年,深冬。
天寒地冻,朔风阵阵。校园内各个锅炉房的大烟囱懒洋洋地吐着淡淡的青烟。
四清运动结束后,李祥君和同学们从农村返回学院,参加了在俱乐部礼堂召开的全体员工和学员大会。会上,院领导奉命给全体师生员工作学院改制的思想动员。
就在李祥君和同学们在海伦农村搞“四清”时,1966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向****中央报告:拟将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脱离军队编制,改为地方院校,仍归国防科委领导。两天后,****中央将军委的报告批转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北方军工学院一向令行禁止,模范执行中央指示,这次也不例外。动员会上,院领导要求大家正确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服从革命需要,听从党的安排;穿军装是干革命,不穿军装也要干革命;改体制不减斗志,脱军装不丢传统;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生交给党安排。院领导洋洋洒洒讲个没完,下面听报告的干部和学员有的交头接耳开小会,有的神不守舍,直着两眼想心事。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会后,学员们带着种种思想情绪,心情沉重地拎起行李回家过寒假。北国的寒风严酷逼人,冷清寥落的大操场上空无一人。整个军工大院空空荡荡,一下子没了往昔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李祥君带着参加四个多月“四清”运动的疲惫和被迫转业的失落情绪,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老家。见到亲人和心爱的颂兰时,他心中的思念和委屈一下子找到了出口,眼泪夺眶而出。亲人们竭力安慰他,说不穿军装没关系,大学生的身份没变,将来国家总会安排工作,给一个饭碗,旱涝保收。李祥君对亲人的善意心怀感激。但是,对于满怀雄心壮志的二十出头的青年来说,“饭碗”对他的吸引力很小,不足以让他得到宽慰。
冯颂兰拉着李祥君的手说:“这是中央的决定,又不是你犯了什么错误才让你转业;这是学校改制,又不是让你退学,你没有必要伤心。今后我们都是地方院校了,平等了,你们那个‘两不准’也该取消了吧?”
祥君抱紧颂兰,开玩笑地说:“怎么?你等不及要结婚啦?那可不一定哟!我们虽然都是地方院校,但我们学院仍属国防科委管,纪律严明。我们都年轻,还没有立业,还在靠人养活。我们一定要能自食其力后再考虑结婚。我要发奋学习技术,将来多多赚钱,好让你过一辈子好日子。”
颂兰挣脱祥君的怀抱,生气地说:“瞎说什么呢?我哪有催你结婚的意思?我在安慰你,懂吗?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先立业后成家吗?我们应该利用在校这几年的宝贵时光多学些本领,将来一辈子受用。”
祥君连忙赔礼道歉,把她又紧紧地抱在怀中。
在以后一段日子里,他们常在一起聊天,畅想未来。很快春节过去了,他们依依不舍地分别,各自回到学校。
新学期开学后,工程学院由供给制改为助学金制,以学员班为单位评定人民助学金。由于学员中家庭条件好的比较多,评助学金的时候既实事求是又发扬风格,结果李祥君和其他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员获得了较多的助学金,基本上能满足日常生活和学习的需要。
那些日子,很多人都去照相,集体留念,或欢送队干部转业。军人服务社的照相部门庭若市,从早到晚熙熙攘攘。李祥君也照了几张作留念,让一身戎装定格。军工人对部队的深厚感情是刻骨铭心的。
春寒料峭,春雪凝素。4月1日那天,全院上下一齐摘掉帽徽和领章,并把它们珍藏起来。此后,大家走在路上,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不自觉地看一眼对方的帽子和棉衣领口,那上面还有帽徽和领章留下的印迹。大家相见都苦笑着,一脸无奈,或者说点转移情绪的话。那几天,在被窝里偷偷淌眼泪的学员也不在少数。谁都明白,“北方军工”成了历史名词,同学们都不再是革命军人,内心难免伤感惆怅。
此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越来越猛。5月份,学校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5月11日,学院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停课两周搞运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晚上,李祥君和同学们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翌日,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7月25日,省委宣布院长退出院文革领导小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8月6日,北方军工学院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和红卫兵组织。8月8日晚,****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北方军工学院“八八团”成立。
军工学院从5月11日停课搞运动之后,一直没有再上课。李祥君每天都学时事和理论,听广播,看各种报刊上刊登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报道。他到学院俱乐部看大字报,了解中央指示和北京消息,思索着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很多事情他想不明白。他是贫寒的农家孩子,父母给他的影响是勤奋克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家乡的恩师给他的教育和激励是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离开农村,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没有灵敏的政治嗅觉,也缺乏对社会活动的兴趣。他天资再聪颖,学习能力再强,从根本上说也只是一个书呆子。他性格固执,没有弄明白的事一定不会贸然参与。因此,虽然军工成立了对立的两派,他却一派都不参加,想当个逍遥派。李祥君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会,用看书和装配收音机来打发时间。
9月5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此后,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红卫兵们如潮水般涌进每一节火车,纷纷进京闹革命。
李祥君在形势的影响下,觉得校园里根本没有安静的角落让他读书。此时造反团来争取李祥君加入,他便答应了。他们马上发给他一个红卫兵袖套。李祥君便凭着这只红袖套去南方大学见冯颂兰。
南方大学也是一片混乱,学校停课,大字报、大辩论到处都是。大部分学生都出去串联了,学校空荡荡的。在寻找冯颂兰的时候,李祥君走在安静的路上,突然觉得这里不是他想象中的大学,更不是他心爱的恋人生活学习的地方。他问了几个人,终于找到冯颂兰的宿舍。
颂兰和祥君一起到学校食堂吃过晚饭后,她给祥君找了一间男生宿舍安排好晚上的住宿。然后,他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走累了就坐在一个僻静角落的长凳上聊天。他们已有近10个月没见面了,有很多话要说。李祥君介绍了学校的现状,以及对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言语中颇多疑惑不解,情绪消沉。颂兰说,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全部打乱,这样下去很可怕。祥君仔细考虑颂兰的话,内心也有同感。他担心颂兰的安全,劝她少说少动,多看多听。颂兰沉默片刻,说她很少和同学接触,更不会跟任何人深谈,让他不必担心。他觉得颂兰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呢?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
李祥君在南方大学住了几天后返回自己的学校。这时,他离开学校已经快一个月了。他本想寻找真相和真理,结果心力交瘁又疑惑迷茫。他想,不如回到学校静一静,好好想一想近阶段的事。
李祥君和冯颂兰分别时,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此后一直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