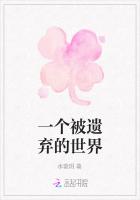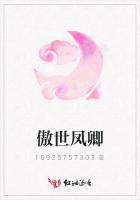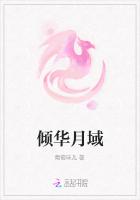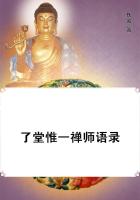整死了长沙王司马乂,最得意地要算成都王司马颖了和东海王司马越了,两人都占尽便宜,司马颖“诏以为丞相”,司马越则为尚书令。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成都王司马颖派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并废除齐王司马冏所立皇太子司马覃为清河王。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颙屡为刘枕所败,非常苦恼,先向司马颖送乖卖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朝廷“诏从之”后,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颙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了这位雍州刺史。时局刚刚安定,成都王司马颖被胜利冲昏头脑,“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早有“司马昭之心”了,看见司马颖“大失众望”,还以为自己颇得民意,就于永兴元年(304)秋天,率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
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乂“奉帝北征”,鼓动傻皇帝司马衷御驾亲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成都王司马颖的老巢——邺城。留在洛阳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见势不妙,逃回邺城,还没有喘口气,司马颖就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双方在河南汤阴相遇,为了戴罪立功,石超豁出去了,他以排山倒海之势大败司马越。混乱之中,司马越大败而归,连皇帝也丢了,但司马颖并不想伤害晋惠帝司马衷,他也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他手下的兵痞不管那么多,结果司马衷车倒草中,脸上也中了一刀,身受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唯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这才保住这位傻皇帝的一条命,当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时,惠帝高喊:“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于是,嵇绍“血溅帝衣”,死在乱刃之下,不久,司马颖派自己的高参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号啕大哭的晋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晋惠帝默然醒悟,大恸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看见哥哥兵败,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和王浚联合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的部落骑兵,南攻邺城,司马颖又派王超等人继续战斗,希望以战胜之威,再创佳绩,但司马腾的联合部队特别是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天下。王超等人连连败绩,“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高参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做护卫还绰绰有余,但司马颖的生母程太妃眷恋故乡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一万五千余大军见主帅无谋,一哄而散,“俄而众溃”,司马颖和卢志只好带数十骑拥着傻皇帝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一路奔逃,狼狈不堪。逃至邙山,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成都王司马颖这时候终于“虎落平川”,不但威风不再,而且形同软禁,相形之下,张方威风多了,不但动了“挟天子”的心思,而且还要“奉帝迁都长安”,晋惠帝被折腾得够呛,不愿再东奔西跑四处颠簸了。张方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其上车,“帝垂泣从之”,附带还有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河间王司马颙暂时成为西晋王朝最高负责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七月,吃完败仗,休整了一年多的东海王司马越终于缓过气来,他蠢蠢欲动,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颙“劫颙车驾”为名,发檄天下,开始报仇雪恨,成都王司马颖昔日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响应,河间王司马颙“甚惧”,又和被软禁的成都王司马颖“哥俩好”,封其为镇军大将军,还给了他千余兵拥返归河北招抚,成都王司马颖经过此番劫难,早已丧尽昔日统领十万大军的虎威。
看见东海王司马越气吞万里之势,河间王司马颙心生畏惧,他动了想与司马越握手言和的心思,但张方坚决表示反对,他才是“劫驾之罪”的真正主谋,害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河间王司马颙派遣张方的好友郅辅以读信为名,一刀砍下张方的脑袋。司马颙本以为杀了张方,东海王司马越会主动退兵,想不到东海王司马越还是继续西进,走在中途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五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第一个牺牲的就是自己。公元306年5月,几经奋战,东海王司马越终于抢回晋惠帝司马衷,河间王司马颙大败,逃进太白山后,看见长安空虚,又趁机进驻长安。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东海王司马越率领大军进驻洛阳,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封自己的堂兄弟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
这时候,还在外面流浪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已经控制了京城,差点哭了,他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但行至新野,东海王的通缉令已经到了,惶恐之间,也顾不上老母亲和妻子,只和车夫载着两个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召集了数百名部下,准备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司马虓也不想把这位“皇太弟”怎么样,但不巧的是范阳王司马虓忽然暴疾而亡,他手下长史刘舆怕他“死灰复燃”,派人“称诏夜赐颖死”。在最后的时刻,成都王司马颖倒很镇静,有几分英雄气概,读毕“诏书”,还准备洗个热水澡,说道:“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看见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司马颖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沐浴已毕,司马颖“乃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人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其“二子亦死,邺中哀之”。
公元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自己的天下稳了,要不要晋惠帝无所谓,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这位饱经磨难的傻皇帝,时年四十八。惠帝死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司马颙,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司马颙为司徒。河间王司马颙接受诏命后,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远远看见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迎接”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至此,河间王司马颙的人生之路也走到尽头。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东海王司马越终于削平群雄,入朝主政了,拥立怀帝后,他大权独揽,首先干掉晋怀帝的侄子,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死时,年仅十四岁,又杀掉怀帝亲舅舅王延及大臣高韬,驱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也有了“司马昭之心”。
永嘉五年(310),洛阳城外狼烟四起,东海王司马越全身披挂入朝,请伐石勒,还想再立立功以自固,他亲自率领四万精兵出讨,飞檄各州郡征兵,但因为丧失人心,“所征皆不至”。终于忧惧劳顿,又怀疑苟晞等人手持怀帝密诏欲杀自己,兵至项城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一天下来,“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司马越的棺柩也化为灰烬,羯族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并食之”,成为了烧烤人肉军粮。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八王之乱终于结束。
继位布局: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晋武帝具有历史上所有开国之君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气度恢宏、胸怀宽广,他对待昔日的敌人,除剥夺政治权利外,不但未曾加害,在生活方面也可以说尽善尽美,蜀后主刘禅喜欢看文艺晚会,整天沉湎于歌舞表演中,晋武帝就尽量满足他的需求,搞得他“乐不思蜀”;南蛮子孙皓英武过人,尽管残暴淫乱,但做了俘虏,依然有男人的血性之气,司马炎第一次见到他时戏称:“朕设此座已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晋武帝哈哈一笑,不与计较,太子太傅贾充颇不服气,心想,你一个俘虏还牛什么牛,就当众斥责他,咄咄逼人地问:“闻君于南方凿人目、剥人面,此何等刑也?”想不到孙皓一点也不畏惧,他直视贾充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贾充闻言,“默然甚愧,而皓颜色无怍”,因为他正是杀害曹髦的凶手。
太康三年,司马炎在南效行祭祀礼后,兴致不错,便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不假思索,回道:“汉灵帝、汉桓帝”,司马炎大吃一惊,问:“你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刘毅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皆入私门,以此言之,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但晋武帝晚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齐王司马攸因为权高位重,出现了功高震主的端倪,《晋书》记载:“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鈂害怕武帝死后司马攸继承大统,对自己身家地位不利,乘间进谗于晋武帝:“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武帝大惊,问:“为什么?”荀勖回答说:“朝内朝外官员皆归心于齐王,太子怎能得立呢?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假装下诏书让齐王回到其封地,肯定会出现举朝以为不可的局面。”冯鈂在一旁敲边鼓:“陛下遣诸侯归国,也是法律规定的事情,应该从自己的亲人着手。陛下最亲近的莫过于齐王了,他应该首先响应命令离开京城去封地。”
晋武帝觉得有些道理,就宣示诏令,假意又把济南郡划入齐国封地,又封司马攸儿子司马蹇为北海王,诏赠六樇之舞、黄羢朝车等仪物,命齐王司马攸回封地就任。诏下,王浑、王骏、羊琇、王济等一帮大臣果然进谏,以为齐王是至亲王爷,应留京辅政才是。同时,大臣们又抬出司马昭、皇太后等人的遗命,劝说晋武帝收回成命。但武帝一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根本不听,认为“兄弟至亲,今出齐王,是朕家事”,把王浑、王济等人贬放外任。齐王司马攸也很忧惧,他深知荀勖、冯鈂构陷自己,就上书乞求为生母王太后守陵,“帝不许”。眼见催促之国的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司马攸又气又急,病势逐渐加剧,为了查明这位老弟是否装病拖延离京时间,晋武帝不断派御医去齐王府诊视。
御医们终日在皇宫中行走,个个都是人精,揣知武帝心思,回宫后都报称齐王身体好好的。“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真实情况是,齐王的病势一天沉过一天,但催其上道的诏书已经日益严厉,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齐王司马攸生性倔强,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仍然穿戴齐整入宫面辞武帝。“痴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无疾”。晋武帝更怀疑他是装病,兄弟两人各怀心事,握手道别。辞出数日,半路颠覆辛苦的齐王终于支持不住,吐血而亡,年仅三十六岁。晋武帝闻知皇弟死讯,才明悟司马攸不是装病,而是真死。不禁悲从中来,恸哭不已。侍中冯鈂倒也会开导,说:“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现在他自己得病身亡,是社稷之福,陛下您何必如此哀痛呢!”晋武帝马上“收泪而止。”司马攸之子司马冏心里憋屈,伏地痛嚎,哭诉御医耽延了诊治。晋武帝愧疚之下,也顺坡下驴,处死了数位为齐王诊病的御医,籍此也掩饰他自己的过失。
晋武帝在选择辅佐太子的东宫官属上,一改曹魏后期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的状况,不仅配齐官属,而且极重人选。对于东宫主要官职的太子太傅和少傅,“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令诸公为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他任命的官僚大都是其宗亲近支,如荀顗、齐王司马攸,杨珧、汝南王司马亮、石鉴等相继出任太子太傅,任恺、卫瓘等皆曾任过太子少傅,贾充、杨骏亦曾行太子太保。东宫的其它官属,也都是当时的清望之士或名臣之后,如王衍、卫恒、阮浑等,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出任过西晋政权的显要之职。他们到东宫任职,一方面说明东宫官属为清要之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武帝为使惠帝能继承其打下的江山而作出煞费苦心的安排,武帝希图造成一种各方面力量均衡状态,以免大权旁落。但由于惠帝智力不全,完全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最终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导致了各方都无休止地追求最高权力,引起了潜在的矛盾,使得中国历史上进入最混乱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十六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