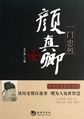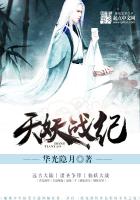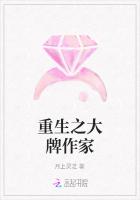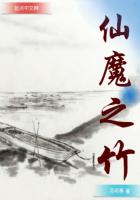洛阳沦陷后,战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叛军开始停滞不前,唐军则从溃败的困境中逐渐走了出来,并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攻陷洛阳以后,连番胜仗使安禄山开始忘乎所以,以为自己的部队是常胜军,竟认为只要小股力量就可攻陷潼关,于是只派崔乾佑进驻陕郡指挥潼关作战,而自己则滞留洛阳城准备称帝事宜。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划,安禄山于756年正月初一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建立起“大燕”政权,自称“雄武皇帝”,任命大臣,委派官吏,俨然一副天子作派。多年夙愿终成现实,安禄山似乎满足了,开始沉湎酒色歌舞,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拼搏进取精神。
安禄山以为凭借着自己的精兵强将,推翻李唐指日可待,否则他也不会急着在洛阳称帝。然而让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部队在潼关这个地方,就面临了一个重大的难题,潼关城久攻不下,战争因而陷入相持阶段。面对这种形势,安禄山忧心忡忡,按照原定作战计划,他们宜速战速决,给唐军一个措手不及,绝非作持久战打算。然而有一个人比安禄山更心急,这个人就是唐玄宗。但是急中所生并非智而是错,且是大错。唐玄宗偏听偏信对作战一无所知的监军边令诚的谗言,认为洛阳失守是由于高仙芝、封常清胆小惧敌造成的恶果,一怒之下,犯了行军打仗的大忌——阵前杀将,将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处死。唐玄宗此举使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这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皇帝斩杀高、封二人后,改派在家休养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是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的后裔,其人骁勇善战,战功彪炳,被称为“常胜将军”。哥舒翰军旅生涯中最光辉的战绩便是收复了石堡城。741年,吐蕃人效仿唐军,用了一个漂亮的突袭,时隔13年,再度夺取了唐朝战略要塞——石堡城。唐玄宗对此事只有一个意见:打!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石堡城!话说石堡城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唐玄宗执著于夺回石堡城,虽然也有出于其重要战略位置因素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唐朝自诩为世界头号强国,吐蕃占领了石堡城,无异于狠狠地扇了唐玄宗一耳光,为了面子,唐玄宗说什么也要夺回石堡城。唐玄宗把夺回石堡城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当时身兼大唐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灵魂人物王忠嗣。王忠嗣认为以石堡城有利的地形优势,夺回石堡城势必要断送上万将士性命,虽然轮不到他这个最高统帅充当炮灰,胜了还能因此加官进爵,但王忠嗣不齿“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的行为,因此并没有好好执行唐玄宗的命令。因为在石堡城问题上的固执,王忠嗣触怒了唐玄宗,加之大奸臣李林甫从中作祟,诬陷王忠嗣卷入了最敏感的“立储风波”,唐玄宗意欲杀王忠嗣,多亏了哥舒翰等军官们苦苦哀求,使王忠嗣免去了死罪,贬为汉东郡太守。前面王忠嗣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里,再也没有人敢忤逆唐玄宗的意愿,哥舒翰被委以重任后,全心全意为出征做准备。749年,哥舒翰率领六万精兵,正式发动了石堡城会战。正如王忠嗣预料的那样,石堡城之战异常惨烈,战斗持续数日,唐军的尸首摞成了山仍未能夺下石堡城。攻不下石堡城,唐玄宗还不得处决了自己以泄愤?逼急了的哥舒翰只能拿攻城先锋官高秀岩、张守瑜开刀,想要杀了二人以提高将士攻城士气。高秀岩、张守瑜恳求宽限三日,如果到期拿不下城,甘心伏罪。唐军不惜一切代价,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死伤数万人之后,终于如期攻下了石堡城。这场战争,唐军以一万多条人命的代价夺取了石堡城,而吐蕃军总数竟然不到六百人。石堡城之战虽然让唐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收复石堡城的积极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大唐以此为契机,全部收复了九曲部落,拆掉了吐蕃东进的跳板,唐军在河西、陇右的战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哥舒翰更是凭借石堡城一战,为唐玄宗所倚重。
为了守住长安的门户——潼关,唐玄宗又在长安城征募了8万余士兵,随哥舒翰前往潼关。面临当前的战争形势,哥舒翰主张:安贼从范阳而来,距离潼关路途遥远,所以宜速战速决。如若拖得时间过长,物资补给供应不上,就会自乱阵脚。我们只需坚壁不出,即可确保潼关万无一失。由于确定了这样一条基本的战略指导思想,哥舒翰一直是以守为上计。
安禄山谋反,世人都认为是杨国忠的逼迫所致,而且安禄山也明确打出了“铲除奸臣杨国忠”的口号,所以哥舒翰的部下王思礼就劝说哥舒翰:“安禄山造反,是以清除杨国忠为借口,我们可以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坚守潼关,率大军前往长安诛杀杨国忠,安禄山的进兵就没了借口。”哥舒翰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办法,但是考虑到安史之乱发生了这么长时间,唐玄宗都没有除去杨国忠的打算,就已明白杨国忠在唐玄宗心目中的地位,自己若率军杀了杨国忠,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最终并没有采纳王思礼的意见。但是,二人的谈话还是传到了杨国忠那里,杨国忠觉得自己生命堪忧,所以积极思考应对策略。此时,潼关在哥舒翰的经营下,固若金汤,叛军主力对潼关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持续半年之久,都劳而无功。而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军接连大败叛军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被张巡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下又被鲁炅阻于南阳(今河南邓州),安禄山腹背受敌,忧心忡忡。当时形势向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各地捷报频传,唐玄宗重拾了必胜的信心,希望赶快结束战乱,稳固自己的地位。杨国忠正好利用唐玄宗求胜心切这一点,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哥舒翰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防止其“西指”长安。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不断派使者催促哥舒翰出城与叛军作战,以致途中的使者“项尾相望”,给哥舒翰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强迫哥舒翰出兵,这是安史之乱唐玄宗指挥作战犯的第二大失误,无异于直接将潼关拱手让给了安禄山。
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哥舒翰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而应战则必败,哥舒翰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哥舒翰无可奈何只得领命出征。出征之前,他捶胸恸哭,既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哀,也是为大唐的安危而痛,全军上下弥漫着一种萧瑟悲情的气氛。哥舒翰率领20万大军在灵宝山西部平原与叛军展开激战。敌军早有准备,在险要地方埋伏,唐军南靠高山,北临黄河,被阻碍在拥挤狭隘的道路上。叛军表面上人数不多,不成阵法。当唐军攻入叛军阵地后,叛军节节败退。唐军见状,拼命追击,却中了敌人的埋伏。唐军顿时乱作一团,相互践踏,伤亡惨重。为了扭转败局,哥舒翰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毯车。毯车是指用毯子将战马全身蒙上,在毯子上画上龙、虎等凶狠的动物,并在它们的眼睛和爪子上都贴上金银,看上去十分恐怖。哥舒翰天真地以为,毯车可以扭转战场不利局面。哪知,安禄山这面早就有所防备,待毯车一进入战场,叛军就推出事先准备好的草车,并将它们全部点燃,熊熊烈火将毯车全部点燃,顿时火光冲天,哀嚎遍野,血流成河,死的都是自己人。在唐军自我混战的同时,叛军绕道唐军背后偷袭,唐军没有防备,全军溃败,哥舒翰只得带领生还士兵逃回潼关。可悲的是,哥舒翰出战之时20万人马,经此一战,仅剩下8000余人。没过几日,叛军乘胜攻城,唐军虽竭力抵抗,但军心涣散,且兵力不足,很快潼关陷落了,哥舒翰也因此失身被俘,甚至变节投降。可怜哥舒翰死不逢时,晚节不保,一世英名,化为流水,在哥舒翰死后,如日中天的大唐盛世悄然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