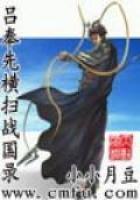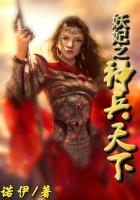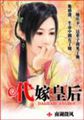中国五千年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史。
古往今来,无数的改革者在这道路上前仆后继。
且不说中国历史早期那些不自觉的社会变革和后来数以百计的中小型改革,仅是那些影响巨大的改革运动就有十几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秦始皇统一后的革故鼎新,气魄大,影响更大,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泽被千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盐铁专卖等举措,影响之深远何止一二千年?王莽改制,本拟挽救社会危机,却以轰轰烈烈始,以身败名裂终。北魏孝文帝改革,既显示出少数民族出身的改革家的卓越风采,又反映出即使帝王带头弃旧纳新也会碰到层层阻力。北宋的“庆历新政”,透露出一家哭还是万家哭的矛盾与隐秘;王安石变法,其是非功过至今众说纷纭。当封建帝国的君臣们骄傲自满、闭关锁国之时,世界风云却在不断变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一次又一次地轰击进来。于是,被动挨打的古老帝国踏上艰难曲折的近代化改革历程,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
一部中国改革史,既有成功的欢呼,又有失败的惨痛,无论何时何地,改革、变法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旧布新往往需要克服各种阻力,要经过艰苦的斗争,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
但是,究竟怎样改革才能成功,怎样改革会导致失败?
这是人们竭力探求而又不易搞清的大问题。为此,才有了和著名历史学者、媒体人,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的吴思先生的这次对话。
傅野: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商鞅到王安石,还是张居正,抑或是戊戌变法,这些改革大多失败了。而伴随着失败而来的改朝换代,最终却成功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国历史上,要创新制度是不行的,推翻却是可以的。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是什么原因呢?
吴思: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来评断这些改革的成效。
比如张居正,他在位时推出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当时是很受君主的推崇,而张居正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君主的重用,位高权重。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依然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我们不能简单的因为改革者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将其改革评价为失败。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等也是如此。
而朝代的更换,可以看作一个暴力集团打天下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江山取胜的,往往是具有血缘集团优势的。麻烦的是,血缘集团一旦取得了江山,一代一代向下分封,越往后血缘关系就越松散,而且人也越来越窝囊,因为不是淘汰竞争出来的,而是按照血缘继承下来的。
商鞅变法立了二十等爵位,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是一个暴力激励机制。从一等升到二十等,斩敌一个首级,爵位升一级,分田一百亩,宅基地五亩。到第二十级的时候就是封侯,就是一个小君了。这种制度同时规定,以前所有的封建贵族爵位要往下一代传,必须下一代有战功,否则他就不能继承爵位。
但是,原本封建制度下就是要世袭的,如果说不许、禁止,会遭来多大的反对意见?能不能活着出来得享天年都很成问题。商鞅就是这个结果,被车裂而死。谁挡这条路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起,吴起说咱们别一代一代往下传,三代终止行不行?不行,有的已经传到第三代了,这等于夺了人家的爵位,这不就得罪了整个楚国的贵族?所以楚悼王一死,吴起立刻就被追杀,伏在楚悼王尸身上被人用乱箭射成刺猬。
所以,简而言之,封建主义是暴力集团打天下的激励机制,一旦成功了也按照这个来分配财富。但是分配下去也有长期的弊病,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一个大弊病,分封的王和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标准的封建制度是上面有一个王,王下面有大批的公,每个公都有自己的军事体系、行政体系、税收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下面再细分。比如说三家分晋,晋侯本来就已经很牛气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但是他下面的三个大夫,每个都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军事体系和税收体系。三家分晋就是《资治通鉴》第一篇的第一个纪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原来的规则体系改了,周王居然承认了他们,封他们为侯,分三个大夫为侯,整个规则体系就破坏了,进入了暴力竞争的时代。下面小的暴力体系的实力一旦超过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有可能推翻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是说封建体系内部有一个暴力均衡,这个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天下就会很乱。春秋战国就是暴力集团的均衡不断破坏不断重建的结果。
傅野:当代也有不少改革者,但这些改革派官员的结局往往令人惋惜。
如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的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如今都已被废黜;现山东省省长助理陈光,中 共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是因当初的基层改革而得到保护性提拔,但历经“险恶”,他们有种疲惫和淡然;而剩余一批如仇和等改革的坚守者们,也依然顶着很多压力,带着“争议”的帽子。
您如何看待这些当代改革者遭遇的命运?这是一种必然吗?
吴思:他们都是改革浪潮中的个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个人命运,而归纳出“所有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个结论。事实上,只要我们找到一个成功的改革者,这个结论就会不攻自破的。
而一个改革者在决定是否进行改革之前,其自身也是经过利害计算的,比如改革的成本、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改革后的收益、自身的名誉等等。
傅野:失败的改革,是否都存在某些共同的原因呢?这是否与改革者必须拥有绝对权力有关?而改革者的身分,对改革是否成功,是不是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吴思:改革失败的原因,包括很多因素。比如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等等。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当权者对改革的利害考量,如果当权者认为改革是利大于弊,那么改革措施就可能会顺利地实行下去,反之就可能不会顺利地实行。
而成功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即便改革措施是从下面征集上来的,最终实施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改革主导者始终是官方,未来的改革要继续推进,就需要执政者有大担当。如果中国政权自上而下都勇敢地为国家担当改革的重任,中国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喜人的变化,我希望这种局面出现。
傅野:您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文中指出,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您觉得这种借力应该走哪些具体的途径?
吴思: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足人民群众发出声音的需要。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 锦 涛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以及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
近几年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当然,发表言论必须要有规范,对改革者要给予一定的宽容,多理解,多换位。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想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另外,还有司法,司法怎么摆脱行政的约束,相对地独立于行政等等。
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因此,应该有一个日程表,这样就可以让全国人民团结于一个新的目标之下,在一个新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建立一个新的公民权利社会。
傅野:1840年以降,中国遇到了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一个现象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当然有体制的原因,但知识分子本身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经过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知识分子已经被迫退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边缘,失去了具有民族特质思想的土壤,远离了传统的政治话语权;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真正突破进入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阵地,从而从外围来真正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两边都不靠,导致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态建设上面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
吴思:作为知识分子,既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更应当有建设性。要尽可能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和平转型。既要大胆揭露和批判公权的腐败方面,也要善意维护政府善治的权威。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稳步演进,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必须稳妥。
所谓稳妥,就是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所谓激进,就是改革方案脱离现实太远;所谓急切,就是改革的时间表安排得过于紧迫。
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堕入暴民和暴 政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在当下,知识分子应当更多地担负起启蒙者的角色,而不是破坏者的角色,只有这样,官方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建设成一个民主的宪政理想国。
(感谢徐阳协助整理本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