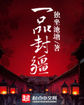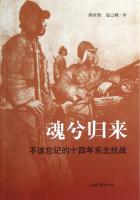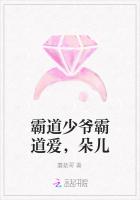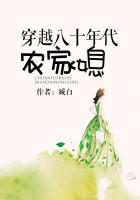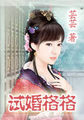历史画卷翻过了崭新的一页,卓资改革渐行渐远。
当人们再次翻开历史这本厚重的画卷时,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张楚,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政地方改革的第一位悲剧性人物。
影像在升腾,躯体却有弹痕。
挣扎与希望
卓资县是内蒙古中部的一个山区穷县,全县24万人,120万亩耕地,以农牧业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均年收入只有41元钱,财政自给率仅达20%,三分之一的人口常年缺粮,挣扎在贫困线上。
卓资县境内有七个火车站,卓资县人沿铁路捡煤渣、扫煤面、扒火车、行乞曾闻名京包沿线,饿极了的村民甚至公开扒火车抢偷车皮里的货物,见啥抢啥,有的为此丧命。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卓资人从陌生的“改革开放”这个字眼中看到了希望。
1979年至1983年,卓资农改轰轰烈烈。
1979年,卓资县就每人下放一亩口粮田,也叫救命田,这让老百姓喜出望外。
可天公不作美,1980年,天大旱,靠天吃饭的卓资县,没有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来了一次“秋后算账”,说卓资县完不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是因为刮“单干风”,搞资本主义所致。
一些本来心有余悸的人产生了迟疑,特别是一些戴过“走资派”帽子的人,更是胆战心寒。然而,老百姓饿怕了,无暇顾及这一切,只要能吃饱饭坐禁闭也行!
改革,似乎是人心所向,民意所期。
1982年,面对穷得讨饭成风的内蒙古卓资县,这个从北京派来据说有高层政治背景的县长张楚决意背水一战:在全国破天荒地把商业部门、粮站、供销社、食品店等国营单位由政府统一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1982年开春,卓资县十八台乡的陈润润在分产到户中,一家三口人分到了12亩地,加上自留地和一些五等以下的土地,陈润润分到了15亩地,四户村民分到一头骡子,价值1000元钱。当年陈家的收入是往年收入的3倍,上交了“国粮”,剩下的余粮还不少,有了粮食,陈家搞起了副业,养鸡、养猪,一年下来,家里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随着土地到户,“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倒台了,队委会也解散了。
张楚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卓资县炸开了锅。原来的商业局、供销社、粮食局及其下属商场商店的许多职工一下失业了。县政府就将卖楼的钱用于安置失业员工,给一部分钱,有点像现在的“买断工龄”,让分流职工投资创业,另谋出路。政府当时甚至还卖掉政府办公大楼和机关里的小车,用于安置因此分流的商业系统的失业职工和县属国营企业失业的职工。
同时,卓资县党政机构由原来的50个压缩为9个,公务人员由711人锐减至394人。县级干部福利待遇也实行货币化管理,搞“小政府,大社会”,压缩吃财政饭的行政人员,精简财政开支。把政府机关部门的车卖了,县城本来就不大,书记、县长、局长、科长统统骑自行车上下班,下乡坐公共汽车,发给交通补助费。
经此动刀,卓资县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财政收入上升而支出下降的县。张楚敢在县级心脏部位动手术,这令时任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非常感兴趣。1984年吕日周带着原平县的三十多位县级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到卓资县学习。谈到压力,张楚对吕日周说,关键不是他的承受力,而是旧体制的承受力。
失落的英雄
如今,卓资人对当年的“中国改革试点”讳莫如深。
在卓资人的记忆里,有那么几件事印象深刻。“一是流通领域打破大锅饭。当时,我们这里的粮食局和粮站、粮店,商业局和第一百货商场、第二百货商场,供销社等,改革力度非常大,可以说是全国破天荒由政府一统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改革在卓资县城展开。当时的卓资山镇是全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城镇人口近三万。
在那个年代,国营是全社会主义,政治地位最高;集体是半社会主义,极力向全社会主义过渡;个体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就要割尾巴、被革命。在这种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效益普遍不高,有的资不抵债,商业、供销社、二轻等部门大部分亏损,食品等部门濒临倒闭。
1984年7月,卓资县县委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城镇改革的决定,参照农村改革的经验,对城镇经济体制展开了全方位的“手术”。首先是下放权力,放鸟出笼。让企、事业单位从政府部门管辖下脱离出来,实行政企分开。
卓资县委的“动作”很快引起了自治区党委的关注,当时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周惠先后三次到卓资调研。1984年12月20日,旗下营镇被正式确定为小城镇改革试点。
改革试点的阻力很大。全国都是“社会主义”,卓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就要另搞一套,为什么要把国营的商场、工厂甚至国家的政府办公楼,局机关的办公楼卖掉呢?尤其是那么多的职工失业,全城都沸沸扬扬,人心惶惶。
很多人不满,也有很多人上告。坊间传言张楚是习仲勋的女婿。因为有岳父做靠山,后台硬,有尚方宝剑,所以才能大刀阔斧,无所顾忌,说干就干。
最终旧体制没能承受住他。
张楚原从北京调任而来,在卓资根基并不深。张楚把全部国有资产都转为民营的单兵突进行为,迅速遭到全县上下的阻击反对。而公车改革结果更令民众愤怒,“钱发完了,小车又全都养起来了”。
各方压力下,孤立无援的张楚被迫离开卓资回到北京,至今隐姓埋名。而之后的卓资县,机构和人员迅速反弹膨胀,恢复如初。政府办公大楼又重新修了,比原来更大,更气派了。各机关各部门的小车不仅又有了,而且比原来更多更豪华了,压缩了的行政人员又多了,并且翻番地增加,早已人满为患。
卓资改革在一片赞许声与责骂声中走过,而张楚成了内蒙古改革的拓荒者。
而这一切似乎是个宿命,扯起改革的大旗越早,所处的地区越落后,改革者越具悲剧性。张楚注定是一位失落的英雄。
如今,张楚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遥远模糊的符号。他只有过去,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现在。
他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消散在这片曾经风起云涌的改革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