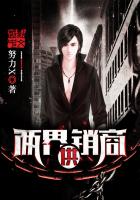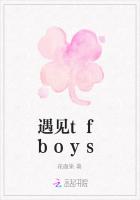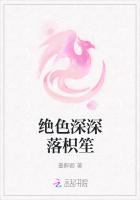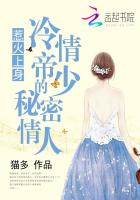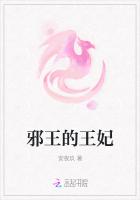这里出现的“太上”一词,帛书本作“大上”,旧注解作“大人”,其实为古书中称引黄金时代理想政治的惯用语,以下的两个“其次”和一个“其下”标明了创世后依次更迭的另三个非理想的社会统治形式,合起来看又恰好构成四时代的序列展开。从文意推求,老于认为理想时代的政治特征是,人民根本不知有统治者的存在,这一点似乎暗合于传说中的太古“无君”之世,如《吕氏春秋·恃君介入览》所说,“昔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此种无差别、无阶级、无君主的母系氏族社会正是老子理想之中“不知有之”的那种混一状态,因而被奉为“太上”典范。接下来的第二时代,其政治统治是建立在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的基础上的,其突出特点在于人民拥戴、亲近和赞誉统治者。相对而言,这种世道还算比较理想的。再往下到了第三时代,人民开始害怕统治者。按照第七十二章所说的“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的道理,一旦人民对统治者有了畏惧心理,政治威信也就丧失得差不多了。再往下发展,便是无道至极的现时代,政治方面的黑暗腐朽,已使人民憎恨和轻侮统治者了。按照循环模式惯有的逻辑,到了这第四时代,也就离回归初始为期不远了。老子自以为处在这样一种民侮君的黑暗政治时期,所以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政治理想是完全顺应历史循环趋势的。所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云云,代表着老子的殷切期望:就像《击壤歌》所显示的那样,统治者的寡言无为将使民众感到并没有人高高在上统治着他们,从而产生出“帝力于我何有”的纯任自然的观念,这才真正符合宇宙自然的总原理。第五十七章最明确地申说了这种治国主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
老子所引用的圣人的四个原则性教诲“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从根源上看都是取法于创世之前的混沌价值观。如前所述,创世之前正是道处于“无”的状态,也是其生命力最富有的状态。从本体论的“无”派生出的“无为”“无事”“无欲”等人生哲学规范,其潜在的信息似乎仍然是回归的要求:与宇宙性的回归于无极相对应,政治性的回归目标则是以“正”“静”“朴”为特征的圣境。
以上讨论明确了老子的退化历史观及四阶段循环模式的神话根源,下文将进而探讨老子循环论的特殊性及其产生原因。在此首先要涉及的问题在老庄哲学对“古始”“混沌”的独特依恋之情。
四、混沌之恋与初始之完美
老子哲学同一般的宇宙循环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之处,那便是循环回归的最终目标上的差异。前文中已经一再提及,老子为自己所设立的回归目标具有溯本穷源的性质,即要求回复到创世之前的混沌为一的状态。
老子在多次表达通过循环回归达到永恒这一思想时,表现出对“古始”这一神话原型的异常眷恋,他关于归根、归朴、归于无极和归于婴儿的种种换喻描述似乎都传达着同样一种努力——重新趋近于太初的“古始”原型。
《老子》第二十五章中有对古始原型的经典性描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在这段文字中,老子试图说明古始就是作为宇宙发生论之本源的“道”,这同作为宇宙运动规则的“道”即“道”之“有”的状态是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老子把“道”作为初始范畴加以解说时,一方面指出了通过循环回归运动而达到永恒性(“周行不殆”),另一方面强调了“道”的始源性(“先天地生”)和创生潜能(“为天下母”)。
在《庄子》中,这种作为古始的“道”得到一脉相承的强调: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老庄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理论建构的基点都集中到由神话所提供的古始原型,也就是创世神话中常常作为先天地而生、先于时空而存在的原始混沌(浑沌、浑沦)。《老子》一书的早期翻译者哈列兹(deH ar lez)于1891年就提出过如下看法:第二十五章中“有物混成”的“混”,作为名词使用时一般指涉“混沌”,约相当于西文中的Chaos;作为形容词或副词使用时意为“混沌的”或“混沌地”。不过,西文中的chaos(混沌)作为哲学概念专指宇宙本源状态这一件事物,而《老子》中的“混”概念可以兼指其他事物,尤其是用做形容词时。“混成”中的“成”字,意义是“完成”“成全”,意指某种所有事物都将从中获得完美性的东西。
蒋锡昌《老子校诂》也敏锐地看到:在《老子》中,最高范畴“道”同“混”有着一种微妙的特殊关系。他在注解第二十章“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若昏”等句时指出,司马光早已认识到老子描绘道家圣人的这种“纯纯”和“昏”的精神状态就是《庄子·应帝王》中作为寓言而提到的浑沌君的状态。蒋锡昌还认为,《老子》第四十九章所说的“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同第二十章的措辞“纯纯”“昏”“闷闷”有题旨上的对应关系,而且“浑”与“混”通用,“昏”与“混”发音相近,意义相关,所有这些用语都是以混沌观念为基础,用来描述道家所追求的“无知无欲”(第三章)的理想状态的一组同义词。
美国学者吉拉道特更进一步发掘了道家思想中的混沌主题,他对“混”概念的分析是这样的:
(老庄)专门把“混”加以突出强调,或把它与“道”相等同,或视之为初始的根源、原则,或作为“道”的神秘状态——“物”,由之主宰、控制普遍的现象世界的生物——宇宙的“生”或“创造”。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关于先于宇宙生成阶段的描述,那时尚不存在现象世界的分化的存在物。那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整体的或所有事物混合为一的(“成”)阶段。
以上引述表明,中外学者都已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老子把初始之道认同为混沌。在我们看来,这一事实的确认无异于把握住了遗留在初期哲学理念之中的神话原型。深入理解这一原型在神话思维中的意义和功用,有助于从根本上洞悉老子乃至整个道家思想的发生及特质。
在创世神话中,混沌作为天地万物产生以前的初始状态而出现,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原型母题。混沌母题有时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如巴比伦创世史诗中的海怪提阿马特;更多的情况下是以非人格化的形式出现,通常表现为混沌大水(海洋)或混沌之气。
腓尼基人的创世神话记载在《桑乔尼阿松之书》中,对混沌的描绘构成该神话的第一段:
万物之始是一种黑暗而凝聚的有风的空气,或一种浓厚的空气的微风,以及一种混沌状态,像埃雷布斯那样地混浊漆黑,而这些都是无边无际的,久远以来就是没有形状的。但当这风爱恋自己的本原(混沌)时,就产生了一种密切的联合,那结合称为波托斯,也就是万物创造之始。混沌并不知道自己的产物,但从它同风的拥抱中产生了莫特,有些人称之为伊鲁斯,但另一些人则称之为腐败而稀湿的混合物。创世的一切种子由此萌发,宇宙由此产生。《犁俱吠陀》第10卷第129首记录着印度最早的创世说,其中突出表现了太阳运行之“道”从混沌中开辟出时间和空间的思想:
既无存在,也无不存在,
既无空气的王国,也无彼处的天空。
有什么去包容,去遮盖,在……之中
它是否只是广漠无底的深渊?
既无死,也无不死:
没有把昼夜分开的太阳。
只有那在自身中安歇的“彼”。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最初,“万有”隐藏在
黑暗遮掩的黑暗中,在不可知的混沌中。
直至胚芽艰难地从无形的空虚中显现,
因热的巨大威力而诞生了。
在这里,混沌母题表现为黑暗的、广漠无底的深渊,这自然使我们想到老子也惯用同类意象描绘作为初始的“道”:
道冲,而用之久不盈。渊乎似,万物宗。(第四章)
敦若朴,混若浊,旷若谷。(第十五章)
从黑暗深渊般的混沌状态到光明照耀下的天地空间,创世过程常以太阳升起为其原型表象,这一点已在前文中涉及。古埃及纸草书中保存的太阳神创世神话对此做出了最具体的示范说明:
万物之主在他形成之后说:
我是作为克赫普里而形成的。
在我形成以后,才形成了形体。
一切形体都是在我形成之后才形成的。
众多的形体是从我口中说出的。
天还没有形成,
地还没有形成,
爬行动物在那里爬行的地方
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我从深渊中,从它的静止之中,
把自己抬高到它们之上。
当我找不到我能站立的地方时,
我在我的心中明智地思索,
我在我灵魂中缔造。
我独自造成了一切形体。
我喷出的是舒,
我吐出的是特弗内特。
我的父亲,这深渊,把他们送出。
这则神话把太阳创世主从黑暗、静止的深渊中升腾而起的表象作为世界创造的潜在过程,并把混沌之渊确认为太阳创世主的“父亲”,突出了混沌母题先于创造而存在的超越性和本源性。同前述几则神话联系起来看,似可大致归纳出混沌母题的主要相关特征:无形,无名,空虚,静止,黑暗,无边无际,先于宇宙而存在,具有潜在的强大生命力。对照老子哲学,可以说所有这些特征都是老子构筑其基本价值观的原型尺度。老子对“无”的推崇,对“静”的提倡,对“古始”和“万物宗”的虔诚崇敬膜拜之心,原来均可一一落实到创世神话的混沌母题之中。
在从神话到哲学的演变过程中,混沌一般是作为混乱或无序状态的象征而保留在哲学语汇之中的。奥古斯特·阿尔赫尼乌斯写道:“希腊文‘混沌’(Chaos)一词本指‘无秩序状态’,是秩序的对立面,哲学家又用该词指称宇宙初始物质的那种混而为一,均等分布的状态。”在西方文化史上,混沌作为创造与秩序的对立面,成了一个具有负价值的概念。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指出,欧洲民间风俗中的节庆演出,常常有这样一些代表着“混沌原则”(the chaos principle)的反面角色:丑角,滑稽人,魔鬼,骗子等。他们的所做所为与正常人相左,意味着无秩序,无规则,违反禁忌或超越常规。他们是这个由神创造的有秩序世界中的异己分子。混沌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这种贬值与负面意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创世主耶和华与混沌的原型性对立关系。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上帝最初的创造始于光明与黑暗的分开及对立,由于上帝视光为“好的”。黑暗的混沌自然成了好的对立面:坏的。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模式在《圣经》其他篇章中甚至演化生成出上帝与海中妖怪的敌对关系,混沌被人格化为各种代表恶的海中巨兽,后者在象征意义上又同在伊甸园中引诱人类始祖犯罪的蛇相互认同。如《旧约·以赛亚书》第27章中所说: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海中怪兽,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海中怪兽,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由以上材料判断,混沌母题在希腊哲学中作为秩序的对立面,在基督教神学中作为上帝的对立面,二者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中“混沌原则”的负价值基础。对照之下,混沌母题在中国文化中却一般只作为“古始”原型而出现,被人们强调的不是它的负价值或恶的象征意义,而是“万物宗”和创生本源的作用。因此,即使在最正统的思想家那里,混沌也会被视为回归创造本源的必要条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混沌母题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问自开辟以来,至今未万年,不知以前如何?
曰:以前亦须如此一番明白来。
又问天地会坏否?
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旧世界的终结便是新世界的开始,“混沌一番”既然是“又重新起”的条件,回归混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追索混沌母题在中国创世神话及宇宙发生论中的多种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本来不含有褒贬色彩的中性存在。大凡人们上溯天地万物之初始,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混沌。《三五历记》说: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这是将混沌母题与“宇宙卵”母题两相结合产生的盘古创世说。在此,混沌是天地、阴阳分化而出的本源。中国哲学中对此本源有许多不同的措辞和抽象,如《列子·天瑞篇》所述: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列子》中说的太初、太始、太素三者浑而未分化的状态浑沦,其实也就是混沌的同义词。清代学者任大椿《列子释文考异》已明确提出:“浑”与“混”是互换通用之词。《山海经》中所说“无面目”的“浑敦”与《庄子》寓言中的“混沌”其实是一回事。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如《淮南子·诠言》中的太一混沌说: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论衡·谈天》中还有元气混沌说:
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
在所有这些半哲学化、半抽象化的混沌(浑沌)概念中,都不带有价值判断上的贬义,按照道家归真返璞的一贯主张,“浑沌为朴”反而说明混沌是褒义的、理想化的。惟独在非哲理化的史书或神话地理书中,方可找到以人格化形式出现的混沌母题。《左传》文公十八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按照杜预的注解,帝鸿氏为黄帝。这个丑恶的化身“浑敦”是黄帝的“不才子”。《史记·五帝本经纪》又称之为“浑沌”。这是上古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仅见的具有负价值色彩的人格化“浑沌”。
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保留着尚未染上道德化色彩的浑敦神的具体描写:在出产金玉的神异的天山,英水河畔,“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毕沅注:江读如鸿。可知这位无面目的帝江神就是黄帝的又一化身。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中的帝江神是关于浑敦人格化的原始记载,《左传》中被认为是黄帝“不才子”的恶的浑敦是神话经过历史化改造后的产物。这一看法是完全合理的。由于道家思想的强大影响。这个负价值的浑敦神并未像西方文化中的“混沌原则”那样推广普及到民俗文化中去,也未能升格为中国哲学中的恶之象征,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有些余响而已。(这个混敦神以及作为“气”的混敦与“道”的关系,本书还要专节讨沦)。
通过混沌母题在中西神话与文化中的不同命运的对比考察,我们发现老子是使混沌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正价值的第一位思想家。正是由于老子对混沌为朴的原始状态的执著向往和热烈颂扬,加上庄子利用浑沌寓言所表达的哲学思想,混沌才得以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作为一种回归的神圣目标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老子卓然独立地打出了混沌理想的大旗呢?我们以为,比较神话学所证实的关于“初始之完美”(Perfection of the Beginnings)的信仰是解开老庄的混沌之恋这一大谜团的重要线索。在以下讨论中,我们将透过初始之完美的信仰去追寻道家思想发生的原始根源,希望能借助比较文化的考察进一步加深对道家哲学特质的理解。
五、玄同大同:中国的“复乐园”神话
《庄子·田子方》讲了一个孔子请教老子的寓言,它用现身说法的生动形式说明了个人如何亲自体验“初始之完美”,以及由此而获得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乐境:
孔子去拜见老子,老子刚洗完头,披散着头发等待它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木头人。孔子退出静候。过了一会见到老子,孔子说:“莫非是我眼花了,亦或果真如此呢?刚才先生形体直立不动有如枯木,好像超然于人世之外而独立存在。”老子说:“我的心已在最初万物发生的虚无之境游历。”孔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子答:“那是理智之心难以认知,人类语言难以描述的。让我试着为你说个大概。至阴寒冷,至阳炎热。寒冷出于天,炎热出于地;两者互相交合而万物产生。万物产生有其规律但看不见形象。死生盛衰,时隐时现,日迁月移,每日都有所作为,却不见它的功绩。生有所萌发之本源,死有所归返之境地,始终循环往复,既无端点也无穷尽处。若不是这样,还有什么能构成初始本源呢?”
孔子又问:“您能告诉我游历此境的情景吗?”
老子答道:“到达这种境界,是最美好最快乐的。谁能体会到最美好最快乐的境界,谁就可以被称为至人。”
庄子的这个寓言表明了道家的个人理想,那就是能够像故事中的老子那样“游心于物之初”,从而超凡脱俗成为至人。这种“游心于物之初”的信仰同人类学家、宗教史家所说的“初始之完美”的信仰似有不谋而合之处。
艾利亚德指出,“初始之完美”是由对“失去的天堂”(LostParadise)的想像性追忆所唤起的神话信仰,也是一种深刻的宗教性体验。所谓失去的天堂,指那种先于现存人类存在的至福极乐状态,一种理想化的和谐完美状态。由于人类祖先的过失、罪孽或堕落,或者由于宇宙万物发展的循环变易法则,现存人类已经远离这种早已逝去的初始天堂状态,处在社会衰败和道德沦丧之中。
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表明,完美至乐之世曾经存在于世界初始期的信念是非常古老,也非常普遍的。这种观念能够被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所吸收和改造,被赋予新的价值。苏联神话学者梅列金斯基写道:“神话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原始神话的基本特征,在于对事物本质推本溯源:对事物的构成加以阐释,即说明其由来;对周围世界加以描述,即讲述天地开辟的经过。……世界的现状——地貌、星辰、各类动物、各种植物、生活方式、社会集团和宗教典制、一切自然的和文化的客体,乃是远古的事态及神幻的英雄、祖先或神祇的事迹所致。而神幻的往昔——不仅是一般已逝去的岁月,而且是特殊的始创时代,即神幻时期、始初时期、经验时期肇始前的‘原初’‘起始’时期。”
道家所追求的“游于物之初”,从神话学立场上看,就是借助于想像和幻想重返那样一种“原初”“起始”的神幻时间的精神尝试。这种尝试为个人摆脱不完美的现状,回归“初始之完美”提供了一种心理途径。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性的复乐园神话。
在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有一种集体性的复乐园神话。按照这种神话信念,初始之完美表现为祖先曾经历过的“梦幻”(theDreaming)时期,那是世界创始、英雄先祖们创立文化基业的时期。一切光荣和伟大的创始事件均在那时发生:水和火如何被窃丢失又重新获得;风俗与禁忌制度如何确立;部族和氏族怎样划分出来;图腾区域如何对生存空间加以分割,等等。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指出,澳州土著神话的根本主题是对“梦幻时期”的追忆与沟通,与神话相对应的仪式活动也力求重演、再现那个初始时期的实况,以便使现存人类重新获至那个时期所特有的超自然法力。
复乐园神话的更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重返创世之初的黄金时代。在前文中讨论退化历史观时已经涉及到这一点,即许多民族的神话都把人类至福的乐园时代上溯到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个时期。那时不仅人在道德上纯洁无瑕,没有打上任何罪恶的烙印,而且就是在生理方面也享有后来的人远远不可企及的天然禀赋:或是像《圣经》伊甸园神话描述的那样永生不死,或是像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描述的黄金时代之人一生享受盛宴,死亡犹如睡眠。除此之外,初始之完美还可以体现为极度夸张的人类长寿。据耆那教神话,人类在第一个时代身长约6公里,寿命有840万年。随着时代循环推移,最终到了当代,人寿只剩下不足百年。佛教传说也曾把最初的人类说成是具有异常生命力的,能活8万岁。这类夸张说法自然使我们联想到中国道教神话中的长寿仙人,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庄子·逍遥游》中提到的彭祖,传说他活了七八百年,与印度神话中的初始之人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不管细节如何不同,神话总是倾向于一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观点,即把远古作为理想时代,把初始时期看成一切尽善尽美的时期。
在神话时代的人们看来,初始之完美虽然是早已逝去的、发生在世界创生之际的过去状况,但又是可以借助于宇宙循环周期的进程重新趋近或再度获得的。换句话说,复乐园并非子虚乌有般的幻想,而是一种坚实可期的未来前景,是以循环历史观为基础的普遍信念。如安达曼群岛土著居民便确信,在现存世界终结之后,人类也将毁灭重生,新的人类将重享天堂状态,那时没有疾病、衰老和死亡。波斯古经《阿维斯塔》所描绘的人祖伊摩在历经四个时代以后为逃避宇宙灾难性寒冬而建造的“瓦拉”,也是以特殊形式表达出来的复乐园神话。瓦拉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与外部世间完全隔离,其中四季常青,流水潺潺,果类与食物取之不尽。那里的人没有疾病,不生残疾,没有贫穷,没有说谎,没有卑鄙。每隔四十年,每对夫妇都生出一男一女,各种动物也是如此。这样自然调节的出生率永远不会导致人口危机和生态问题。
复乐园的神话主题同样潜存于巴比伦和希伯来的古文献之中。《圣经·旧约·创世记》所描绘的始祖犯罪和逐出伊甸园是以上帝的最终拯救为补偿的。似赛亚书》借上帝之话表示:“看那,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从犹太教的《旧约》发展到基督教的《新约》,回归天堂时代的希望由朦胧变得具体,特别寄托在死后将复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身上。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曾深刻地指出,整个《圣经》只讲了一个神话故事,其情节叙述模式类似于标准喜剧的U形结构:“开篇的《创世记》讲述了人类失去生命树和水,而最终又在《启示录》末尾重新得到了它们。在这两端之间,以色列人的故事被讲述为一系列的灾难,即先后落入各异教王国的掌握——埃及、非利士提亚、巴比伦、叙利亚、罗马,而在每一次灾难之后都接着出现一个短暂的相对独立的时期。除过历史部分之外,在约伯的灾难和复兴的故事中,在耶稣关于浪子的寓言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U形叙述。”由《圣经》神话奠定的这种介于乐园的“失”与“复”之间的U形叙述结构成为西方文学中一再重复出现的一种原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