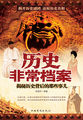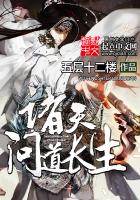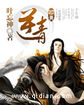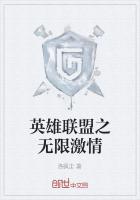在任何时候,董安于都不是赵鞅的腰,而是他腰间的智囊。
董安于深刻地认识到,荀跞跑官、要官的行为固然不可取,但是此一行为最大的危害是,一旦梁婴父代替荀寅的职务成为事实,那荀跞就等于为晋国又贡献了一个中行氏。
因为梁婴父其人居心叵测。一旦飞黄腾达,势必祸国殃民。
要为国举贤,别为国举奸。
这是董安于给赵鞅的忠告。
赵鞅接受了董安于给出的忠告,婉拒了荀跞跑官要官的行为。
这是一个大国首席元老的政治觉悟,当然也是赵氏家族自我保护的一个预防性举措。赵鞅只能这么做。
但是荀跞的心渐渐硬了,他恨不得一口把赵鞅给吃了。只是赵氏家族的势力不是一口能吃得了的,荀跞那叫一个着急。
野心家梁婴父也着急,只是他着急得比较有分寸——这是一个野心家和军事家之间的区别。
梁婴父趴在荀跞耳朵边悄悄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赵氏的力量要做大,那是咱们智氏的悲哀。要命的是现在韩、魏两家成了墙头草,一看赵鞅受宠,全倒向他那边了。大王,做人要厚道,下手要趁早。
荀跞就像放屁被人堵住了屁眼,那叫一个难受:别说没用的,快说怎么下手吧。
梁婴父就告诉荀跞,要一个人死有一万种方法,但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是砍去他的左右手。现在谁是赵鞅的左右手?谋臣董安于。只要这个人在,赵氏力量做大只是时间问题;这个人去了,智氏力量做大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梁婴父,就是大王您的董安于。
荀跞深深地望着梁婴父,觉得他实在够无耻。
但是,这样的无耻,他喜欢。因为有时候,无耻也是一种力量,让人浑身有劲。
无耻者无惧。
24小时之后,赵鞅在一个问题面前心乱如麻。
问题是这样的:这场举国震惊的内乱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尊敬的赵鞅首席元老阁下,请您告诉我,荀寅为什么要主动攻击您呢?如果董安于不在您府中私自调动军队,荀寅会铤而走险吗?所以表面上看,这场内乱是荀寅起头,可要是刨根问底,董安于不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吗?尊敬的赵鞅首席元老阁下,您千万别告诉我这是您的主意,否则我会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呈国君来处置。
问题的提出者当然是看上去一脸诚恳的荀跞。当然,这个说法不尽准确。准确地说,问题的提出者是梁婴父,表述者是荀跞。只是赵鞅不知道这其中的内在关节罢了。
其实,事情走到这一步,赵鞅知不知道都已经无所谓了,要命的是问题本身。
问题凶猛啊!
凶猛得简直要人命!
董安于命不保矣。赵鞅突然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当初的自私和暧昧。表面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率先动武;可当董安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调集时,他却躲在一边不闻不问。
这是致命的暧昧,置董安于的命。现如今荀跞步步紧逼的提问毫无疑问敲响了他的谋臣董安于的丧钟……唉,董安于命不保矣……
也是致命的开脱。开自己的脱。赵鞅当初旗帜鲜明的表态和紧随其后的不闻不问成了今天他明哲保身的最好武器。荀跞也深刻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能以调侃的方式告诉赵鞅别乱揽责任,做过婊子的人就不能立牌坊,这是战国江湖的行为准则。
站在战国起始年代的蔚蓝天空下,衣冠楚楚的晋国首席元老赵鞅就这样在一个问题面前心乱如麻。今天他将失去他的左右手,明天他会失去什么呢?没有人告诉他。但是,这样的年代,失去是永恒的主题。没有人可以最终获得,暂时获得的也将很快失去。
一切都已是命中注定。
赵鞅满脸落寞地向董安于问计,以应对荀跞的咄咄逼人。
董安于不说话,只是看向他。
董安于看向赵鞅的眼光里有泪。董安于原以为,赵鞅不敢先用兵只是想做个遵纪守法的模范人物,却不成想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赵鞅充分利用了他的忠心耿耿,在率先用兵的问题上将他推出去做了替死鬼。
董安于输了,输在他对主公赵鞅的不用心上,输在他对人性善良面的不抛弃、不放弃上。而赵鞅却对他用心了。赵鞅早就抛弃了他放弃了他,现如今却一脸愁苦地向他问计,继续做遵纪守法状、做大智若愚状。
对董安于来说,曾经的苦谏恍如昨日,但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因为赵鞅绝对不会将责任揽下来,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失去董安于,对赵鞅来说,只是壮士断臂。赵鞅做得没错,在目前情况下,壮士断臂是明智的选择,只有敢于断臂、勇于断臂,逆境中的壮士才能有明天。而左右手是没有明天的,左右手就是左右手,要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
仅此而已。没什么复杂的,也没什么想不通的。
把什么都想明白了的董安于选择了自缢身亡。他甚至给赵鞅留了遗书,告诉后者在其死后将他弃尸于市。“这样荀跞包括智氏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已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可保主公无虞。如此一来我也就死得其所了。”
董安于果然死得其所。
因为荀跞再也没说什么。
赵鞅安然涉险。他失去的只是一个谋臣,获得的却是整个家族的安全。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一方面感慨董安于忠义救主,一方面羡慕赵鞅福气好,身边竟然有如此不惜命的人才。
战国年代,人才最贵。不惜命的人才,那是贵上加贵。赵鞅也是心情复杂,若有所失。他偷偷地在府中为董安于设了灵堂,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喃喃自语。至于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赵鞅的另一个举动是抚养了董安于的家人,当然也是偷偷的。因为赵鞅深深地明白,在这样的年代,要想光明正大地干一件事情,真是太难了。
经过了“信任危机”事件后,作为晋国首席元老的赵鞅开始义不容辞地担当大任——率兵攻打荀寅和士吉射所部。朝歌城内外,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
但是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是不平衡的。局势的发展变得对赵鞅不利。国际上,齐、鲁、郑、卫等国倾向于支持荀寅——国际势力乐于看见一个大国的分裂。晋国四分五裂了,他们的好处才是大大的。
好在五年之后,荀寅和士吉射所部支撑不住了。智族荀跞在看够热闹之后也在晋定公的一再催促之下出兵援赵。荀寅和士吉射不敌,放弃朝歌城仓皇逃奔邯郸,但还是在邯郸落不下脚,无奈之下只得逃出国门,来到齐国寻求政治庇护。
自此,晋国六卿中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行氏和范氏在该国的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历史在这里做了减法。但历史还将继续做减法,因为六卿去二,尚存四卿,下一个出局者呼之欲出。当然,在历史老儿给出答案之前,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推测出谁是下一个出局者。
这是历史的有趣与诡异之处。总之,愿赌服输,在战国江湖上玩游戏,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四个字。